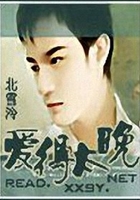因为自悔失言,她的脸上浮起两片浅浅嫣红,像是桃花落尽的芬芳,自有一种令人无限怜惜的风情。而木槿的树影投到她身上,落下浅灰的暗色。她微微低着头,眼里透出无限的懊恼,像是小孩子不当心做错了事,害怕被责骂,但又带了点不甘不愿,终归让人心里不由柔软起来。
苏慕北止住笑,道:“走吧。”
回到安西官邸,苏慕北自是有大堆的军务要处理,谷衣这久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回房休息,刚躺下就听见小孩子呜呜的哭声。谷衣自己有了孩子,最听不得小孩子哭,只觉得那哭声悠悠钻进耳里,心也一下一下牵着疼。谷衣叫来秋兰问:“是谁在哭?”
秋兰侧耳倾听了一阵,脸上露出迷惘的神情来,说:“没有听见有人哭呀。”谷衣不信,起身顺着哭声寻去,慢慢越走越远,最后到了内院最里面的小楼,哭声就从里面传来。谷衣记得这栋小楼原先是废置的,现在倒像是有人住在里面,于是问:“这里住的是谁?”
秋兰道:“住的是萧姨娘。”
谷衣顿了一下方道:“你进去看看。”
秋兰去了不多时,抱出一个小小的孩子,是苏焕辰,脸上挂着成串的泪珠,萧姨娘陪笑跟在后面道:“夫人,孩子不听话,妾身正管教呢。”
谷衣接过孩子,这孩子她只见过一次,现在细看,一张小脸满是泪痕,眉目十分像苏慕北,她心里不由生出母亲般的疼爱。掏出手绢细细拭去他脸上的泪,温言道:“不哭了不哭了。”
苏焕辰嘴一撇,边哭边道:“妈妈打我。”
谷衣看他哭得可怜,轻声哄道:“不哭不哭,我帮你骂你妈妈。”苏焕辰这下才止住,睁着滴溜溜的一双眼,奶声奶气道:“妈妈坏,骂妈妈。”连秋兰也撑不住笑了。
谷衣问道:“孩子做错了什么打他?”
萧姨娘张了张口,脸色有点发白。倒是苏焕辰抢说道:“我读不出来,妈妈打我。”
这下连谷衣也笑了,只觉得小孩子真逗,又不能跟他讲道理,只好顺着他的话说道:“读不出来就算了。”
萧姨娘忙上前道:“夫人,我错了,下次不敢再打孩子了。”
谷衣看她脸色发急,额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心下奇怪,总觉得隐瞒了什么。怀中苏焕辰委屈瘪嘴道:“那个字老师没有教。”
谷衣含笑道:“那我教你好不好?”
苏焕辰乖巧道:“好。”说:“我去拿来。”
谷衣放下他,对萧姨娘笑道:“这孩子真可爱。”
萧姨娘勉强笑笑,说:“夫人,我错了,以后不敢再打孩子了,您看您刚回来,要不您先去歇息,我自己来教。”
谷衣点点头,刚准备走,苏焕辰已经跑出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带着哭腔道:“要你教,要你教。”
萧姨娘一把大力拉过他,看见谷衣皱眉,讪讪道:“这孩子不懂规矩。”
谷衣看他小脸上满是害怕,许是常被打骂。想来苏慕北并不喜欢这个孩子,甚少关心。萧姨娘又是满身不得宠的怨气,不免发在孩子身上。虽说不是自己的孩子,心里却也心疼,就道:“我先教了他再去休息。”
苏焕辰闻言脸上高兴起来,挣脱他母亲,走到谷衣身边,秋兰早搬来椅子,谷衣坐下,把他抱到自己腿上。苏焕辰指着报纸的右上角:“……如……竹”小手指着第一个和第三个字,“老师没教。”
谷衣只一心看他的样子,并没有留心报纸上写的什么。闻言向他手指的地方看去,细细说道:“第一个字念势,第三个字念破,势如破竹,表面的意思指就像劈竹子,头上几节破开以后,下面各节顺着刀势就分开了。”谷衣看他一脸迷惑,心里笑自己,这孩子这样小,哪会听得懂。就指着报纸上的字,“跟我念一遍。”说话间,余光已经看清这个词语原是报纸标题的一部分,顺口一起念了出来:“苏军势如破竹。”刚念完心里突地一跳,眼光慌忙往下面扫去,只一眼,脸色瞬间雪白。
苏焕辰无知无觉,跟着念:“苏军势……如……破……竹……”
谷衣只觉得耳旁像是有无数的虫子嗡嗡飞来,那一个字一个字,像是一把把锈迹斑斑的刀,慢慢的一把接一把插进她的心里,钝钝的,麻木的。她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从头一个字一个字看起,正标题下有一行副标题:辛三小姐身陷安西,定北军心存忌惮,苏军势如破竹。
还是不相信,又从头看了一遍。辛三小姐身陷安西,定北军心存忌惮,苏军势如破竹。这一个个字,她都认得,可是连在一起,她却仿佛不认得了。一字一句念出来:“辛三小姐身陷安西,定北军心存忌惮,苏军势如破竹。秋兰,告诉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秋兰看着那双眼睛,无波无动,像是一潭死水,那声音也无情无绪,听起来平静得——平静得不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发出的声音,心里生生打了个寒颤,扑通一声跪下去:“夫人,我不识字,我不知道。”
谷衣嘴角浮起一缕笑容,端端让人生了无限的惶恐,萧姨娘仓皇叫道:“夫人。”
谷衣只觉得气血上涌,那报纸竟像有千斤重一样,怎么拿也拿不住。苏焕辰小小年纪也觉得不对劲,自己下到地上,怯怯走到母亲身边。谷衣无知无觉,慢慢站起身,往前迈了一步,眼前一黑,身子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