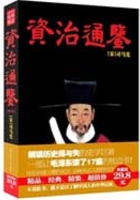然后一个可爱的女生冲了出来,看见我后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故意撞了我一下。
拜托!我旁边的那个才是许沐川的正牌女友好不好,我也是受害者好不好!
我扭过头去大受伤地问许小爱:“我没你漂亮吗?”
怎么可能嘛,我这么天生丽质这么沉鱼落雁这么花见花开车见车载的。那人什么眼光嘛!
许沐川捏着快要散架的礼物走出来,看见我和许小爱就笑得很好看:“没办法啊,我已经够默默的了,但耀眼的光芒还是无法遮盖啊。你知道她们刚才都喊什么么?”
那还不简单。我酸溜溜地说:“不就是喊‘许沐川,我爱你’呗!”
许小爱超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臂,幸福的眼泪撒出来:“哥,她终于说了!”
什么?哥?
“嗯!”许小爱“嘿嘿”地奸笑:“有一次我跟他提起我有一个朋友,也最喜欢欺负我了,而且还说什么‘这是爱的表现’,哥哥就特别受伤地问‘啊,居然有人抢了我的爱好啊’,然后就特别关注你了。当哥哥说他喜欢上你时我特别赞成,我多么希望你们以后彼此眼中只有对方,那么你们就可以遗忘我,就没人欺负我了,哈哈,到那时我就自由了!”
许小爱许沐川,许小爱许沐川,我怎么没想到呢,居然是兄妹!怪不得两个都特别好看,原来是基因优良啊!
原来是合伙欺负我啊!我扭头就准备走,许沐川抓住我的手臂问:“你干什么?”
我“哇”地一声哭起来:“我干什么…该问你干什么吧…兄妹一条心对吧…把我耍得团团转啊…当我是白痴呀…”
许沐川轻声地哄我:“行了行了,别哭了,再哭别人都以为我真的干了什么呢。”
我终于破涕为笑,但仍不依不饶地说:“喜欢我干嘛呀,不是有女生投怀送抱的嘛。”
“那不是她投怀送抱,我不是在拼命拒绝吗?你听到的呀,我不是拒绝吗?谁让你都靠近我了却不说喜欢我,让人家都以为我名花无主,就都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我觉得有道理:“那就……”
“那就在一起呗。”
在一起啊可以呀,我喜欢啊,我梦寐以求呢。但是你们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很痛苦诶,所以我也不能让你们好过。
反正你也喜欢我。
“不行!”我现在是老大了。
“怎么不行?”许沐川循循善诱,“在一起了我就有主啦,那些狂蜂乱蝶就可以挡回去了,我可以天天给你买樱桃西米露,还可以每天送你回家,早上你就可以多睡十分钟呢。”
每天早上多睡十分钟,我想想这个就觉得垂涎三尺……有车就是好啊,即使是单车。
“那以后……”
“从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许沐川笑得很愉悦:“故事的最后不都是这样的吗?”
考试前夕,纪善晚才坐到图书馆里温习功课。她的成绩很糟糕,前途似乎一片渺茫。坐在五月明媚阳光里,习惯性耳机里放着歌,用右手托着下巴看窗外无所事事地发呆,和等待沈音叙。
当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沈音叙出现在门口时,看见善晚正在明眸善睐地回答一个男生的告白:“我也喜欢你啊。”正当男生无限欢喜时却听见善晚继续说:“就像喜欢其他人一样的喜欢。”心里突然似雷电闪过,那么善晚,到底怎样的男生才会让你觉得不一般呢。
善晚生得好看,骨骼柔弱伶仃,有一种令人疼惜的美。哪怕只是懒懒地撅起嘴,想要的便信手拈来。她会在深夜睡不着时发来骚扰短信:“告诉你七个快乐的方法,多关心我,多想我,多照顾我,多疼我,多见我,多多打电话给我,最重要的就是喜欢一个这么古灵精怪的我。”
暧昧甜美的撒娇,沈音叙内心的喜悦不知道如何安放是好,单单一条短信便弄得他几乎一夜无眠,第二天旁敲侧听地试问时,善晚却说就只是短信啊,带着一脸无辜的茫然和疑惑。
仿若鱼刺梗在喉咙,按照剧情铺展的告白无法说出一个字。从此,沈音叙就是以保护的姿态站在她的身旁,却不言爱。就像小时候怀里抱着的五颜六色糖果,舍不得打开,仿佛只要轻轻一旋转颈口味道就会被风抢走吹散。只想让那种气味被长久的封藏保存,永远都不想松手。
沈音叙在这头善晚在那头,中间隔着一段距离,可她仿佛感应到有注视的目光,便转过一张如茶花般洁白的脸庞来,眼睛里面涌动着潮水般的欢喜。
善晚总是这样,扰乱一池春水又不负责任地离开,别人还在祈求再给一个欲说还休的目光,她的心却早已走过万重千山。
沈音叙走过去翻查善晚搁在桌上的数学习题集,还是一片空白,密密匝匝的失望融进风中:“善晚,你不乖。你没有听我的话好好做题。”
沈音叙身型清瘦如挺拔的竹,惹得很多女生侧目看。家境殷实,母亲是优秀的钢琴家父亲在政府工作。自小到大没有经历太大风浪,顺利长成品学兼优的男生,年年拿一等奖学金,前程是一段早已铺织好的锦。
善晚眨一眨眼,把桌下细长的双腿伸展出来:“好啦音叙,我们走吧。”然后自然而然地挽过沈音叙的手臂,分给他一只耳机:“这是我最近听的CD,我敢打包票音叙你肯定也会喜欢的。冷锦的声音真的很赞。”
Lavender,一个学生兼职酒吧驻唱的乐队。最近小范围地发行名叫梦境爱丽丝的专辑,业内评价不错纷纷赞有潜力。
沈音叙笑得有些意味深长:“冷锦的声音是不错。但我觉得歌词写得更不错。”
善晚调皮的笑容仿佛是寂寞的水底开出的一朵娇艳珊瑚礁:“扯诶,我还可以厚脸皮睁眼瞎地说我唱得比其他人都好呢。”
“是吗。”沈音叙绅士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此时万家阑珊灯火,纵使隔着几步距离梦中佳境仍在。善晚缓慢地开口,一个音调一个婉转地溅落在唇齿间,她的声音仿佛白色鼓鼓的茉莉花蕾被泡在清水里,搅动一下玻璃杯里的碎碎花瓣,就微凉而小心翼翼地握住沈音叙的耳朵。虽然赶不及冷锦的声音空旷如开满蓝紫色烂漫野花的草原,却多了份女生情怀的旖旎婉约,像下起五月江南的绵绵密密细雨,柔软无声地落满心房。
有宝马急速行驶而来,善晚被车灯照亮的清澈双瞳写满惊慌。沈音叙眼疾手快地拉过善晚拥进自己怀里,终于与车咫尺地擦身而过。
“没事了。”沈音叙轻声宽慰着明显受惊的善晚。却又见那车在前方骤然熄火灭灯停下,车门打开走出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不紧不慢地朝他们走过来。
沈音叙侧过一张好看的脸:“你躲我后面”,善晚心头缓慢温柔起来,好像蓄起一汪清浅的水。那人却把目光不偏不倚地落在善晚的身上,良久竟轻轻笑出声来:“小姑娘歌唱得不错,我们公司刚好有个歌唱比赛,如果有兴趣就请和我联系。”然后右手递过来一张名片,善晚踟蹰地接下望眼一看便落满璨亮的惊喜,男子微笑着点头转身离开。
“会去吗,善晚。”沈音叙的声线清浅颤抖,哪怕结局昭然若揭,他也想孤注一掷地听到结果。
“你会支持我对不对呢,音叙。”善晚问,一张脸写满纯真期待。
原来她和其他人无异,也是想要歌舞升平,想要镁光闪耀,想要绵绵甜糖,想要华丽衣裳。
善晚。
善晚夜晚睡不着干脆爬起来推开窗,有薄凉的晚风吹进来,院里的蔷薇就扑簌簌地落满一地芳香四溢的花朵。远处灯塔忽尔掠过微薄的光线,稍纵即逝,却艳丽得让心里无限欢喜。正如冷锦用清冷声线唱出的歌词,轻而易举地就让自己心中的不知所措和仓皇不药而愈。让自己被一片湖水覆盖,而心躺在那里轻轻呼吸,不愿意醒过来。
冷锦。
是一个拥有怎样凉薄凛冽眼角眉梢的男生,越是浓烈的情感,越是根深蒂固地深植于心中。只会在凌晨时盏着灯,面容不动声色却内心波澜起伏地写下这些破茧成蝶的字句。他应该不食人间烟火而站在虚无缥缈的云端,拨开厚重云层对自己伸出手,便划来一抹最耀眼的彩虹。
去初选时善晚独自一人,在不停穿梭混乱的人群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期待着沈音叙会出其不备地站在她面前。
窗外有成群飞鸟极块地掠过苍穹,云朵堆积成黯灰色的塔,下一秒就要跌落下来。善晚杵在原地惊讶于天气的更更迭迭,被一个慌乱奔跑的女生撞得生疼。女生早已学会娴熟的化妆技巧,不需他人太多指教就将自己打扮精致像杂志上的平面模特。
肇事者却反过来先发制人地怪罪,善晚不服气,把双手交叠在身后仰起一张年轻倔强的脸:“怕你就不是纪善晚。”
气氛剑拔弩张蓄势待发,四目相对,空气仿若被掐断交汇处顿时火光四溅。有男生仿若未见地走过来,女生眼睛里燃烧的火焰像浸进一波凉水,愤怒就被熄灭得无声无息,波光潋滟明媚动人,欢喜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锦。”
粟色头发的男生,穿质地厚重的牛仔裤和侧面印着红色五角星的板鞋。戴金属感浓烈的戒指。面孔笼在一片炽热凛冽的光线中,双眼像夜幕中的星辰般熠熠发亮,望过来的目光深得像一口井,引人不由自主地坠落进去。善晚竟喃喃地低声唤:“冷锦。”
是Lavender的主唱,冷锦吗。善晚还来不及开口询问就被安排站上了舞台。
明亮炽热的追光灯落在中央如圆月,架着一只孤单单的立式话筒,掌握杀生大权的评委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潦草地翻阅一下善晚事先填写的资料后抬头说:“就清唱一段副歌吧,限时三十秒。”
善晚并没有开始唱,而是习惯性地拿眼在参差不齐坐了百来人的观众席里到处寻找。
没有沈音叙。
他或许是在图书馆里翻阅英文原版小说,或许是在黑板前写下条理清晰的解题方式,或许在帮老师整理学生档案之类。反正,他不在这里。
善晚的心脏像被扎了一针,细小的伤口涌动着剧烈的疼痛。原来等待里,时光那么慌张那么凉。
她想起那次两人一起去有不灭灯火的游乐场,新落成正式营运第一天。那是托沈音叙父亲的原因,拿到了两张免费的通票。
善晚执意要看晚上的烟火溅起时最动人的缠绵,一脸期待欣喜得像贪玩不肯走的孩子。人群如春季回潮的鱼群,一丛一丛地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什么时候原本握在一起的手被松开。
她在原地急切地唤,声音轻巧地就被淹没。她才明白,其实不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她想就可以见到沈音叙。
善晚双手合拢放在胸前开始唱。空气像一只温暖的手不断轻轻地抚摸她,善晚想象自己是一只在枝头伶仃无依的花朵,她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哭出声来,眼眸如一汪快要溢出的清泉。
等到最后一个尾音都跌进沉重的幕布里,周围的灯光纷纷乍起明亮如白昼,仿佛显影药水里的照片,善晚才看见不知几时赶来的沈音叙,灯光伴着尘埃在微微单薄的肩头起起落落。倚着门沿脚底的converse迅速淌出一条细小的溪流,他朝她疲倦地抿出一个微小的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