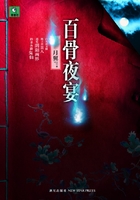这个傅觉冬连亲爹都要蒙,真是大逆不道。祈愿心里暗想。
此刻店主的小儿子精力充沛东奔西跑着,顽皮得让人头痛。母亲追在身后一脸疲态无奈,却又满脸幸福欢乐。
祈愿咬着筷,只是不自觉的,又想起言玥。
她长睫一抖,抬头看他,秀净无匹的俊容,动静相宜。
她突然动起鬼心思:不知道傅觉冬是喜欢儿子还是喜欢女儿?
如果是个儿子,是个到处闯祸惹事的小破坏王,他会不会像阿育王一样抱着他坐上王位,教他骑马射击,把自己所有统统毫无保留继承给他?
如果是个小公主,她会撅起嘴来向他撒娇闹脾气,他会不会也像白瑞德对邦妮一样,给她穿银色的小舞鞋和粉红色的蓬蓬裙、搂着怕黑的她安然入睡?
祈愿一手支着脑袋,情不自禁,笑盈盈就开口了:“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问得如此随性,仿佛就跟问他要不要添杯茶一样。
傅觉冬却猛地仿佛叫蜜蜂蛰了般,惊愕的一个抬头,眼中聚着深究解析的眸光凝望她。
她虽后知后觉,可一见傅觉冬这夸张的反应,立马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有多暧昧而不合时宜。怎么说她现在还是傅太太的身份。
傅觉冬是如何机敏精明的一个人,一定以为她有歹念,想续约或者附加条款之类。
祈愿被自己的话吓出一身冷汗。
“啪啦哒”一声,她手里的筷子铛然坠落。霞飞满面。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摆着手急切争辩:“我没有要想和你生孩子,我一点点这个意思都没有。况且你要生孩子又不见的要跟我生,你可以找随便什么女人生的!”
老天爷,她都要窘迫得哭出来了,这种过犹不及的解释还不如不解释。
傅觉冬单眉一挑,更加精研不惑地望着她面红耳赤,笨舌口拙的表情。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还不放弃,接着往黑里描、往牛角尖里钻:“我不是说你放荡形骸,私生活不检点。你要生孩子也不一定要找女人的,现在科学那么先进,像C罗那样找人代孕就行!”
天哪,她在说什么?祈愿连想死的心都有了。什么叫矫枉过正她算是明白了。她真希望他能暂时失聪一下下,耳蔽她刚才一连串胡说八道、不靠谱的解释。可是傅觉冬偏偏还那么认真的望着她,听得一字不漏。
她解释了半天,仿佛是打完仗,觉得自己心慌气短。
“帅哥,我要加水!我要加水!”她死撑着窘笑,抬臂拉住一边持着长嘴铁壶的小伙子。
“那个……你刚才不是说要收钱不要嘛!”那小伙子还不忘笑诮一下。
祈愿急了:“你你你这么那么不机灵,一点推销意识都没有。没看到我们杯子都空了么?”
傅觉冬眸中诧然透出一中虚凌的幻色。就在刚刚,她说话的样子让他蓦地想起一个人。低头只是不动声色轻斟浅酌。
小伙子倒完茶,祈愿蒙头捧起杯子“咕咚”一声喝了个底朝天。
“儿子!”
“啊?”她还没从窘迫的深渊里爬起来,他的话如冰点漾到她耳边。祈愿抬头,傅觉冬随性的持着一串土豆置放到烤架上,眉宇间都是倜傥的俊逸,“我要儿子!”
“为什么?”她几乎凭着本能就问出来,直接得自己也觉得唐突。可是依旧是好奇。
“女儿多好,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大学时看《乱世佳人》,祈愿有多爱那个不可一世的瑞德船长对女儿没有原则的娇惯和纵容。他多希望有一个像白瑞德一样的父亲,宠女儿宠得全镇出名。
“不!”傅觉冬眸色深凝,暗得发亮的瞳孔有种攫魄的可怖,他幽幽的说:“我只要儿子!”祈愿有一瞬间的窒息感,傅觉冬手中铁棒上,那串土豆被火烤得嘶嘶作响,仿佛低声的哭泣,土豆的边缘已经开始卷缩而发焦。可是他依旧还在炙烤着,就像上帝看着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
不知为何傅觉冬突然不高兴起来。一张脸绷着。祈愿反复在脑海里回放之前的对白,也不知道哪句话得罪了他。
而脱离烟雾缭绕的店外,上海的夜,灯火辉煌。
果腹后田师傅将车驱到傅邸门前,祈愿旋开车门,而傅觉冬只是幽幽坐在后排,冰雕般不动,并没有要下车的意思。她和司机见惯了他这副龙颜不悦的表情,谁也不敢造次往枪口上撞,只是默默的不说话。祈愿孤身下车。
“你下车吗?”最后还是不得已问了句。
“你先进去!”他冷漠的一应。祈愿和田师傅交换了个无奈的眼色,转身而去。
女佣们已经都回房,祈愿精疲力竭的脱下鞋,赤脚踩在印度手工名贵地毯上。她没有开走道上的灯,因为她懒得再跑回来关。只想一路迅速寻到自己房门进去便罢。
终于,她来到自己的房前,低头寻着银质门把,刘海很长了,挡住视线,她抬手向一侧掳去,另一手终于感受到冰冷的门把。只是遽然一道黑影突然从身后一下压上来,祈愿一个心惊身颤,整个包“啪嗒”一声掉在绒毯上,仿佛一声无力反抗的闷哼。
而傅觉冬已经将她整个困进自己的臂膀中,不得动弹。
她被完全唬住,“你你要干什么?”
傅觉冬没有回答,沉重的鼻息顶在她额头,这个男人,连呼吸都是冰冷的。
她想起来自己应该反抗,他已经踢开门,将她粗暴的推进去。
清冷的月光洒进来,镀在她发颤的身体上。
“傅觉冬,你发什么神经?”她很没底气的骂他。
傅觉冬还是不回答,可这次她看清他的脸了。双眼鹰隼般的冰冷的像两把刀。
她倒吸一口凉气,紧张仓惶史无前例涌上心头。脑里冒出一个荒谬无比的理论:他是不是要杀她?
她拔腿要闯出去。却轻而易举被他抓回,傅觉冬真是疯了,将她双肩钳制,用力压到床上。她吓得不可抑止的颤抖起来。
他只是不顾一切吻上她的丰唇。祈愿想躲闪,怎奈他是吃了秤砣般铁了心狠狠咬住她。她感到窒息般难受,凌乱如兰的轻喘,不自觉的张嘴呼吸,他趁虚而入侵占住她芳泽,吮吸、轻啃。
可是她还是不依,卯足了吃奶的力推他,挣扎出他可恶的唇。他的手不规矩的到她身上探索,滑进她的白T恤。直到听到她清幽的鼻音啜泣。
他终于离开被他蹂躏红肿的那两片柔唇。
“怎么,还没做好准备尽妻子的义务?”他指尖划过她下巴,笑起来,却是沁入五脏六腑的冷讽:“我可是刚给了你张支票的。”
祈愿好似被他狠狠刮了两巴掌。她是贪钱,可是还没到出卖自己的地步。潋滟溶溶的眼满是屈愤。咬着唇,一字一字从舌尖吐出:“你给得太少,买不起我!”
他仿佛一憾,然而只是半秒,最多半秒,立即又恢复笃然冷酷的笑,目光竟是不偏不倚寻到角落的那只青瓷花瓶:“那个值多少钱?”
祈愿只觉得脑袋一轰,仿佛被无形的铁锤击中。
他讽刺她?他一针见血提醒她被贺意深夺去的那个吻么?
祈愿整张脸不争气的气红起来。
他总是这样,可以一言击中你软肋,如镭射般精准。
“有些事,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除非我不想知道,我可以装不知道!”他的话像劈头倒下的一盆雪水。
“同样的错误,犯一次就够了,一而再,再而三就不那么可爱了。”
他的唇冰凉彻骨,擦过她滚烫的颊。就像无数针尖从脸上碾过、擦过她滚烫的耳骨,声音低柔却冰冷:“祈愿,我不喜欢重复提醒!你最好记住这一点!”
傅觉冬终于松开她,一个凌厉的起身,扬长而去。门被砰的一声关上。
祈愿仰躺在床上,很久很久都处于一种游离而无意识的漂浮状。很久很久她才回过神思索起他的每一句话,吓得瑟瑟发抖。她跑到门前把锁别住。然后又把衣橱里的毯子一条条搬出来全裹在自己身上。可是依旧辗转难眠。一闭上眼睛就是傅觉冬那张放大可怕的脸庞浮现眼前,简直比贞子、伽椰子、美美子加起来还可怕。
大约是吃了太多烤肉,她只觉口干舌燥,喉咙干涩发烫。她拗不过自己的身体,思想斗争了不知道多少时候才不得已爬起来。
她太怕遇见他,时至如今还是惊魂未定。脚步轻得跟猫似的,一溜烟弯进书房。
祈愿长吁口气,从药箱里取了包喉糖,将药箱阖上,正想物归原处,只是她眼神好,格案最深处,一个袖珍的药瓶被藏在壁镜后,引起了她的注意。在微微发黄的灯光下透出幽光,仿佛蕴藏着无限的秘密。她抬手透过壁镜,伸手去摸,一点一点的接近谜团。终于盈盈一握,就像钓到上钩的鱼儿难掩兴奋,将手中的瑰宝昭然灯光下。
果然是一瓶药,瓶中只剩一半,绝对有人定期在服用。可是问题就来了,既然一直有吃,为什么还要藏得那么神秘呢?
她微微转过茶色瓶身,“卡莫氯片”四个字赫然入目。
她突然一个激灵。
卡莫氯片,又称孚贝,是专治食道、食管癌症的药物!是谁?是谁患了食管癌?不祥的预感扼住她的喉咙。
瓶子上贴着医生龙飞凤舞的字迹,她很努力的辨认出来那三个字。是她!
她患了食道癌?
她患了食道癌?
所以她嗓子一直沙哑着,她却以为她只是感冒,所以家里菜谱都改得清淡易吞,她还以为只是厨师贴心。
食管癌是发生在食管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起初只是声音沙哑,喉咙痛,慢慢的,淋巴压迫声带,患者会渐渐失去说话发声的功能,直至死亡。
她倏忽一个颤惊,突然幡然,想明白一件事。
所以……所以她才要雇用她么?
窗外夜色浓重,无星无月,祈愿瘫软着倚着墙默默滑下,明天的明天,还有怎样的阴谋陷阱等着她?
可是傅觉冬,傅觉冬又为什么要答应娶她呢?
言玥的话一遍遍回荡在潮湿的空气中:“他不会娶我,我一点也不惊讶,可是我惊讶的是,为什么他会娶你!”
为什么呢?窗外,又下起雨来,滴落在片片梧桐叶上,淅淅沥沥。
她想起一首诗: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
大片的落地玻璃窗前,从66楼眺望出去,浦江夜景尽收眼底。车灯川流不息,旖旎辉煌。犹有一览众山小的磅礴浩汤气势。
麦永嘉独立窗前,星河楼宇踩于脚下。两刷浓眉凝出一道深深堑壑,暗眸迸发出可怖的光芒,如被困在一道解不开的魔咒中。
“老大,人都到齐了。”乐训在身后提醒。
“嗯,”麦永嘉沉声一应,没有动。身后的一屋子人都噤口而待。望着他的背影巍然窗前,楼宇林立,直上擎天,霓虹缤纷姣丽,与无数繁星共接壤,互竞亮。
他手里磨捻着一串佛珠,鸦雀无声的空间里发出“嗑哒、嗑哒”的拨珠声,诡谲而森然。
终于,他转过身,一双炯眸迅速如豹在屋内每个人身上扫一遍。那目光像上弦之箭随时放矢。
声音低沉:“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件事要宣布。”他停顿了下,“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他缓慢凝重地重复了两遍“非常”。
一屋子人有的胆怯,有的狐疑,有的漠然,有的纳罕,相互交换神色,却不敢说话。
“咦,七哥呢?”也不知道谁环视点数后发现贺意深竟不在屋里,藏不住的惊疑起来。
众人这才如梦初醒,四下搜寻查找起来。
“不用找了!”麦永嘉一声冷叱,“老七不会来了!”
大家又是诧异又是震骇,只是将目光牢牢凝在麦永嘉身上,等待答案。
“饺子,你跟老七时间最长,你说说看老七平时待你们怎么样?”
被点名的饺子浑身一个悚然,抬头却是立马激扬答道:“七哥平时忠义仁智,对手下更是一向有肉大家吃,有酒一起醉!能跟着七哥混是我们弟兄的福气!”
麦永嘉幽幽眯眸,缓缓坐下,悠悠然开口:“既然他待你们不薄,你们也对他没有半点生分,那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给他下套?”后半句说得豪气盖天,狮吼虎啸,风声鹤唳。
“老大,我们不明白……”一个中直的人冲在前问。
“不明白?”萧楷冷笑,“哪个王八羔子竟敢在老七车上做手脚,放了那么大个炸药,伊拉克都被夷平了!被我查出来,他个崽子别想死得太痛快!”
在场众人,无一不被震慑。
“大哥,三哥,我们二十四个兄弟自出道来跟着七哥,一直忠心耿耿,你何必这么说?”有人出来打圆场。
“兄弟?”乐训鹰眸横涤一瞬,无限凛利,“是23个兄弟和1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