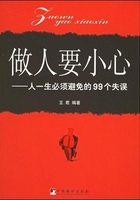为了夺权,为了争官,为了山头和派性,人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利用宣传单、大字报、传单互相攻击、互相丑化、互相谩骂,继而是大集会、大游行,后来发展成全面内战、全国性的大武斗。开始用拳头、用棍棒,打砸抢抄抓。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给武斗火上浇油,乱世英雄立即用作大搞武斗的借口,许多地方发展到用枪炮、坦克的地步。广州的大街小巷都是传单和标语,“紧急呼吁”“十万火急”“X X告急”“惊天血案”这些骇人听闻的标题触目惊心。火药味、血腥味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今天打倒了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打倒。如果说“文革”初期是“痞子运动”的话,现在已变成了“狂人运动”。中国大地已成了野心家、冒险家的乐园。
我们厂是“文革”初才筹建的新单位,办事处又在远离工厂的广州,大家刚从五湖四海汇集在一起,没有历史上的积怨,所以我们都未卷入派性斗争中去,大家都是观潮派,都在忧心忡忡地看着国家正在遭受的劫难。看那些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看那些耀眼的政治流星,看花开花谢,看潮涨潮落。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拥挤不堪、交通不畅的情况下,我步行一了五十多公里才回到了湖南老厂。一方面是办些公事,另一方面是照顾妻子生小孩。我到后不几天,儿子智明便出生了,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孩子全靠自己来管,拉屎撒尿,洗尿布,洗衣服,给孩子洗澡,穿衣服都是我来做,既要照管小孩还要照管妻子的生活营养、休息起居,忙得手脚不停。但心里很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但我希望他不是我们命运的延续,不要像他爸那样吃那么多的苦,饱尝人世间那么多的艰辛。我要为他创造一个幸福、祥和的未来。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厂里计划在一九六九年初试制和生产了。夏厂长出差到湖南老厂来,打算从老厂再调一批老师傅去。我和妻子商定:在这动荡年代里,我们一定要生活在一起,以便在生活上、精神上互相照顾和依托。我向夏厂长提出这个要求,他显得有点为难的样子。但他又不愿违背两年前的诺言,他叫随来的管人事的陈科长对贺进行“政治审查”,在查看档案后又去贺的老家调查情况。后来我从侧面知道了贺的家庭概况:贺的老家是当地的大资本家兼地主,其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以捞鱼虾为生的农民,后来在当地一家杂货店当店员,杂货店的老板死后,经营十分困难,老板娘想把小店打出去,可是谁都不敢接手。后来老板娘叫三个店员抓阉儿。
他抓到了阉儿,不得不接手杂货店。他克勤克俭,苦心经营,不但生意渐渐地好了起来,在短短七八年间还成了当地的大商家,在解放前几年还买了一些田产,解放后就成了工商业主兼地主。不过贺父比较开明善良,在群众中口碑较好,没有受到批斗和冲击,直到“文革”前还是当地的人民代表。夏厂长与新厂的最高领导通过电话,征得同意后才决定了贺的调动,一九六九年元月,我带着妻子和出生才两个多月的儿子随同其他几位技术骨干从湖南到了海南岛。在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安了家,家是十分简陋的。双人床和三斗柜是厂里配给的,唯一的高档电器就是熊猫牌五灯收音机,但这个家是幸福的、温馨的:有活泼可爱的儿子和同甘共苦的夫妻。
“九大”以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敌伪政权的乡长、保长、连长、宪兵以上共二十一种人都是清理批斗的对象。清理这些人肯定要殃及其亲属子女。在老兵工厂特别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兵工厂,有这类关系的人不少,但新建的兵工厂,员工都是新招的,都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贫下中农的子女,是出身好、根子正的红五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两口子便成了“万红丛中一点黑”,特别引人注目。我妻子从来到这里就未安排工作。开始,我们还以为是照顾她多休息几天,以便照料孩子,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未安排工作。我找到夏厂长,他显得很为难,叹了口气:“唉!先休息一阵再说吧!”于是我心里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无产阶级夺回了文教战线的领导权,岂 能让地主资本家出身的人继续把持教育战线!如果安排在车间则更是危险。这样就把她挂了起来,长期不安排工作。半年后,组干科张科长通知我:将我妻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去放牛。我当时就火了:
“亏你们想得出来,我儿子才半岁,正在吃奶,你们这样做还有点人性吗?”
“哼!你敢说组织上没有人性!”
“我是说你没有人性!”
“我是代表组织宣布这个决定的!”
“你代表不了组织,你叫朱军代表和李书记来,我俩是通过组织调来的,你们如果认为我俩不够条件,可以退回老厂去!”
“你以为你了不起哇!没有你我们厂就不能转了吗?”
“对!我就要你这句话,如果你能代表组织的话,马上把我退回老厂去!或者把我俩一块下放到五指山放牛去,以便照顾正在吃奶的孩子,孩子是无辜的,你总得给我一条路呀!”
看到我们吵架,来了几个同事,把我劝走了。
我一脸怒气回到家里,妻子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敢告诉她,在她的再三追问下,我把刚才发生在组干科的事说了。她哭了,哭得好伤心,似乎把近几个月的委屈都哭出来了。我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唉!我真傻,在这造反有理的年月里,我为什么要服从组织分配?那些下了调令拒绝来的同事们在老厂不是照常工作吗?!那些家庭背景与我妻子相同的不是仍旧在教书吗?!在老厂仅仅是精神上的压抑,但没有这么严重的政治歧视。而这里吃的、住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那样艰苦、困难,连吃水也得从山下的井里挑回家,与老厂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为何来呢?
可能是觉得我还有点利用价值吧,有关方面再也没有提及将我妻子下放去“五七干校”的事了。虽然工资月月照领,但我俩情绪低落,特别是妻子心情很坏,经常找我吵闹,我工作也提不起精神来。夏厂长找我谈了一次话:
“我知道你们两口子很委屈,心里很苦,你们服从组织调动,来支援‘三线建设’,竟落得如此的对待。你是我亲自点的将,你有气、有怨可以朝我来。可是我比你们还委屈啊!我是按照党的政策和组织原则办事的,现在弄得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找谁去发泄啊!”
夏激动得有点哽咽了,他点燃一支烟,猛吸了几口,调整了一下情绪,继续说:
“工厂马上要试制和生产了,现在是用人之际,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你要以工作成绩来体现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再说,这个世道不会总是这样吧?!”
我这个人心肠软,别人一两句贴心话就打动了我的心。“士为知己者死”,那股干工作的傻劲又上来了,起早贪黑地为厂里的产品试制忙碌着。我从学校毕业第二年即一九六0年赶上老厂试制这种产品,与老工程师、老师傅们一起摸爬滚打,跟着学了点东西。现在是在一个新厂试制同一种产品,所不同的是自己由配角变成了主角。我主要是负责工模具设计与制造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历来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关键。一是要求精度高,二是消耗量大。我利用这些年来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在工具上作了系统的变革,在精度上作了宽严适度的修改,在生产效率上也采用比较先进的新材料、新工艺,所以工模具生产和供应比较顺利,这使全厂的人都感到吃惊和佩服。
我妻子在“靠边站”了大半年后,被安排在托儿所,这种安排显然是不合理的。但作为权宜之计,这已是较好的结果了。我们对维护自己权利的抗争应当有理有节。过了一段时间我找到那位张科长,质问他:
“你们认为我妻子家庭出身不好,不能教书,怕她毒害下一代。托儿所里都是幼苗苗,没有任何批判力和免疫力,岂不是更容易受到毒害吗?!”
这一次他没有与我打官腔,想说什么又没说,眼珠子转了转,算是听懂了我的话。一九七0年,我妻子被调到工具车间料具库当管理员。一九七一年初,我被调到厂革委会生产组主管技术工作。从种种迹象看来,对我们这类人采取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政策,表现出一点宽松和理性,这使我们感到一些欣慰和希望。
一九七一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对中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林彪一伙推行的极“左”路线被慢慢纠正。外交路线和国内政策都呈现一种理性和灵活的迹象。“文革”中被打倒的老一辈领导人先后恢复了职务和工作。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也出来工作了。这些迹象是正义战胜邪恶的结果,还是邪恶对正义的暂时让步?当时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对国家对人民所带来的好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随着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等一系列外交胜利,改善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处境,摆脱了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全面紧张和孤立的局面。在国内经济方面,邓小平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工业、交通、教育、科研等各行各业都慢慢有了起色。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人的理性和良知都在慢慢恢复。这一切都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和曙光。人们满以为随着林彪的倒台,中国会走向长治久安。
一九七三年七月的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一篇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文章,把在升学考试中交白卷的张铁生吹捧为反潮流的英雄。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把邓小平的整顿污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复辟。我有个同事叫梁宝权,他的思想很活跃,说话很风趣,按照他名字的谐音,大家都叫他“两毛钱”,他常叫我“王老大”,我与他的政治见解和其他许多观点比较一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天早晨我刚进办公室他就问我:
“王老大,今天早晨的广播听到没有?”
“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