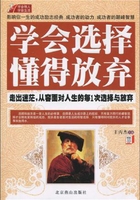飞葳一只手颤抖地指向我,委屈万分:“逐风你听我说,都是情鸢不好,亏我把她当成姐妹,她却敲晕了我扔进山洞,然后冒名顶替我来同你成亲!我千里迢迢追来京城,却发现你们出征了,呜……”
不用问也知道,多半是飞葳的“意中人”不要她了,飞葳回头又惦记起了燕逐风的家产,她拼命给我使眼色,我可悲地居然领悟了她的意思——“我就暂时借来混几个钱,完了就把他还给你!”
燕逐风那么聪明,不会被蒙蔽却也不说破,他轻笑着揽了飞葳的肩,拍了拍:“其他暂且不论,回来就好。”似曾相识的亲昵。
后来飞葳告诉我,那一刻我的脸色好可怕,像要冲上去和他俩同归于尽似的万念俱灰。
飞葳留了下来,无论燕逐风的召见还是飞葳的拜访,我都闭门谢客一概不理。
有几次偶遇,燕逐风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便把话岔开,因为如果他真的亲口告诉我要迎娶飞葳,或者撵走我的话,我不敢肯定自己能够不怒火攻心把他撕碎……
索性很快我就有事做了。南边连年向熵朝称臣纳贡的边陲小国,也不知道受了谁的挑拨,突然兴兵北伐,偏巧这时某地诸侯王显露反叛迹象,燕逐风手握重兵,皇帝担心派他去戍边是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计,于是调拨兵马委任了另一位将军。
燕逐风的意思是,我也同去。
我已无法分辨,他是忧心社稷,还是在借口支开我,总之我没有逆他的意。
“情鸢,有劳你了,此去路远多加小心。”燕逐风握了握我的手,飞葳也来送行,客套不停,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摸样。
浴血疆场是我,坐享其成是她,我心内戚戚然,说出来的肺腑之言反而像讽刺了:“我是将军夫人嘛,不能和你长相厮守,也要怀君之忧,忠君之事。”
戍边之战两败俱伤,敌阵里有懂法术的人,我中了毒箭而坠马。我想,也许战死沙场埋骨他乡比较好,来世化为一棵树,站在风里,隔着黄沙古道和燕逐风遥遥相对,浮生共憔悴。
在腥味的狂风里,有人倒提长锋,嘴角挂着一抹邪笑向我走来……
[肆. 飘零事后千载东风相谢]
我被人救了,救我的说起来还是旧识了——献帝英崖。
他大骂熵朝皇帝这老狐狸,果然没有派燕逐风迎战,顾此失彼。英崖说别人的时候忘记了自己,远交近攻,通过挑拨边境小国来借刀杀人的他就不阴险了吗?
“不过白捡了一个美人儿,也算不虚此行。”他一只手挑起我沾血的下巴,“你肯定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情景了,你乘一匹骐骥,在战场上翻手云覆手雨,连发梢都浸染鲜血,就好像狼烟深处走出的阿修罗……”
阿修罗族,异域的诸神之一,生男极丑,生女则有惊世美貌。
在英崖微微迷醉的神色下,我也想起了那时的自己,风波险处心正炽,可就算为燕逐风竭我所能,他心中装着天下苍生,唯独容不下一个爱他的女子。他和飞葳都那么无情,真是绝配。
献帝想要熵朝军情,面对严刑逼供我守口如瓶,被审得烦了就胡说一气。
他终于气急败坏道:“你等着瞧好了,不用你我一样打败燕逐风,到时当着你的面将他挫骨扬灰才解气!”我打了一个冷颤。
又有一天,英崖眉飞色舞地拎来一个金丝鸟笼,那鸟笼比不上冰冷可怖的刑具,可不知为何我心里突然涌起大难临头的感觉。
笼中怪鸟雀长了一张人面,活像《山海经》中的“凫傒”。这种鸟我认得,它本身不能言语,但可以复述别人的话,一字不漏绝无谬误,所以名叫“信”鸟。
原来献国的丞相机敏,纵使熵朝皇宫布下天罗地网,还是给混进去了一只长翅膀的“探子”,它偷听到的这段话,对行军打仗没什么用,却几乎能要了我的命。
投食之后,信鸟惟妙惟肖地模仿了起来。
一开始是燕逐风的声音:“这次戍边之战,我想再让情鸢随行,一是可确保万无一失,二来……也能避免她在府邸和飞葳争风吃醋,再起事端,否则收留她反而得不偿失。”
我胸口的物件狠狠往下一沉,什么是“得”,什么又是所谓的“失”,权衡之下,一切都是算计!
“可大将军你千万想好,边陲艰苦,刀剑无情,情鸢姑娘万一有个闪失……”比较担忧我的居然是军师,多讽刺。
燕逐风回答:“那样岂不正好。”
——杀人何须刀剑,六个字已经兵不血刃地置我于死地。
原来有了飞葳这强悍的心上人,我就立刻变成了棋局中的弃子。也许是我唇边浮起的笑容太诡异,英崖扶了我一下:“你无妨吧?”
我惨笑:“为免燕逐风知道我被你捉住,前赴后继派来刺客灭口,你还是飞鸽传书送他一个我已身亡的好消息吧!”
一语不发抚着我头发的人还是不错的,至少他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收声。如果能为一段不堪前尘祭上眼泪,之后便封存沉底是最好不过了,可是我哭不出来,眼若枯井。
我彻底地转了性,拼命折腾我以前记住的那一点东西,对英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有一日,我还是趁其不备逃回了熵朝。
怎么用元神翻山越岭,越过栈道和一座座城池,怎么潜入将军府,我都不知道,一切都在浑浑噩噩中完成。站在朝思暮想,又恨得咬牙切齿的人身后时,我屏息凝神,他则在一堆兵书地图前猛然转过身来。
看到曾允诺要迎娶的女子,他的第一反应是拔剑——燕逐风以为我是来寻仇的。
我笑着走向他,张开五指握住那把反射窗棂外月光的双刃剑,当剑尖离我的胸膛愈发的近,燕逐风的手像是动摇似的发抖,剑终于“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我弯腰替他拾起,他不禁微微蹙眉。面前一只恼羞成怒,涕泪纵横的妖怪,抑或是鬼怪——没有比这更可笑亦可怖的光景了。
“要除掉我何其容易,何须又是设计又是演戏那样大费周章?只要大将军一句话,甚至不必亲自动手。我已经生无可恋,死何足惜?”我凄然说到。
“你……都知道了。”燕逐风半晌才沉声说,开口的话显得那么多余,“既然你能来到这里,就说明你还没死对不对?”
“将军大可放心,我活不了的。这个妖怪因为你而有了‘心’这种东西,有了七情六欲,你爱她护她时,她可为你千军万马四海潮生,你若弃她,那么这个自己她也是不稀罕了……”
话音未落,燕逐风,这个所向披靡的一代名将眼里居然显出了一丝怪异的慌乱,或者说是——“害怕”。在他莫名伸出的手指碰触到我之前,我转身跑了出去。
乱云翻涌的天际忽然破开一道莹白的伤痕,然后一道天雷准确无误地落在了我身上。
“知道我为什么今日才来找你么?”我倒在地上,只觉筋骨尽碎,五脏俱焚,张开嘴一口黑甜的液体就涌了出来,“妖即使不修仙,也不该杀生犯天条,反正……我已经在战场上杀人如麻,索性归途上又除了几个恶人,正好……凑齐了挨天雷之数。今天就是我的天劫之日……”
“不——”我听见逐渐远离的嘶吼,温热的东西砸在我渐渐雾气般弥散的身体上,我感觉他的手滑稽地在地上摸索,想把我抱起,却只能是徒劳无功。
打散的精魄彻底消失前我想:若是,若是那一日,我没有在熙攘的红尘,多看他一眼……
[伍. 盛世花对残阳,忘前朝]
英崖第二次救了我,用一座城郭换得高人出手相助,那方士暗中庇护了我一路,最后又在落天劫后及时聚拢了我的元神,移魂到了附近一个刚下葬的年轻女子身体里。
我苟全了性命,只是美貌不再,道行尽失,英崖一字一顿告诉我,这次我终于可以不再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好好活一次。情鸢,是完全属于他的情鸢,他会珍重我一生一世。
不久之后,熵朝传来消息,飞葳死了。我怀疑是英崖暗中遣人所为,替我报仇,他但笑不语仿佛一种默认。
我以为已经被打上封条的心不会再疼,此时还是揪了一下。半月之后,封条彻底裂开,因为,燕逐风被斩首了。
熵朝一直蠢蠢欲动的诸侯王兴兵造反,大将军通敌叛国,做了那人的内应。造反重罪下没被凌迟腰斩,夷三族已算皇帝仁慈。可是我不相信,那个比谁都痛恨战乱,一心为国的燕逐风,会做出这种有违常理的事!
后来又听闻,燕逐风是因为心爱的飞葳死于非命,才会沉郁终日失去理智,入了叛党。
英崖不知是不是开解我,说:“也许和飞葳的事没关系,有个词叫‘功高震主’。你和飞葳一‘死’,燕逐风等于失去了左膀右臂,加上你来之后,我不再热衷开疆辟土,熵朝战乱剧减,燕逐风这个牢牢把持着兵权的人在皇帝心中,百害一利,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我的天地没有倾覆和崩裂,只不过以后平淡如水的几十年,我都活得好像行尸走肉。
几十年,人间沧海换了桑田,我和英崖都形容枯槁,他言信行果,一生对我不离不弃。
英崖病重之际攥着我的手说:“很多年前我听说飘渺山上有两个妖怪,一个艳冠神州,一个清秀绝伦。我只想要那清佳之人,派了方士去找,可是被她逃掉了。燕逐风探到了我的动静,唯恐我得到妖术后如虎添翼,才会忙不迭向九尾狐妖飞葳提亲。”
我红了眼眶,那个人啊,从来都不是真心之人,他到底是谁都未爱上。
弥留的英崖已看不到我失神了,喃喃说:“想不到,你终是兜兜转转地来到了我面前,老天待我甚厚……这一世,我已无憾。”
多少人可以如此坦然说满足?我捂紧了那双渐渐摊开的手。
我回去熵朝。天边霞光好像我初见谁时那样绚烂,城上云絮,也好似那日护城河边城阙,簇拥着那个举世无双身影的流云般风行流动。
城高休独倚,而今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飞葳没有和燕逐风合葬一处。走向那被腐败枝叶覆盖的石碑我步履沉重,不算尽职尽责的守墓人忽然叫住我:“你想知道燕将军身死的隐情吗?”
老人告诉我燕逐风被杀,是因他当时一意孤行要辞官。
我难以置信,那个人居然放得下视为比性命更重要的责任?守墓人叹气说大将军是要去寻一个人,他总觉得她还没有死,加上半生的金戈铁马也疲了……可是皇帝不信啊,担心对朝中军机,战略部署了若指掌的燕逐风辞官后转头就投奔造反的诸侯王,遂起了杀心。
我还想问什么,一回头,哪里还有什么守墓人。半空中盘桓着一个声音:“为了候着姑娘你,我已为燕将军多留人间四十年,不快些上路不行啊……”
我颤抖着手指,拨开枯枝败草,拂去碑上经年累积的尘埃,显出碑刻铭文——是夫妻合葬墓。燕逐风的名讳旁边,赫然写着“夫人情鸢招魂葬于此”九个大字。
有什么顺着脸庞潸然而下。我想起他在马上轻轻护住我,想起他叹息般说“也许你已经成功”,想起他说我是他的夫人,想起那些认真的算计,真实的动容,想起天劫之日他泪水的温热,和太迟太迟的不舍……
人间一百年,竟比山中千年还要来得心力交瘁。掩面长叹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大限已至。我到底是借尸还魂的妖,死后精魂散去,不得再世为人。
燕逐风,你已然转世,而我正要湮灭,或许当你抬头仰望无垠苍穹时,会有一瓣不知何处飘来的细小鸢尾花落在你挺秀的眉上,不等你察觉又被清风带走,就像风吹散眉头雪。
所以你终将漏听,那隔世也执拗说着爱你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