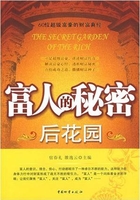其实这玉锁中哪里有什么事关天下机密的东西,不过是两家和亲时随手写下的诗句罢了。林卓然蹲身正想捡起,身侧神色木然的女子却先他一步,将那纸条抓起,痴笑着松开手,让那纸条随风,远去。
而后伏在他的肩头,似心满意足地,快要睡去。
千尘历颜武二十年,异术师暮色夜观星相,述有青鸾星动紫薇劫,衔玉女子必将更朝替壤。
时帝君重赏暗寻此女,欲扼之,以求福佑闻廉王朝。
云照国皇城上空,一行征雁嘶鸣着北飞。
当朝二皇子永安站在大皇子府的袖壁旁,有些发怔。
对面长廊上,湖蓝色长裙勾勒出旖旎风情,却有一点鹅黄,似桃菲尽放的初春时候,碧水滩涂上探出的嫩芽,夹杂在数团姹紫嫣红中,不动声色地入了他的眼。
“殿下。”
他一愣,那点鹅黄却已到了眼前,衬映在衣香鬓影中,望着他,右手敬上一杯清酿。
他望着她,怔忡间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分明只是一眼,就知道,是她了。
皇兄永征见他代其出征且凯旋而归欲赠舞姬十名作为答谢,他却独独只要了她。
名满帝都的舞姬。
锦宁。
有一泓银烛点于暗室。
深处,三人对立,织成一片沉寂——
“锦宁,你此行的目的,是让永安与吴丞相反目,我便可坐收渔翁之利。”已入中年的大皇子垂着脸,身旁幕帐下绮光的曳金流苏沙沙地抚过肩膀,在跃动的烛光中,泛出冷光。
“是。”锦宁颔首。外人皆以为她是大皇子府的一名得宠舞姬,却没有人知道她师承云照异术师流光,受大皇子所请铲除异己,“只是我一直都不明白皇上素来多疑,为何会在十八年间一直深信吴世观,眼看着势力坐大都毫无举措?”
“这是因为,十八年前术师暮色夜观星相,预言衔玉出生女子必将亡朝,而其时吴丞相长女诞生便是口衔宝玉,皇上一纸诏书要将其沉湖,吴丞相果真依令行事,皇上感其忠义,愈发对其宠信,更是在十余年后将其二女儿吴凝言赐为异姓郡主。”一直缄口的黑衣女子缓缓答道,锦宁正纳罕为何小师妹竟知道得这么多时,大皇子扔过来一把剑:“锦晔,你未免说得太多!”
剑起剑落,锦晔似乎靠着椅子睡着了,鲜红的液体在嘴角蜿蜒,锦宁面对着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师妹渐渐失去呼吸,有片刻的恍惚,恍若回到了多年前师门被诛,唯余二人逃出生天的情形,然而握着长剑的手并没有丝毫颤抖——她的目光久久地落在墙上的画上:“你可不可以将这幅画给我?”
永征有些诧然,但却没有拒绝,那十余年前便入画的自己,意气风发,风华正茂:“锦宁,你知道我为何会千里迢迢寻了你来?”八年了,她渐变成绝美的女子,眼底却永远是灰暗的沉静。
锦宁嘴角抹过一丝笑,看了看椅上逐渐僵硬的师妹尸体,心想无非是因为我对你足够忠诚,即使是自己的同门,也可以如此无情。
但他却只是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永安从未试过在一个女子的琴声中陷入酣睡。
周围是安神的龙瑞脑香,梦境里却蓦然出现女子呼救的情景,就仿佛冷冽的寒潭中囿了一尾小鱼,喋喋细语在胸腔轰然炸响,但永安看不清那女子的模样,似是锦宁,又似凝言,又或者,根本是不相干的另外一人。
脑海蓦然闪过多年前的一桩往事——
“凝言,你没事吧?”她耍小姐脾气,偏偏瞒了家人骑了府中最烈性难驯的马匹出来,他急切追出来,果真看见那踏雪骢将她抛落。
“看你吧,叫你别任性,你偏不信,给我看看,摔怀了没?”他嘴上凶狠,确实极心疼地要替她察看伤势。
“安哥哥。”她目光清亮,双颊着火。
“嗯?”
“你会不会一直对我这么好?”
他笑笑,还未来得及回答,便有一伙黑衣人冲出来,瞬间便掳了她去。
“安哥哥,救我!救我!”
“凝言!凝言……”
“殿下。”仆从在门外声音急切,“郡主病了,丞相请您过府。”
“什么?”猛地一个激灵从酣睡中惊醒过来,永安只顾得上与锦宁说了一声我要去丞相府便跨马远驰,全然注意不到马蹄声惊慌,扬起了锦宁的得意。
坊间盛传皇上将择吉日为郡主与二皇子主婚,而大皇子将锦宁安插在永安身边的目的就在于使得这种关系分崩离析——他不过是要她下一个病咒,使得她有机会在郡主生病期间趁虚而入,而自己,也能事后抚慰美人心,与丞相联手,位登龙椅。
但是她偏偏见过那郡主的相貌——柳眉杏眸,额前一颗美人痣,与自己有七八分相似,其时她才明白大皇子当时的语焉不详。又在永安的梦境中看见他念念不忘的情景,听到他割舍不下叫唤的名字。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女子?为什么偏偏是她,竟能让云照国的两位皇子都对她钟情?
自师父从寒潭中救得自己,锦宁自问这么多年来还从未对男子如此上心,便想起师父常会临潭而立,感慨这世间最厉害的异术非蛊非咒,而皆发于情。
那么,倒不如索性将她斩草除根,也免得自己胡思乱想。
况且,她也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了断这份相思才将病咒变成死咒。
不由得,叵的一声,弦断难再续。
莲瓣琉璃香炉里袅袅散出轻烟,昏迷的女子气若游丝,永安刚迈进屋时就听见丞相夫人低低的啜泣,而御医则在旁捻须沉思道:“怕不是一般的病症,而是中了咒。”
不过是偶尔兴起,踏青归来的当下就忽然晕倒,看似沉睡,内里血液却如火滚烫,最终,便会心力交瘁而死。
吴丞相见多识广,看着御医脸上的作难神色,便知这咒的难缠——“莫非是天要亡我儿?”没来由想起十多年前被下令沉湖的大女儿,又想起十余年来尽管有三妻四妾,却也只存留了现在的小女儿,“莫非是天要亡我?天要亡我?”
“丞相别急!”已近中午,日光正盛,却有影子倾斜而至,众人一看,方才看清是大皇子,“本宫知道,枫蔚堂有佳宝一件,可驱毒挡煞,化风解咒,本宫也想为此事出力,无奈身体向来弱……”
“丞相,就让我去吧!”未等皇兄将话说完,永安出列请命。
“二皇子千金贵体,如果……”
“丞相放心,我向来将凝言当妹妹看,何畏艰险?”说着便已飞身离去,完全没有注意到永征面上的隐隐笑容。
“什么?殿下要孤身夜闯枫蔚堂?”锦宁看着永安急匆匆回来告知一声便提剑就走,又听得仆从无意透露了此行目的,心下一惊,她当然知道这枫蔚堂是玄门重地,里面机关重重,结界密布,心里密密匝匝泛过涟漪,却并不表明。
呵呵。永安笑了笑,锦宁刚到自己身边,自然不知道自当年凝言被人掳去后被送还时一脸懵懂失措,自己便早已暗下决心——此后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一定会佑得她无碍,即使面前的是刀山火海。
“锦宁,你只需知道,在我心中谈得上爱的,唯余你,而凝言,我对她不过是像妹妹般看待。你放心,待我取回宝器,救活凝言,我即刻回来见你!”
锦宁听完这话有微微的愕然,她原本并不知道自己在二皇子的心中有这般重,门外一阵微风,倏忽人已不见。
哎,怎会救得活呢?他不知道自己下的病咒除了本门能解,外界任何宝物都没效吗?
但是她又怎么可能告诉他,自己便是下这个咒,也是唯一能解这个咒的人。
“哼,好自作多情!竟以为我们锦宁倾心的是他?”有声音突兀压住了叹息,锦宁回过神来,永征不知何时已站在身后,拥住她,“放心,永安此去必是死路一条,枫蔚堂向来有得进没得出,不说那件法器是枫蔚堂镇堂之宝,不会出借,就说他能侥幸出得枫蔚堂,我另外派的人也想必能将他,碎尸万段!”
“哦?”锦宁不动声色,“殿下要的不过是帝位,何必要将他置之死地?”
“是他一贯以来都如此骄傲,才给他惹下如今这祸事,当年我与敌军协议,拟将他结果在战场,却没想到他代我出征,又擒回敌首,父皇愈发器重他,这次他更是要孤身一人去取回宝器,哼,我这么多年来筹划此事,每一步都计划精准,决不让自己出半分差错。”他幽幽道来,“十余年前吴府诞下千金,我便收买了异术师暮色,让他指认她必使闻廉王朝灭亡,本以为丞相会因爱女而与皇上反目,我便能坐享其成,可是谁想吴世观那老匹夫倒沉得住气,还真的狠心将女儿沉湖,于是多年后我又将其小女儿掳去,调换作我的人,当然,吴凝言与永安青梅竹马,她也没理由来爱上我这大二十岁的男子,所以我没有让她即刻与永安反目,只静静等待时机,而最近我知吴世观已暗蓄了足够的力量,又最疼这个小女儿,于是便让你下病咒,让一切来得自然而不会引起猜疑,你可倒好,以为我爱的是她而下了死咒,你哪里知道她对我来说不过是一颗棋子,没有她我做事自然要费力些。不过无妨——现在一不做二不休,没有了二皇子,这皇储的位置当然是我的。到时候你便是后宫之首。”
“说道殿下的棋子,其实我自出生就是呢。”锦宁轻轻挣脱他的怀抱,嘴角扯笑,“千尺寒潭中随波逐流,被异术师流光救下,研习异术;却又在你要将暮色所属的目连师门悉数杀绝时投于你门下,自那时起,这盘棋便不再受你控制了——如今我要为自己报仇,替师门雪恨,”说着,指尖隐隐有荧蓝色火焰,“暮色所说吴凝诺必将亡国也未必是假。因为,皇储备选人之一的你确实会死在我的手上。”
就着手上的火焰,她将一幅画点燃:“不错,我确实因爱生妒而给她下了死咒,但是我爱的那个人并不是你,而是你的胞弟,永安。哼,我当日要你的画像也不是来慰藉自己的相思,只不过因为施死咒要用到这幅画罢了。”
“你说什么?”永征愕然,当年见她身负重伤却仍然有力量催动骇人的咒,又见她与吴凝言有几分相似,心想将来有朝一日必能派上用场,所以才救下她,哪里会想到她竟然就是那沉湖的吴家大小姐,吴凝诺。
他来不及痛呼出声,即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惶惶碧空。
锦宁冷冷地看着这一切,想起他刚才所言,遁空而去。
枫蔚堂。
长廊两旁红灯悉数发出轰隆隆的燃烧声,于外人看来,似杀人于无形的口。
叵地一声,两旁红灯悉数尽灭,漫天绯红,有缥缈香气隐隐浮动,永安收手,却仍不敢松懈。
“果真是英雄出少年。”云破月来,树影婆娑,枫蔚堂的女主人戴着面纱,缓缓出现,眸若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