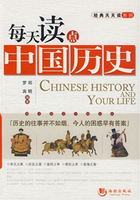“茗莱公主,你的记性倒是差得很呢,你难道忘记这是你亲手给我要我肃清南景乱党,以正朝纲的吗?”千若笑了笑,“你让炎凉下毒害我,所以疏于防范,连这金翅鸟令符早给我的事都忘记了是吧?你虽贵为公主,却从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是一句,还有一句便是‘亲贵不认’,无论是谁,只有拥有这块令符,才可以调遣这令符管辖的军队!也便只要拥有这枚令符,无论是谁,云照公主也好,南景的王子也好,又抑或是我这山野女子,都可以调遣这枚令符管辖的军队!况且,即使没有这金翅鸟令符,当日皇后为我安排下的死士也都在三年前来到景城,为我今日夺回一切而做足了准备。”
那不过百来人的死士,实则都是受过皇后恩惠,在南景军队中占有极大权利的统领。
“你,你……”茗莱还想说什么,一把飞剑已经穿过了胸膛,她看见昔日的贴身宫女蜜珠站在对面,狠狠地盯着自己,“你也是,也是她的人吗?”
不然怎会放过她,现在又来刺杀自己?
蜜珠痛不自抑,吼道:“我本是将你做主子看待,对你也一心不二,然而,你,你却杀了我最爱的人!”
蜜珠最爱的人?是谁?太子么?竟然是太子么?茗莱只觉得脑海一片混沌,方才青君所说的话都只在心底轻轻撩了一下,便沉了下去,然而蜜珠的话却一下下砸着自己的心,她想起他临死前的咆哮——他早就料到了自己的结局所以早于自己心爱的人一步而奔赴黄泉了么?
蜜珠却是哭着摇了摇头:“我喜欢的人,是木四,我们已经约定好,待再过两年,我二十五岁出宫去时我们便成亲!”说着,亦将她胸口那把剑抽了出来,横剑自刎。
一口鲜血喷薄而出,茗莱想起太子死的情景,他那样的男子,到底是为了不能得到她真正的爱而死,还是为了那个默默爱着他的丞相千金而死?她伸出手去,想要够到千若的脸:“千若,你既然是数一数二的易容师,那么你告诉我,我这样的面相为何连一个真心爱自己的男子都找不到?”
连炎凉,都违背了自己的命令,而给千若下了极毒——她知道,不是为她,是因为想要取肃王而代之,能够成为她身边手握重权的摄政王。
没有一个人爱她。没有。
那样的脸,被称作利主的面相,其实如果是有幸登上帝位的话,必是一代英明女君,但若是陷于情爱而不得自拔的话,只能是“妨主“——时刻压着对方,试问哪个男子又能甘心爱她呢?
沉默中只听风声萧萧,她能因自己而放弃夺得南景帝位的任务与野心,无论因着千若“肃王”的身份,还是他本身的性格使然,这一份爱,都让自己承受不起。
而那真正的肃王,在栖霞山与他喝酒时吐露的苦恼,或多或少,也有一点是不堪她那猛如洪兽的爱吧?
千若轻轻地替茗莱阖上瞪着似极不甘心的双眼。
一场搏杀就这样风淡云轻地被解决了。
“真是可笑,南景堂堂的毒神夜叉竟是分毫毒技都没有施展便将这天下收入囊中。”
“哈哈,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施展毒技?你难道没有注意到王城内新植的兰花?那其实是栖霞山兰花的变种,本来栖霞山的兰花就是人间极毒,你们当初在栖霞山遇见的毒雾迷障实则就是那花香,再加上此花生命力极强,每移植一次为防绝种,毒性也增强一倍,所以太子妃暴毙后,仍有不少宫女嫔妃因此而气若游丝,精神恍惚。而大概茗莱至死都不曾想到这一层吧?而这花虽是人间极毒,其花粉却是以毒攻毒的好东西,而每日执帚宫女打扫殿堂,,总是会扬起那些花粉,所以,即使没有蜜珠因木四死在你们手上而想为他报仇才救下我这一层,七日后,千若也会醒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花期已至,错过就太可惜了。”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炎凉猛地一个激灵清醒过来,方才知晓那句话的深层含义。何止是茗莱,即使是自己,也不曾想到青君竟就是南景新一代的毒神夜叉而自己朝夕相对的肃王竟是千若假扮。
若不是那晚在太子寝殿内放下傀儡娃娃意欲嫁祸而看见那枚佩玉的话,连他自己都要以为太子妃暴毙是因为自己下的毒。
“你大概是在昭阳宫的寝殿内放下那东西栽赃太子时发现这枚玉佩的吧?”
一枚玉佩,晶莹剔透,折射着绿色的水样的光泽——南景历代毒神相传的物件,至高毒术的代表。
毒神夜叉,千面般若,两不相离。
如果说青君就是夜叉,那么与她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千若就是易容师般若?
那么现时昭明宫中的主人,便十有八九在三年前就不是真正的肃王了吧?
所以,他才会在看见她只带了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经输了。
“你是云照国太炎世家的人,按理说即使是派质子来南景,也绝不会选你,但二十年前云照毒神带着一个男孩嫁入太炎世家,我亦听我师傅提起——若没有那场与你母亲的斗毒比赛,她也不至虚弱得会被我生母救下——你既然不是太炎家族嫡传的孩子,那么派不派你前来南景对于太炎家族并不重要。”
他点点头——所以才会如此识时务。这是寄人篱下多年后学到的东西。
隐忍,不为儿女情长所动。
“男子总不会为女子付出太多的。”她浅笑着扔给他一瓶药丸,他讶然,“你不杀我吗?”心里存着一丝侥幸,她果真因为自己的识时务而没有杀害自己?而这瓶里的药丸?
“那是你下毒害千若时所中的面目溃烂之毒的解药。”她提裙而去,“即使你做了这么多坏事,我亦会放过你,因为,你是千若同父异母的兄弟。”
男子总不会为女子付出太多的吧?她,她刚才说的话和母亲在世时说的一模一样。炎凉扶着自己的脸,还有她刚才那若惊雷的话语——同父异母的兄弟?
“我师傅南景毒神,和你母亲云照毒神共同的丈夫,千若与你共同的父亲,是南景上一代的千面般若,里杀。”
情爱二字,才是世上让毒神都牵扯不开的至毒。
大景历七百八十年三月,太子泰怀殇,景仁帝禅位,肃王泰泽登基,称景宏帝。
同年五月,废妃甍,景宏帝立女官青君为后,其时礼部大臣持门户之见反对,称皇家血脉不容混淆。翌日太上皇临朝,收青君为义女,称和鸾帝姬,赐婚,不容置喙。又有国师附议,称帝姬身带盛世命格,必将昌典南景。
朝中持异见者渐无。
八月仲秋,国丧毕,景宏帝登基大典,并举行大婚,举国之力迎娶和鸾帝姬。
这一日婚典,青君正在梳扮时忽听见殿外乍然起了喧哗,刚要起身看个究竟,却被一双颤抖苍老的手按住,她摒退随后的看管太上皇的内侍,焦急关怀地将老人扶住,低低唤了一声:父皇。
这些日子来,她用毒技控制了他,先是让他禅位,又让他着议收她为义女,名正言顺成为皇后,早已与傀儡无异。但她怜他越发老迈况且大局已定,便将真相悉数告诉他,又替他解了毒,还撤去了安插在他身边的心腹——本以为他会识时务,却没想到此刻竟来搅局,手里暗自加大了力道——他这一开口,便是惊天的秘密!
然而老人却只是抚着她的脸,眼底满是怜惜与愧疚,恨不能立即赶往奉仪殿亲自主持她与景宏帝的婚礼。
青君在心底暗暗吁了口气——到底是他的骨肉,告知他真相的这一步棋,竟是走对了!
吉时已到,内侍在殿外高喊,她蒙上喜帕,出殿去。
奉仪殿上,邻国皆派了使者携了重礼来贺,连对废后之死颇有微词的云照也送来了一扇七彩屏风,有凤舞动,翼放五彩。
朝臣哗然,这凤虽美,却是在龙之上,龙是九五之尊,凤在龙之上分明不敬,再看那使者,竟是昭明宫原来的统领,云照国多年的质子,炎凉——好一个巴结皇后,趋炎附势的小人。
但皇上却是含笑赞许:“还是炎凉知我心,你虽生于云照,却知我南景为凤神护佑,古书中也是将凤视作南景的图腾的,好礼,好礼,赏!”
其实这本来就是他的主意,他在宫中假扮肃王三年,自然知道云照国有这样一块屏风,与其他皇室物器不一样,是以凤为尊——他其实是想借这一块屏风向青君表明立场,甚至有些近乎于讨好。
“臣躬谢皇上恩典!臣祝皇上皇后百年好合,福运连绵!臣祝南景千秋万代!”
“呵呵。”景宏帝携了皇后之手,大笑道,“炎凉,看来你的南景话倒是学得很好嘛!”
素颜
屋外,云雾缭绕,一团,氤氲不开。
屋内,铜狮香炉似蚌壳开阖吞吐,朦胧迷离的香气,缱绻袅袅。
竹嵌紫檀躺椅上,一个女子奄奄一息,伤痕遍脸,只见一双泡在花香精油中的手,拈起冰鉴镜奁中的一张面皮,仔细地贴在女子脸上。
故事的开头,还得从年初的民间选秀说起。
是为千尘王朝的第十三代传人景薇帝长沐纳娶新妃。
那日,是初晴。素颜刚喝了一碗粟米粥,又在藤椅上小憩了一会,难得的心情好,寻了竹纸与糨糊,小心地站在圆木凳上准备修补前几日因为风雨而破了洞的油纸窗户时,就听见柴扉被推开并毕恭毕敬的“在下沈冰,素颜姑娘在吗?”的声音。
三月的初春,正是满山红杜鹃开得正艳的时候,一男一女穿过烂漫山花前来寻找传闻中的易容师——素颜。
易容,祈梦与蛊,共同称为千尘王朝的三大巫术,虽遭朝廷明令禁止却又屡禁不止。易容虽比不上蛊的凶险,但易使有罪之人逍遥法外的可能性也让千尘王朝历来对其打压至重。但素颜却毫不在意:既是能找到自己这里来,必是有人指点的。
她当天穿了一件月白色的衣衫,襟袖用浮云藤萝作边,站在木凳上,又衬着南方山城的雾霭,显得宛若天人。然而当她的面孔随着声音回转过来,朝向来者时,来者却是惊住了——有着“圣手”之称的易容师长着天底下最普通的容颜,而那张随时会淹没在人群中的面孔又时刻让人百看不厌——不知道这平常容颜的底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一张面孔?又或许,是她早知道今日的见面,随意换了一张脸孔来应付他们罢了?
不过易容本就是秘术,二人并不多言。只见那男子先拿出一个包袱并解开,里面金银一片,接着他又从怀中拿出一张绢画,小心展开,摊在桌案上:“请姑娘照这幅画为我妹妹沈澜易容,薪酬先付一半,三日后再付一半。”
素颜接过那包酬金,并不去瞧画,易容一行也有不成文的规矩:一张脸,只接一次;而除了无中生有的面容外,若是有人拿着画来要求照着此人易容的,画中之人大多不在人间,若是在意,实在是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