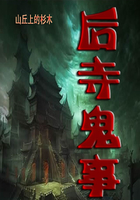手指移到删除键,轻轻一摁,画面就彻底消失了。
拜良关了手机,背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飞机冲入云霄,只落下一片轰隆声和一道长长的航迹云。
旧事,在这稀薄的氧气里,落下帷幕。
我该如何,将此刻的悲喜与你分享。我该如何在这煊赫里,轻轻抹去你眉间那一缕荒凉。
三月。春风乱。柳絮坠。
静默小巷,闭上眼扶着墙沿缓步徐行。指尖凹凸微凉,是淡青暗沉纹理,兀自班驳。不敢睁眼,只怕这荒凉空景,不经意落进眼里,便成了折人噬心的刺,动摇了信念。
即便是身隔沧海,云泥之遥,为你,我亦可跋涉而来。我许你的,不是沧海桑田、生生世世的虚妄。我许你的,便是这一生,这一生所有的流光。
温言软语,犹在耳侧。耀光熠影,历历在目。耀柘,你的这些话语,即便到了如今,我仍是欢喜。只是,它们已落满荆棘。你许的漫长一生,是否便是如此短暂,就在你一个转身间,结束了。
但即便杳无音讯,我依旧笃定地相信着,那日你话语里的真诚:“此生,最幸福的,便是望能如这样几个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锦落,我要你,做我的妻。”
凤冠霞帔,红烛照影。
锦落安静地坐床沿上,聆听着外面喧嚣变化的动静。平西王府的喜事,自是要一番热闹。她的丈夫,则是当在今朝廷江湖皆叱咤风云的小王爷,慕容耀柘。而她却未感觉丝毫的喜悦。只有悲凉,一点一点,渗进骨里,渗进心里。这门亲事,不过是一场交易而已。
父亲获罪,于是锦落选择牺牲自己。但她心里,竟还是有隐隐的期待。尽管,她深知他恨她入骨。她深知这是一场难以辩解的误会。她的身子动了动,挥掉这些无用的情绪。
夜渐渐深去,声嚣也慢慢静寂下来。不时,锦落便听到门被推开的声音,一阵刺鼻的酒味扑面而来。她的心,也随着脚步声的临近,渐渐缩紧。抓着喜被的手,也不觉间加大了力道。
喜帕被猝然揭开。锦落低眉敛目,不敢抬头直视。但她能感觉到,他灼热的呼吸。忽然,锦落感觉鄂下吃痛,头被迫抬起。肌肤相触,摩挲出粗糙的温暖。他琥珀色瞳眸里,放射出冰冷若刀的光。更深处,涌动着千回百折的颜色,复杂得令她无法探究。而他的眉目,依旧那样深艳绮丽,如女子般顾盼嫣然。锦落的心,为之一动。
这样无声对峙良久,锦落终于微微偏过视线,身子轻轻颤抖。如今面对他,竟会有莫名的恐惧。
耀柘却是忽然一哂,放开了她,而欺身向前,靠得更近。他凑到她耳朵边,轻声说:“放心,我不会对你怎样。既然娶了你,本王自然要好好照顾你,不然怎会甘心。”说罢已抽身离开,向门外走去。而那些话如针,狠狠刺进锦落心里,扎得她鲜血淋漓。极力控制,才未让泫然欲泣的泪掉落下来。
她起身敛裙,恭谨地说道:“王爷好走,臣妾恭送王爷。”不愠不怒,得体大方。而耀柘的身影一震,停顿一会,走出了房间。
月光透过窗户,冷清落照,寂淡了这屋子里喜庆的红。
成亲当晚分房而睡,这样的事第二日早已传遍整个平西王府。一时间,流言四起。但奇怪的是,竟无人出来辟止。锦落苦笑,这便是一个下马威。那些下人看着她探究的眼里,隐隐胀满了幸灾乐祸。
而之后的几日,耀柘依然睡在书房。对锦落,依旧是一言不发的冷淡。看着这情势,府里的下人对锦落也越发放肆起来。锦落倒是不在意,每次见了耀柘依旧淡笑行李,不失分寸。但当独自躺在床上时,心中依然流出一声浮云般的叹息。
这晚,已过二更,房间里依旧燃着蜡。锦落披着衫子,望向窗外。这时耀柘依旧没有回来。锦落在等他。不知为何,她要等得他回来,才能入睡。耀柘是知道的,却只是冷笑:“别以为这种伎俩,便可让我放过你。”说完绝然离开。而这席话,说得锦落背脊一僵。那面上的笑,再也挂不住。
忽然,屋外响起了声音,是耀柘的贴身小厮:“主子,爷现在请您走一趟。外面车已备好。”锦落生疑。这么晚了,能去哪里。想问,最后还是罢了。小厮定然是一些客套话便滴水不漏地挡回来,索性随了他去。
马车颠簸了一会,停了下来。锦落在小厮的搀扶下,下了车。赫然眼前,竟是红灯高挂的青楼。丝竹之声,不绝地飘出来。
“爷在里面,主子随我来吧。”锦落略有踟躇,最后心一横还是走了进去。忽然间,那莺歌艳舞,绮香丽影兜头而来,撞得锦落一个趔趄,险些不稳摔倒。牙齿紧咬,嘴唇泛出一片苍白。
他,竟要这般提醒她,羞辱她。而记忆,却是纷至沓来。
锦落初遇耀柘,便是在青楼里。
那时锦落贪玩,竟扮了男装来烟花之地一看究竟。而正巧的是,竟让她遇见夺魁大会。
那花魁虽只是略施粉黛,却是面若芙蓉,丰姿绰约,却又带一点纯真的羞涩。顾盼间,眉目生辉。引得一干人趋之若骛。
出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一百两!”“二百两!”“三百两!”……一时间,喧嚣鼎沸。锦落一时没耐住性子,竟然也跟着喊起价来。她适可而止地玩玩,反正总有人能比自己出更高的价格。而此时,一个喊价却只比她高出一两的差距。这分明上挑衅。
锦落一倔,竟和那人僵持起来。整个场,便只闻两个声音将价不断哄抬。最后,当锦落喊到一万两时,那个戏谑的声音竟戛然而止了。而当一个洪亮的声音宣布结果时,才令锦落幡然醒悟,自己根本没有一万两。
于是她准备开溜,却被老鸨拦了去路,笑里藏刀。锦落看着她渐渐凶狠的表情,一咬牙索性亮了身份。对方现在没料见她会是个女子,都愣在原地。而那讨厌的声音再次响起:“长得明眸皓齿,倒是一个标致的可人儿。既然没钱,不如留下来抵债。”
回转过身,看见一个男子随意立在身后。披着云纹缎面狐裘。腰间南锦淡黄流苏细碎垂坠。纤细指间,折扇穿梭自如。眉目嫣然,仿佛锁着清冷的月华,散出淡淡光辉。这男子,惑如鬼魅,邪如妖灵,偏偏又散发出一股温暖却也出尘的气息。
而面对如此俊美的他,锦落却全然没有欣赏的心情,只是狠狠地盯着他。而他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这时,两个彪形汉子朝锦落走了过去。忽然,那男子腿微微一伸,那两人便摔倒在地。锦落惊讶地看着他。而老鸨此时满脸阴霾:“公子可是要来趟着混水?”那男子不置可否,径自朝老鸨走去。经过锦落时,一阵幽兰的清香随着柔软的声音而来:“你这女扮男装的样子实在差劲。不过我很喜欢。”锦落脸顿时烙出一片红霞。竟被他一眼看穿。
他走过去,仿佛亮了什么东西出来。老鸨立时寒蝉若噤,恭顺起来,立刻对锦落堆满谄媚的笑:“方才得罪姑娘了,还望姑娘见谅。”而那男子转过来,望着锦落笑意清浅。
这场景,早已重放千百次。锦落烂熟于心。而每一次,皆只疼痛。只是,他不明白。
尔后,两人当然是山盟海誓,缘定终身。然,就在平西王府来提亲后不久,锦落家竟然举家搬迁南下。父亲更是要她断了与耀柘的一切往来。仿佛落慌而逃,弄得锦落不明就里。
她不从,倔强地要留下来。最后母亲以死相逼,她只能就范。本是权宜只计,哪知一切早已无可挽回。
南下后不久,就得知耀柘被圣上软禁的消息,说是有篡位之嫌。这时锦落才明白父亲的落慌而逃。篡位,是何等严重的罪名,必定牵连甚广。
锦落望向京城的方向,潸然落下清泪来。她知道,此后必定为他,寝食难安。她竟就这般,抛却了他,辜负了他。
但朝政风云变幻,峰回路转,不时间慕容小王爷就已获赦。而暗中主导这阴谋的势力,被一举掀翻。这次之后,慕容小王爷更是深得圣上信任与眷顾。
锦落欣喜,欲回京去寻耀柘,却被父亲的一席话冷冷地泼了回来:“此刻前去,你认为他还会顾念旧情?你认为他会原谅你的落井下石背信弃义原谅你?锦儿,不要傻了。而且那样的人家,不是我们这样的商户高攀得起的。”
“不,我没有……”锦落听得心惊肉跳,不住呢喃。苏父看着心疼,却无能为力,最后只能一声叹息,说出最残忍的话:“可在他眼中,你就是如此。”锦落颓然跪倒,眼神里一片空落落的绝望。
而不想,父亲最后竟然莫名获罪,被收监关押。多方疏通无路,只能厚着颜面去求她曾经断然拒亲的青梅竹马,沈怒。然而沈怒也是无能为力。最后无奈,她只能寻到平西王府门下。
她仍记得他再次见到她时那种震惊里怒不可遏的神情,仿佛要将她活剥了一般。她却只能忍着心里万蚁啃噬的痛,哀声求他。在情绪起伏叠没后,耀柘平静下来,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不知对峙了多久,就在锦落几近绝望时,他竟然答应了。而条件是,她即刻嫁给他。
锦落望着他冰冷目光里难抑的疯狂与狠绝,颓然低眼,心里一片寂静无声的凄凉空惶。他恨她。他恨她不声不响的离去。或恨她在他最困难时抛弃了他。亦或,两者皆有。
锦落闭上眼,不敢再去奢想未来。那里,早已落满苍白的荆棘。
“主子,请随我来。”小厮的话打断了锦落的思绪。她赶紧收拾心里涌动的情绪,不动声色地越过一池香艳奢靡,来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
房间里,耀柘正拥着这楼的红牌。对她,连一瞥都不曾有。锦落依旧是低眉顺目,安静地站着。仿佛眼前的一切,与她无关。他的风花雪月,根本打动不了她。
忽然,耀柘猛力往地上一掷,酒杯顷刻间碎裂,声响清脆。他挑衅地看着锦落。锦落却依旧如常,不言不语。而那个红牌却自以为是的走上前来,一巴掌就朝锦落呼了过去:“没见王爷正在兴头上吗,哪来的野女人?”尖细做作的声音撕裂了空气,却令随后赶进来的王府侍卫寒蝉若噤。
锦落暗中握紧了拳头。她拼尽全力,才忍住没让泪落下来。而耀柘眯起双眼,渐渐流溢出危险的气息。他看着锦落眉眼低得更深,心里却没有预想的那种快意,反而是一片怒火。
“你是说,我的女人是野女人?”字句清晰,缓慢平静,却让那红牌瞬间跪倒在地,瑟瑟发抖。而耀柘没去管她,拉起锦落便往外走去。指间脉脉的温度,令锦落有一瞬间的恍惚。仿佛身旁的耀柘,依旧是从前那个温柔体贴的他。
刚上香车,耀柘就睡了过去。兴许是太累又喝了太多久。锦落迟疑着,最终将手指落在了他微微蹙起的眉间。她试图想要抚平,却最终没有动手。他时而平缓时而急促的呼吸,令锦落的心一阵一阵地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