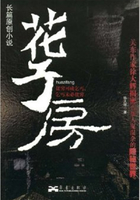秀园她爸说,你进哪间屋都可以,唯独不能进这间屋,再来,我就踢你屁股。我忍了半天,才忍住没让眼泪掉下来,秀园发现我的神色不对劲儿,就问我怎么了,我咬紧牙关就是没吐口,我要告诉她,我叫她爸训了一顿,岂不太现眼了。从此,秀园她爸的那间书房,在我眼里就变成一个神秘的所在,总设想着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前去探险,解开其中的奥妙。
你胆大妄为,我都不敢进那间屋,你竟敢……秀园最后终于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离开涓涓他们这里时,我将一片桃形的树叶夹在书里,当书签用。涓涓姣美的脸庞和黢黑的眸子,常常让我联想起秀园。其实,我总能从不同的女人身上,发现秀园的某个局部的影子。离开涓涓,多少我还有点儿留恋,她也很留恋我们,把我们送出去很远很远。我们没有将我们的截车计划告诉她,怕她担心。黎彩英她们一再对她说,到北京来,一定要找我们。涓涓也满口答应,一定一定。拐了弯,谁都见不到谁了,她们双方才想起,都没给对方留下通信地址。
初次见到涓涓那年,我十七岁,这次再来探访她,我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头发都白了。搭了朋友的车,过了天镇,就多方打听涓涓的近况,却都回答不认识这么个人。好不容易找到个知情人,竟告诉我她早死了,学大寨那会儿,时兴劈山造田,她在炸山时遇难了。我问知情人,她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吗?知情人说,她没出门子,哪来的儿女呀。据说她死时仅仅二十二岁,还是花样年华。问到那个寡妇和寡妇的女儿,谁都说这里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白问了,仿佛寡妇和寡妇的女儿人间蒸发了。我朋友说我,准是你记忆短路了,我说我明明亲眼见过那个寡妇,我朋友说,见也是你在梦中相遇。我真茫然了,点上一支烟,倾听着蝉的呜咽和蛙的哭泣,心绪缭乱,我的眼睛不禁水气濛濛。
拉煤的卡车居然直接将我们送到县城里,可以看见颓败的城门楼子了,卡车才掉头走开。我们徒步开进县政府,一路上见路边的商店字号,还都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之类,江晓彤草拟了一个通告,责令县政府择期将所有带有封资修色彩的村落、街道和商店字号一律改过,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反正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江晓彤嘱咐大家,拿出精神来,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北京红卫兵的崭新风貌。我们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曲,直奔县委书记办公室。没想到在二楼的楼梯口,突然出现了一队奇兵,他们也戴着袖标,也排着队。双方通名报姓,我们知道原来他们是来自太原的,对方说,革命也要讲个先来后到,既然你们来迟了,那就只好去左云或右玉那两个县城。
我们就此拉开架势,展开了辩论,我们坚持就地闹革命,他们也不肯让步,每个人都举着语录,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剑起来。这时候,我发现县委的窗口里探出一张张灰色的脸,心惊肉跳地注视着这场恶斗。黎彩英关键时刻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这样,太原的革命战友负责道南的破四旧、立四新,而道北则由北京来的革命战友负责,兵分两路。两拨人想了想,也只能如此,就都同意了。
回想起当年的景象,确实蔚为壮观,县城的主要的一条干线上,所有的招牌幌子和匾额,撕的撕,砸的砸,烧的烧,附近的居民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却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反对,店铺里的人更是唯唯诺诺,说让他们改名叫“群众照相馆”,他们就叫“群众照相馆”,说让他们改名叫“星火燎原土产门市部”,他们就叫“星火燎原土产门市部”,乖得很。太原那帮小子跟我们较上了劲儿,比我们更嚣张,动不动还踹店员一脚,嫌人家动作慢。县城里的狗都被吓住了,叫都不敢叫,全躲了起来。江晓彤悄悄鼓动我们,卖点儿力气,北京的红卫兵要给地方上的红卫兵小将做一个表率作用。尤反修见江晓彤将药铺的一块牌匾拿斧子要劈成两半,有点儿心疼,说上边是名家书写,一笔好字,留下来吧。江晓彤狠狠地瞪她一眼,你还有立场没有,字好,人不好,该砸烂的也得砸烂。尤反修还不死心,想让我劝劝江晓彤手下留情,我没答应,这会儿除非党中央、国务院亲自出马,不然,谁说他,他也不听。
现在的江晓彤似乎已经醉了,两眼迷离,完全沉浸在破坏的快感当中,嫌热,他干脆敞开了怀。尤反修见我袖手旁观,脸色寒冷下来,不再理我了。一直忙活到晚上,我们的第一战役才算告一段落,这时候,我们刚刚懂得,造反实在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腿肚子都转筋了,走起道来都一瘸一拐的了。县委把我们安排到招待所,并且叮嘱食堂给我们烙饼,款待我们。黎彩英问江晓彤今天感觉如何,江晓彤说过瘾,可是我想到那块起码有上百年历史的牌匾,心里就隐隐作痛,只是不说而已。好歹吃了两口,我就钻进被窝,拿被子蒙上脑袋睡了。这是我打小养成的习惯,到点我一不睡觉,我奶奶就给我讲鬼故事,吓得我不敢把脸露在外头,怕鬼揪我的头发。这时候,杜寿林将我的被子撂起来,叫我起来到城门楼子上联欢去,我问他,跟谁联欢?他说,跟太原那几个小子。我说,我们不是冤家对头吗?他说,不打不成交嘛!我只好起来随他去了,就算是尽尽义务吧。
太原那些人早已点起了篝火,引火的材料就是那些老牌匾,火苗子一蹿老高,稍微不小心,就可能燎掉了眉毛。尤反修坐在人群的最外边,我挨着她坐下,想跟她解释解释,她一见我,闪身躲到一边去了,仿佛我是细菌。两拨人拍着手唱着歌,比谁会唱得多,到后来,还是我们占了上风,我们的歌一首接一首,而他们别说是唱,很多歌就是听都没听过。太原一方大概是觉得输了面子,不想再唱歌了,建议去掘此地一个状元郎的坟,坟上有皇帝老儿给他立的碑,底座还雕了个大乌龟。杜亦她们一听说深更半夜要去掘坟,都惊叫起来,一个劲儿往后退,江晓彤生气了,训她们,亏了你们还是打北京来的,怎么这么缺乏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呢?尽管非心所愿,杜亦她们却不再言语了,我把江晓彤叫到旁边说,让女生先回去吧,她们舒舒坦坦一觉睡到天亮,明天又可以精神抖擞地出发了,要是超负荷了,累病一两个,恐怕就得拖我们后腿了。江晓彤想一想,点头答应了,就让黎彩英带女生回招待所去了。我们几个跟太原那一伙打着火把,向垄沟西边的坟地进发。
这是一次真正的冒险行动,坟地周围一片静谧,只有被惊扰了野鸟呼啦啦地扇动翅膀飞走的声音。坟墓外围环绕着一遭矮树篱笆。大伙儿的脚步都迈得很轻,仿佛是怕扰了谁的清梦似的。我想不光是我,其他人恐怕也是心存疑虑,忐忑不安,只有江晓彤气定神闲,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估计他也是装出来的。我想,这时候谁第一个冲上去谁就算得上是个真汉子了。结果,谁都没挺身而出。都是围着坟墓转圈,不动手。那副战战兢兢的架势,打个极端的比喻说,不像是我们来打鬼,倒像是鬼来追打我们。突然,刷刷刷,从坟地蹿出几个黑影,一闪而过,我们撒腿就跑,跑出去很远,才发现原来那是一窝狐狸。有人说,算了,天亮了再说吧,不然这么大的碑,不用拖拉机拖,怕是也搬不动。众人都点头称是。于是,这次夜间冒险行动也就不了了之了。大伙儿敲定明天带上铁锹等家什再来,并约定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才各自回去休息。
这一天实在累得够呛,我几乎没顾得上怎么想秀园,就呼呼睡去。转天醒来,天已经大亮,江晓彤叫大伙儿抓紧时间收拾,准备出发。我问太原那群人呢,江晓彤说他们早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我们整队,浩浩荡荡地出了县城,竟没有一个人再提起状元坟的事,都把约定扔脖子后边去了。黎彩英她们还一再跟我打听,昨天晚上战果如何,我支支吾吾地说,你去问江晓彤。她们去没去问,问了的话,江晓彤又是怎么回答的,我就不知道了。早晨的空气特清新,吸一口,一股子薄荷味。我紧走两步,跟江晓彤并排,咱们下一站去哪儿?我问他。他面无表情地说,尽管走你的吧,瞎打听什么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大动肝火,估计多少跟状元坟的事情有点儿关系,他这人自尊心最强,我知道。一路上,我们都没再说话,直到半途纳凉的时候,江晓彤过来,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对我说,昨天掘坟时我应该起个表率作用,却没有起,我惭愧得要命……
10
现在的状元坟已经成了当地一个景点。八月,庭院里的紫葳开得正盛,新盖起的祠堂的油漆味和花香混在一起。读了一遍碑文,我才知道这位状元是道光年间的人。赶上高考,当地许多家长都带孩子来拜状元,祈求考出个好成绩。我想我也该拜一拜,就近买了一炷香,敬上。朋友笑我,说我人老了,就什么都信了。我心想,我是感激状元容许那窝狐狸做他邻居,如果不是狐狸突然现身,我和我的那些伙伴指不定干出什么荒唐事来呢。
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朋友身为律师,这两年刚退休,才得以有空闲陪我走这么一趟。那时候,他是个少年老成的孩子,几年不见,变得嘻嘻哈哈玩世不恭了,而且热衷于老同学联谊会,上蹿下跳,也不嫌累得慌。一路上,我似乎没什么话可对他说,他也没什么话来对我说。此时此刻,他闲不住,里里外外地溜达,我则拿着一瓶矿泉水,坐在草地上,兀自冥想:假如,那天晚上,我们真的把状元坟刨了,将会怎样呢?
没有答案。庭院后身种着一架葡萄,枝丫上垂挂着硕大的葡萄,我朋友想跳起来摘一串,我没让,我的朋友问我:“你怎么这么虔诚?”我皱皱眉头。他感慨了一句:“到底是做学问的呀。”不错,我一生用十年的时间研究鲁迅,又用十年的时间研究李劼人,最后的十年研究郁达夫,现在我回头一看,觉得白白浪费了时光,我对他们突然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了,甚至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起这段,更为自己曾为此熬得瘦小枯干而感到不值得。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多地回想起那次大串联,以及大串联中的零七八碎,并且沉浸其中难以自拔。我最常干的事,就是拿个地图,在上边描画我曾走过的地方,画了一遍又一遍。一天,我信步走到长途站,随便上了一辆车,就此开始重温旧梦之旅。走到半道,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是两手空空,一应用品都没带,这才打电话向这位朋友求助,好在他也闲,没犹豫,就颠颠地开车找他来了……
在这座状元坟滞留了多半天,过去的简堂陋舍、残垣断壁,早已是金碧辉煌,建了不少的亭台楼阁,我想,这里恐怕再也容不得狐狸安营扎寨了。想到此,我不由得打了个激灵,招呼我朋友,匆匆离去。“不想照张相,留个纪念?”我朋友问。我黯然地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