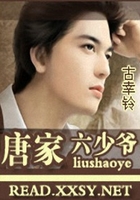清脆掌掴声干脆利落,古晟锦来不及阻止,心因为这记声响抖了抖——
就像在火锅城楼下偶见方樱房柏好像很熟陡然升起的感觉,此时此刻,那种心绪再度攫取住心脏。
错愕看向这幕,立在原地的古滔神情复杂。往事如浓雾笼罩,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疯疯癫癫的女人竟然真是自己这么多年想寻却又不敢寻的苗紫烟。厚重深切的罪孽感像春天里肆意蔓延的藤条紧锁住四肢百骸,淡粉色嘴角蠕动好几回,他却说不出一个字。
右脸颊火/辣/辣的疼,手抚面颊的莫九九并没哭,愣愣凝向脸色苍白眸光惊恐的母亲。
第一个从这种不算僵局的僵局中反应过来,古晟锦顾不得询问父亲怎么回事,疾步上前柔声道:
“我们离开,阿姨…”
“阿九,晟锦,我带你们走,我会保护你们的,我会的!”
许是潜意识里也知道自己从没对女儿动过手,苗紫烟从懵懂中醒悟,闪烁的眼神里有股清晰的恐惧。一边如临大敌的碎碎念,一边抓起他们的手,言谈举止平时都像个孩子的她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生生将莫九九两人拽起朝前走去。并不想拂逆她的意愿导致更糟的情况,古晟锦回头望了一眼父亲。父子俩的眼神在充斥压抑和疑惑的空气里相遇,古滔敛敛眉眼,棱角分明的国字脸上堆满莫名的羞愧。
一路跟随母亲又快又乱的步伐,直到站在古晟锦的车前,莫九九才从一巴掌的震惊和疑惑中清醒。
默默扶嘴里仍在不停念叨的母亲上车,她朝投来关切眼神的古晟锦努力逼出丝笑意,示意自己没事。
“回家,阿九,我要回家…”
蜷缩在车椅一角,苗紫烟瑟瑟发抖,抓住女儿的手因为太过用力而泛出苍淡的白。
所有状况尚未弄清楚,古晟锦只能保持缄默。
无言看了看脸颊窜红的莫九九,他没由来的难过——
二十七年,她究竟怎样一步步走过来?
车子驶出医院,阳光比来时更显明媚。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国际大都市的繁华在各个角落一一登场。难得的好天气,出来活动的人和车都比平日见多。稳稳驾车的他平视前方光与影交错的街道,生平第一次有种茫然无措的彷徨与害怕:
很小就知道当年父亲娶母亲并非情愿,今天这幕让他不得不怀疑父亲和苗紫烟的关系。
假如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我和阿九的相识是缘,还是孽?
耳畔不断传来苗紫烟絮絮叨叨的细念,从嗓音和反应很容易就看得出她处于极度惊惶之中。阿九说她的精神状况一年不如一年,为什么见到第一眼她就能说出父亲的姓氏,并念念有词说父亲会抢走阿九?当年肯定发生过什么,或许是仇恨,然而,比仇恨更可怕的是如果阿九和父亲存在某种彼此从来都不清楚的关系,我和她便有可能是……
一堆毫无章法的头绪在胸口横冲直撞,聪睿过人的古晟锦不敢再往下细想——
此刻的脑海里只有一件事无比明了,那就是害怕万一。
真的害怕。
其实,害怕的并不只是他。
坐在后座噤声不语的莫九九同样陷入空茫无助的情绪,手背被母亲抓出一团团淤红都未察觉。
将不断呻吟的苗紫烟搂入怀中,澈如清泉的眸子不再像平时那般水波荡漾,不安像汹涌泛滥的海水,将她灭顶淹没。母亲竟然一眼就认得出古滔已是大大的意外,最令她惶惑的是母亲最后一句说的竟然是带自己和晟锦一起走。精神状况糟糕的人通常会对一些记忆特别深刻的事并不会完全忘记,如若母亲认定古滔就是充满威胁的坏人,那么,她想保护的不仅只有自己,还有莫名卷入其中的古晟锦。
意识到这点,她的害怕一点点滋生壮大——
还记得周年庆那晚,老妈突然说自己还有个儿子。
公司里,朱海琼又偷偷告诉方佩说有人在议论古晟锦并非她亲生。
这些本来并不存在任何关联,可是,现在一股脑儿涌进脑海,莫九九只觉嗖嗖寒意正在向上攀爬。
假如,假如一切真有某种微妙真实却被掩埋在时光岁月河流中的关系……
她也不敢再想下去。
恰如其分的相遇叫缘,若过犹不及,恐怕就是孽。
一片阳光俏皮的穿过留了条缝隙的车窗,安静躺在墨黑孤峭的左肩。莫九九无力抬头,线条优美的侧脸落入眼帘。时至今日,她记不起自己最初对他的厌恶,也不愿回想某段时间自欺欺人的闪躲,唯一篆刻在心头留下印痕的只有自从相识之后共同经历的美好,以及掩藏在他淡漠讥嘲面具下的温暖。
猛然一阵心疼,她赶紧抿抿唇收回视线,继续安抚受惊的母亲。
窗外的景致和来时相差无几,但是,他们各自的心境却已翻天覆地。
车照样停在了巷口,两人搀扶情绪依然不稳的苗紫烟往里走。
三个人的沉默被“滴”的一声短信提示音打破,古晟锦掏出一看,短信来自常年不与自己联系的父亲:
晟锦,情绪波动对身体有害无益,给她注射镇静剂,再观后效。药和注射器我请人送来,请复地址。
进了院子,苗紫烟飞快跑进房间缩进被子再不肯出来,任凭他们怎么劝慰安抚都无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只能采取古滔的建议。半小时后,果然跑进来个气喘吁吁眉清目秀的年轻小伙。在莫九九和他的协助下,古晟锦将一管镇静剂注入苗紫烟体内。
确定母亲完全入睡,莫九九走到前院,失魂落魄的盯住满院枯败花草。
顺便让送药的男子给父亲带句话,立在院门口的古晟锦转身,幽邃眸光在触及到莫九九时立时温软。
沿着石子小路走回屋檐边,眉宇清隽而肃然的他犹豫片刻,道:
“我约了他见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