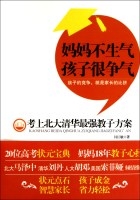“这几个时辰又要审问霁儿,又要决定她的生死,主谋一定会亲自到场。但霁儿如今在城外。”
“所以我们只要查出现在谁不在京城,便知道是谁劫持了小姐!”小浮脑海中灵光一现,她终于看到一缕希望,激动了起来。
乔轩羽并不多说,转身吩咐随从,“立刻去查谁不在京城,先查颜夫人和清裕王,一旦有人不在,我需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随从应声退下,小浮惊讶不已,京城大大小小上百的官员,他难道能够潜入他们的府中全部彻查一遍?
“现在,要不要报官?”小浮忧心忡忡地问道,恐怕乔轩羽寡不敌众。
“不能打草惊蛇。”乔轩羽飞快地否定了她的提议,“况且已经没时间了。”他略一思忖,便回到房间。
宁大人正拥着美人左亲右抱,“乔大人……”他舌头已经不好使了。
乔轩羽不与他废话,径自走过去从他怀中掏出令牌,“借在下一用。”
“尽管拿去!好兄弟,我的就是你的。”宁大人豪爽地一挥手,醉得人事不省,根本不晓得私借令牌是死罪。
“看好他。”乔轩羽对桌边另两个官员说道,两人立刻点头答应,“乔大人放心。”
乔轩羽揣好令牌出来,带上房门便向楼梯走去。
“你去哪?”小浮追了上去,她不可能心安理得地留在这,她也要一起去找颜霁。
“出城。”乔轩羽快步下楼,楼下已有快马等候。
京郊东部有一座城隍庙,久置不用,早已破败。四面的窗户都用木板钉起,冬天里还是渗着寒风。颜霁被押进来,身后有人猛地一推她,她不由跌倒在地上,冰凉的匕首立刻又架在了项上。
她侧耳听着,隐约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刚刚马车转了几个弯她都记在心里,可是她自己知道又有什么用,这么偏远的地方,就算有人要救她,恐怕也寻不到这里。
空气里一片静寂,忽然绑匪们不知接到谁的授意,伸手扯去了她眼睛上的罩子。室内的光线并不明亮,可颜霁还是被耀得眯起了眼。
“姓苏的那个贱人在哪?”一个尖利的声音高高在上,咬牙切齿。
颜霁叹了口气,听到贱人这个词,不用看也知道来者是谁。
“我娘进京,又没有碍到你半分,你怎么就不肯放过我们?”颜霁不解地抬起头,幽暗的灯光下殷璧如脸色阴沉,她的怨气积攒了十几年,早就不知不觉刻在脸上。
“放过你们?”殷璧如冷笑了一声,目光骤然变得阴毒,“谁又来放过我?”
“这么多年,我的丈夫和我同床共枕,心里记挂的却是别的女人!我一直哑忍,只求他能留在我身边。可现在那个狐狸精来了,我岂能眼睁睁看着守了十五年的家就此分崩离析!”
“娘她是来见我的,根本就没想跟你抢我爹。”颜霁争辩着,她们母女好好的团聚,从来没想过招惹别人,殷璧如何必乱担心。
“再说爹也不会离开你。他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不认,也早就忘了我娘。”颜霁黯然道,难过油然而生。她从小就幻想过在父母膝下撒娇,见到苏梦珑之后这个愿望更加浓烈。如果有一天能像千万子女一样,有心事可以跟娘诉说,有困难可以找爹撒娇,可是她知道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美梦,她从不敢启齿。就连这些年自己受的委屈,她也对苏梦珑只字未曾提起。
“不!”殷璧如狂乱地打断她,狠毒的目光中竟露出凄然,“他根本就没忘!你七岁生病昏迷不醒,他在你床边守了两天两夜,你气走二十一个师父,他就不厌其烦地给你请第二十二个,我让你嫁给清裕王,让他大发雷霆,他从没对我发过那么大的火……”
颜霁讶然看着她,不敢相信她所说的话,是她疯了还是自己疯了,为什么这么多年她看到的,和自己完全不同?
殷璧如却好像忘了颜霁的存在,自顾自地说着。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在她心中埋藏了这么多年。如今提起,记忆还无比鲜活,这是刻在心底的伤口,原来从未愈合。
“每年的五月二十日,他都会喝上一壶杏花酒,从不绷着脸。就连晴儿都说,这一天能见到爹一年里最开心的样子。可我怎能告诉她,那是你娘的生日!”殷璧如的声音颤抖着,面露痛苦,往事如一把钝刀,在她心上重复地割出新的伤口。
“不会的,爹从来都没正眼看过我,爹从来都是嫌弃我们的。”颜霁不觉间流下泪来,以为早已不在乎,可她终究还是一个渴望父爱的孩子。
“说!苏梦珑在哪?”殷璧如目露凶光,十几年的色厉内荏让她几近疯狂,苏梦珑就像她心脏中的一颗毒瘤,随时都可能发作,让她日夜不得安宁。
“一切都是你自己幻想,我娘不会踏进相府半步,你有什么不能安心?”颜霁无奈地争辩着,殷璧如像中了邪,非要把她娘当成假想敌,现在竟又绑架她。颜霁看她错乱的样子,恐怕已经失去了理智,不由有些害怕,不敢激怒她。
“你不说是不是?早晚有一天我会找到她,让她受尽折磨而死!”殷璧如恶狠狠地说道,一把揪起颜霁的头发,“你也别想活着回去。”
颜霁心里一凉,殷璧如早就恨她入骨,今天把她绑了出来,恐怕早就打算神不知鬼不觉地弃尸荒野,自己凶多吉少了。她心里暗暗着急,小浮找到乔轩羽了吗,可找到了又有什么用,他们一时半刻寻不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