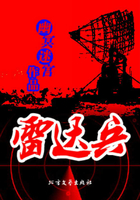“骗子,你有资格对本将说这些吗?”他狠狠掐住她,直到她脸色开始泛起青白,才缓缓松开手指:“你没有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就不要妄想对本将指手画脚!”
没有经历过吗?
她经历的还少吗?
夏清闭上眼,深深吸气,面色变得更加苍白:“你留下我也没用,皇上是不会拿百姓的性命来开玩笑的。”
如果元彻真的将边城布防图交给斛律楚邪,或许她会感动,但她绝不赞同,一个将百姓的生命置于不顾的帝王,不但不是一个明君,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斛律楚邪咬紧牙关,呵呵冷笑,“你忘了吗?本将说过,这一次若捉到你,定不轻饶。有没有做好准备?如果害怕,现在自尽还来得及。”
夏清笑:“自尽?我也说过,不论遇到什么事,我都绝不会自尽。”
“那本将,就一直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死不如生。”
“没有人能困得住我,你信吗?”夏清扬起纤细的柳眉,笑得灿烂。
斛律楚邪双眸微眯,脸上的笑容,既愉悦,且狠辣,他冲不远处的士兵喊了一声,紧接着,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身影,被推了出来,踉跄着倒在地上。
因为对方的脸正对地面,所以夏清看不到他的脸,直至一名胡人士兵,用力抓起那人的头发,强迫他抬起头,夏清才认出了他。
“斛律楚邪,你别太过分!”她猛地转头,如果不是双手被缚,她一定会给斛律楚邪一记响亮的耳光。
站起身,斛律楚邪缓缓走到东郎的面前,一脚用力踢在男孩的腹部,看他痛苦地蜷起身子,这才转向夏清,目光雪冷如刀:“这都是你造成的,因为你撒谎,还教他们学你撒谎,那些人……”他指着地上村民的尸首:“都是被你害死的,你才是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害死村民的人,真的是她夏清吗?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斛律楚邪说得对,是她间接害死了这些村民,如果没有她的出现,他们一定还在平和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必然不用遭受如此灾祸。
是她错了吗?
她根本不该逃走,不该忤逆斛律楚邪,就应由着他肆意折磨鞭挞,丧失尊严与人格。
这样就是对的吗?
她第一次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如果逃走是错误的,那她忽然多出来的一截生命,岂不是错上加错?
“你可知道,本将最讨厌什么人吗?”他忽然大踏步走回来,弯身面对她:“就是说谎的人!他们,本将不会饶,你,本将更不会饶。”对于欺骗了他短暂怜惜的夏清,他有种说不上的恼怒,恨且失望。
夏清不语,她是欺骗了他,她没什么好说的。
既然他要折磨,事已至此,她也绝不会求饶哀哭。
看着她倔强的样子,斛律楚邪兴味顿生,两条长而有力的臂膀,自她身前绕到背后,缓缓地解开捆绑她双手的绳子,期间,他与她离得极近,几乎只要一低头,他的唇就会触碰到她光洁的额头。
手腕上的紧缚感终于消失,夏清却仍旧低着头,默默不语。
斛律楚邪挑起她的下巴,线条刚硬的脸庞,因逆光的原因,而显得沉肃冷峻:“那一下真狠,差点废了本将。这一次,还会逃吗?”他意有所指,夏清看了眼被人踩住双臂的东郎,诚实地摇头。
“本将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他眼中闪着不信,浑身戒备如一只蓄势待发的兽。
夏清坦然迎着他的目光:“既然你捉住东郎,是为了牵制我,我又怎敢再逃?”她挑衅的目光,忽而之间黯淡下来,忍不住朝那些死去村民的尸首望了一眼,顿时一阵窒息。
“这个,还要吗?”斛律楚邪很满意她如今的现状,松开她,从怀中取出一只莹白玉镯,置放在她眼前。
心脏猛地一缩,她别开眼,“你就是凭这个找到我的?”
“也不尽然。”他认真观摩手中玉镯,忽而抬头问:“你们天朝的女子,都这么喜欢戴首饰吗?”他目光下移,定格在夏清的腕间:“本将还是比较喜欢这只血玉镯,想把它送给义妹。”说罢,陡然伸手,一把扣住夏清手腕。
同样的情形,似乎已经是第二次经历,然而,性质却完全不同。
夏清以左手护住手腕,将玉镯护起:“对不起,这只镯子并不配你的义妹。”
斛律楚邪不肯松手,唇角弯起的笑意,冷得决然:“你的命,和这只镯子,选一个吧。”
夏清也笑,却笑得淡然轻松。
她说:“好。”话落,褪下玉镯,猛地站起身,用力砸在坚硬的岩石上。
霎时,红色的碎片四散飞溅,有些落在地上,有些擦过夏清的脸颊,割出细小的伤口。
上一刻,还流盈夺目的玉镯,下一刻,便成为了无数零散的碎片,孤零零落在脚下的土地上,与鲜血的颜色融合在一起。
“你疯了!”斛律楚邪愤怒地看着满地碎片。
“斛律将军,这就是我的选择。”夏清同样看着一地碎片,神态却安宁沉静。
肆虐的风吹拂着,撩起夏清鬓侧的发丝,她眼神如水,话语如冰。
“你的选择?”沉肃汹涌的暗流,盘桓在二人之间,斛律楚邪猛地抓住她一只手腕:“宁可毁了,也不要本将得到吗?”
“是。”夏清看着他的眼,轻轻道:“中原有句话,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将军听说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