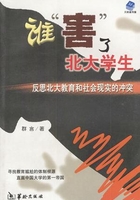关于我和哈文的婚姻,请打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您猜,您猜,您猜猜猜!
一边猜,我一边继续夸我老婆。
我们俩很互补。
论体质,中医说,她阳刚气重,我相对阴柔——说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却是事实。比如我胆小,甚喜恐怖片,看了又怕得要命。
“老婆,求你了,醒醒,陪我看会儿!”夜里,我拿被子半蒙着脸,使劲儿捅她。电视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正从井里往外爬。
“烦不烦啊?我明天上班呢!”她闭着眼,恼火地一抡胳膊。
“就一会儿,关键时刻,求你了。”我不依不饶,连拉带拽。
结果一个字:扁!
论生辰八字,我们相互对应,她有矛我有盾,最适合搭伙过日子,并肩作战。我负责闯祸,她负责收拾残局。
论星座,我的太阳星座是金牛,月亮星座是白羊,她恰好反过来。总体形势是我管赚钱她管花,我为五斗米折腰,她视钱财如粪土。
论性格,她爽快,男子做派;我矫情,脂粉气浓。我们俩一起出门,她梳洗打扮只用5分钟,我捯饬50分钟都不够。
论处世,我举轻若重,她举重若轻。我爱拧巴,她看得透。我除了录节目没别的事儿,当我的宅男,还老睡不着觉。她每天8点准时上班,一脑门子官司,可是从不失眠。
最近,她对我最大的褒奖就是:“李咏,你不纠缠了。”
纠缠怎么讲?我爱钻牛角尖。想当初《咏乐汇》刚刚上马,编委会全体通过,热烈鼓掌。长官给我一系列承诺:考虑制播分离、公司化运作……本来前景描绘挺美好,“李咏工作室”指日可待。哪想牛年的正月十五一过,一切都变了。我这叫一个闹心啊,吃了几个月的舒乐安定。
有一天哈文实在看不下去了,找我谈话。
“你最开始做《咏乐汇》,是指着它发财吗?”
“不是。”
“是指着它扬名吗?”
“不是。”
“你是特在意‘个人工作室’吗?打着你李咏的名号,成为众矢之的,让别人看着眼红?”
“不想。”
“那不就完了吗?该干吗干吗去!”
说罢起身,拿起卧室里一尊一男一女纠缠相拥、名为“爱情”的木雕,“蹬蹬蹬”走进浴室,往洗手台上一放。然后扭身回屋上床,抱着笔记本看她的《24小时》去了。留下我一人在那儿咂摸滋味——这艺术品,有收藏在浴室里的吗?
有个对人特高的评价,叫明心见性,说的就是我老婆。我这是拧巴什么呢?明明啥也没影响,啥也没改变。要怨就怨我自己,非把那6000点没来得及抛的股票算成户头里的既得资产,弄得好像赔了老本儿似的。
可能,就是那木雕闹的,纠缠。
哈文很有管理天赋,一来她大公无私,永远一碗水端平;二来她尊重导演,不干预创作过程,只关心结果。她立的规矩叫“导演中心制”,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组里的导演个个比她这个“领导”工资高,关键时刻,谁也不掉链子。
我不提倡做人玩儿“阴谋”,但“阳谋”可以适当地搞一搞。我们两口子在节目组开会的时候有个阳谋,就是假装吵架,拉开了架势地吵。
为啥?借用个舶来语:脑力激荡。
长官管我和哈文这样的组合叫做“夫妻店”。他说,中央电视台多几个我们这样的“夫妻店”会更好,前提当然是我们干活儿。但夫妻店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显得太强势,开会时弄得年轻人不敢说话:挑拨我们俩等于找抽,只听我们俩说,又不够客观。所以我们琢磨出这么个办法。
我提出方案A,坚持说A好,说得天花乱坠。
哈文提出B,在吹嘘B的同时使劲儿踩估A,公然挑衅。
我又奋起反抗,钻她空子,还挑动群众,“你说!同意我还是同意她?”
“我觉得把你们俩意见综合一下就挺好。”少来!和稀泥的话蒙不了我,说你自己的主意!
底下群众一看,非常可乐啊,打头的都吵成这样,吾等小字辈还有甚放不开?马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C、D、E、F、G一揽子方案火热出炉。
这就对了嘛。我和哈文偷偷相视一笑,阳谋得逞。
在工作中,不管发生什么状况,哈文都主意挺正。事儿都是人盘活的,她就属于这种人。
说心里话,我欣赏哈文,不仅欣赏,而且佩服。但要论私心,我真不希望自己的媳妇儿到了40岁,还在为工作受委屈,挨辛苦。每天按点儿上下班,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人和事之间平衡来平衡去。对她来讲,这固然是发挥所长,但咱又不是阿甘,犯不着“就是喜欢跑步”。
“媳妇儿,你是救火队的啊?升官的事儿咋从来不找你呢?”
哈文一瞪熊猫眼,“又能吃多大亏?”
得,算我觉悟低。
对了,刚才我出了个谜面,谜底您猜出来了吗?
恭喜您,答对了:满族。
李氏父子
我爹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他永远默默地在电视报上划出所有我的节目,到点儿必看,不管重播多少次。烦人的是他光自己看还不行,非拉着我娘一块儿看,一遍都不能落下。
我爹今年快80了,生活规律,身体健康。每天下午5点打开收音机,躺床上听点儿小道消息,吃完晚饭,按时收看《新闻联播》。除了这点儿事,就是担心我,仨孩子里就我爱兴风作浪。
每当听说有关我的负面消息,他就很恼火,跟我辩是辩非。不管我怎么解释,我爹都是这一句:“你怎么就这么不省心?怎么就不能向人家罗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