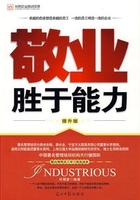十四阿哥意识到自己弄痛了我,于是马上松开搂住我腰间的手,改去扶我的肩膀。“怎么那么不小心……”只听他口中小声喃喃。
唉,我无语了。
我本是打算坐下的,可是,按照我现在身体的状况是不允许我这么做的,而且,刚才一路走回房,我已是精疲力竭,两脚打飘,所以,在站和坐都不行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趴着,在床上趴着。纵使我这样的行为很不合时宜,或者说是于礼不合,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下午还必须洗很多衣服,眼下要养精蓄锐。
我刚在床铺上躺下,舒心地吁了一口气,一道身影也利索地跟着翻身上床,躺在里侧,如入无人之境。
十四阿哥一气呵成的动作把我惊愣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这……这好像是我的床吧。但又转念一想,我似乎根本没有计较的资格。这整座皇宫都是他爱新觉罗家的,何况是洗衣房里的一张床?成,他十四爷爱躺就躺,躺哪儿都随他高兴,我管不着。
“听说你被人打了。”十四阿哥两手枕在脑后,望着屋顶的天花,口气淡淡的。
“十四爷的消息还真灵通。”我脸朝外讷讷道。敢情全世界都知道我被打了二十大板?还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呐。
“伤得严不严重?”十四阿哥的言语里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关心。
唉……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二十大板啊,您说严不严重?
“我瞧瞧。”见我久久不说话,十四阿哥干脆坐起身,作势就要掀我的裙子。
他想干什么!十四阿哥毫无顾忌的举动着实把我吓得不轻。“不行!”我惊叫,直觉就往床外躲去,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碰。
“啊!”谁料我这么一闪躲,人在床沿扑了个空,重心一歪,整个身体就直接向床下滚。
要命,这下肯定摔得伤上加伤,不痛死才怪。掉下床的一瞬间,我悲哀地想。
然而,预期的疼痛却并没有来光顾我的身体——男人的手臂及时地圈住了我。
“不让瞧就不让瞧,用不着那么激动。”十四阿哥把我捞回床上重新趴好,听他的口吻,好像做错事的人是我。
我激动?!我怎么能不激动!心底刚冒出的一丝丝感激,刹那间灰飞烟灭。我一个姑娘家伤在那种地方怎么可以随便让男人看的!
再说说,我这一身的皮肉伤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你四哥赏的?为的,不就是我走了霉运无巧不巧撞见你那个当皇太子的二哥和洗衣房里的宫女乱搞男女关系!
可能是一直以来压抑得太久,而十四阿哥的话就像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眼眶一热,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
为什么找上我的总没好事?想起之前遭遇过的那些事,我越发觉得自己凄惨,眼泪越掉越多,终是哭得稀里哗啦,又是泪水又是鼻涕的。
一条手绢垂在我眼前,十四阿哥皱起眉头看着我,脸上尽是嫌恶的表情。“丑死了,拿去擦擦。”他别过脸,对我眼涕交纵的脸惨不忍睹。
我一听,觉得更伤心了,不客气地扯过他手里的手绢,重重擤了一下鼻涕,边哭边大声抱怨:“我为什么不能哭?这里吃不饱,穿不暖,成天洗不完的衣服,还要随时挨板子,就连哭……都要被人嫌丑!”
这里根本就是地狱,丝毫看不见希望和光明!不让我哭,我偏偏就是要哭!
哭着哭着,眼睛无意中瞥见十四阿哥右手掌大拇指和食指间的胯口上有一抹暗红,我猛地止住了眼泪。
“怎么不哭了?”
哭声蓦然停止,十四阿哥转过头,神情不解。
“你的手怎么了?”我抽泣着问。
十四阿哥不以为意地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伤口,轻描淡写道:“早上骑马练箭的时候,不小心给弓弦割的。”
我抹抹眼泪,支起身,伸手取过放在床头的木盒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小药罐和一卷白布。
“想不到你这里的东西还挺齐全的。”十四阿哥挑了下眉毛,自认很有幽默感地调侃道。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也没征得他的首肯,便直接用手指从药罐里蘸出些药膏,径自在他的手掌上涂抹。伤口不大,却伤得很深,还在往外渗着血。“这叫百病成医,十四爷一定听过。”药膏和白布都是我处理自己的伤口时用剩下的。
“这是你的?”趁我抹药的当口,十四阿哥也没闲着,另一只手执起我胸前的玉佩,放在眼前端详。“挺精致的。”
我微微一愣,这玉佩一定是刚才我滚下床时从衣服里掉出来的。我没有说话,只是从他手里拿回玉佩,塞进内衫里藏妥当后,低头继续为伤口裹上白布。
十四阿哥失笑,笑我的幼稚:“我只是看看,没想抢你的东西。”
“谁知道……”我含糊咕哝。
在白布的尾端打了个节,把药罐和多余的白布放回木盒子里,我又重新趴回床上,经过刚才的一场大哭后,心里觉得舒服多了,虽然屁股还是疼得要命。
“你说我们这算不算同病相怜?”十四阿哥举起被包扎好的手掌朝我摇晃,漫不经心地笑着。
“呵……”我被他的模样逗笑,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十四阿哥呀,总有让人又哭又笑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