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我是看你这小姑娘不错才勉为其难的让你叫我一声哥哥的,一般人想叫我还不让呢!”说着说着叶净那玩世不恭的架势又端出来了。
卢瀼一副敬谢不敏的表情,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谢谢哈,我想您还是不要勉为其难的好!”
“行,那我就不勉为其难的让你叫我一声哥哥!”
“怎么样,我这次是心甘情愿的。”
“快点叫一声我听听,来么?”
卢瀼听着这话咋就这么别就捏,怎么听都好像是一欺行霸市的恶少调戏一良家妇女时才会说的经典台词。
终于,忍无可忍无须再忍:“叶净,你别逼我把今天晚上吃的这一桌子东西用另一种更容易消化的粉碎式的物理形态还给你。”
“真是,我又不是什么青楼头牌,你丫装毛火山恩客呀!”
“比猪后鞧上的肉还腻歪人。”
话说思想一向不是很纯洁的某人,在说这番话时思想是前所未有的纯洁的,比甲醇还纯来着……
卢瀼没有让叶净把自己送到小区,而是在离家小区五百米的一个公交车站下了车。
原因无他,今晚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她需要散步消消食。
五百米,卢瀼走得格外珍惜,可无论多长的路,任凭你怎样放慢脚步,总还是会有走到头的时候。
走到小区门口,门卫的胖大爷看见她朝她打招呼:“回来了。”
“欸,您还没休息呢!”
“快了,这就休息!”
话音刚落,就听见身后‘嘭’的一声巨响,整片天空照亮了,五光十色的烟火让原本清泠的天空瞬间流光璀璨。
卢瀼站在那里,仰着头看着一簇一簇炫目的烟火,笑得像个傻子:“大爷你看,那边有人在放烟花。”
“是啊,这不年不节的咋还有人放烟火呢。”胖大爷嘀咕着。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烟花。”小时候卢瀼家住在城郊,离市区很远,每次市里放烟火奶奶因为年纪大都不能带她去,这样一来她就只能看着被烟花染亮的天空一角,和闷隆隆的炮声。记得那时,她曾无数次的憧憬过真正的烟花该是多么的流光溢彩。
但当真的看见时她还是忍不住震撼,那样的绚烂,却又是那样的悲凉,它比彩虹还要瑰丽却还不及萤火虫来的持久。
流光的盛宴在天空的舞台上缓缓落幕,凉风拂过,卢瀼这才感觉到了冷,拢了拢领口,正准备转身上楼,肩头突然被一只手压住。
卢瀼还以为是叶净尾随她回来了,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发生一两次了,于是她也没怎么害怕,把那只手毫不留情的拍下去:“干嘛,还贼心不死呢,告诉你门都没有,切!还哥哥呢,姐姐我看还差不多。”
吊儿郎当,是她对叶净的一贯态度。
“卢瀼,你给我回头看清楚我是谁!”
天崩了,地裂了,小花猫不见了,主啊,你敢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么。
“幻听,幻听幻听,幻听幻听幻听。”卢瀼一边加快自己的脚步往前走,一边自我催眠着。
但有时现实总会让生活万分无奈,就像现在,当顾北辰鲜活无比的杵在卢瀼的面前时,卢瀼的所有催眠都无效了。
“真是巧。”卢瀼觉得今天想以喜剧告终是不能够了,但她要试着用正剧的形式结尾。
“你不请我上去喝杯茶。”今天的顾北辰穿着一件浅灰色双排扣风衣,米色长裤,双手插在风衣兜里,相当的绅士风。
汲着路灯,卢瀼能看见他脸上浅浅的笑意,没有了之前的颐指气使看起来倒是显得有几分孩子气。
“我没有什么好茶,恐怕都不会和您顾先生的口味。”不管是偶然还是刻意,她都不想和眼前这个男人有过多牵扯。
“没有好茶白水也可以,你总不会小气到连一口水都要计较吧。”顾北辰看着强自镇定的卢瀼,笑得越发无害,他是真的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怎么会怕他怕到这种地步。
卢瀼看着实在是推不掉了,咬着牙心一横,连连笑着说:“怎么会,我是怕顾先生贵人事忙,在我这耽误了宝贵时间就不好了。”
这女人,还学会倒打一耙了,明明是她不待见自己现在反倒成了她替自己找想了:“不会,我晚上有的是时间。”
“呵呵。”卢瀼干笑了两声,“是么?”不等顾北辰再说什么就朝着楼里走去。
顾北辰也没再说什么,凭着个子高和腿长的优势几步就追上了卢瀼,走到楼道门口时卢瀼停了下来,从包里拿出随身带着的手电筒。“啪。”的一声把开关打开,一道白光瞬间将漆黑的楼道照亮。
“你看着点脚下,贴着墙这边走,千万别去扶楼梯,有些把手已经松动了,还有的钢筋被人撬走了,很危险的。”卢瀼在前边走,还不忘细心地给走在身后的顾北辰提着醒。
“这怎么连个声控灯都没有?”顾北辰长这么大还没进过这样的地方。
“三四十年前上那安声控灯去啊。”卢瀼没好气的说。
卢瀼住的这个地方是六十年代初a市修建的第一批七层暖气楼,原来是一处政府大院,后来大院里的住户外调的外调,升迁的升迁,大多数的房子就空了出来再后来这个地方又成了某事业单位的家属房,前几年主要市区整改旧房棚户区改建的时候这里本来是要拆迁的,可这块地的使用权归部队,地方没有审批权,就这样,拆迁重建的计划一拖再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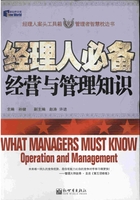
![[茜茜公主]贵女启示录](http://c.dushuhao.com/images/book/2020/03/23/21142513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