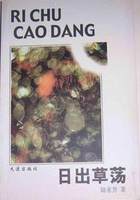阴冷逼人的暴室,四处结满了青苔和蛛网,几处槁木在风中呜烟,没有灰雀,也没乌鸦。义妁和赵婕妤紧挨着,蜷缩在阴暗而潮湿的一角,对面的女囚已经昏睡,睡在一堆干草之上,旁边放着一只破败的便桶,那股弥漫于囚室的臭味就是从便桶中散发的。
赵婕妤大哭一场之后睡了过去。义妁把目光停留在女囚的身上,猜测着她的身份,女囚突然醒了过来,女囚抬起了头,那是一张被屈辱和仇恨扭曲的脸,义妁不寒而栗。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女囚突然冲了过来,似乎对义妁暗中打量她感到极为不满,女囚冲到了义妁的面前,义妁猝不及防,一下子就被女囚拖了出来,女囚的力气之大令人不可置信。义妁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女囚狠狠地摔在地上。义妁想爬起来,腿却痉挛了,一点力气没有。
“你,你要干什么?”
义妁半个身子躺在地上,声音瑟瑟发抖。
女囚什么话也没说,脸上挂着狞狰的笑,突然抱起一条破烂的褥子蒙住了义妁的头。
“叫你看!叫你看……”
义妁挣扎着,叫了一声:“娘娘,救命……”
声音就微弱下去了,义妁被褥子蒙住了头,呼吸急促,女囚又拿出吃奶的力气勒紧了她的脖子,似乎要把义妁勒死。
好在这时赵婕妤醒了过来,看见女囚发狂的举动,不顾一切冲了上去,奋力扯开了女囚,一边扯一边骂:“你这个疯子,你要干什么?!”
义妁把褥子甩开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差点就窒息而亡了。
女囚的手向赵婕妤的脖颈伸来,赵婕妤抓住了女囚的双手。女囚挣脱出一只手来扯住赵婕妤的头发,赵婕妤疼得尖叫了一声,也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不要命了似的伸手去抓女囚的头发。可是怎么抓都是那么几根,而赵婕妤已经被女囚弄得披头散发。赵婕妤变换了策略,扑向女囚,企图用身子把女囚撞倒,女囚眼疾手快,紧紧地抱住了赵婕妤。赵婕妤也趁机抱住了女囚。就这样女囚和赵婕妤势均力敌,僵持不下,谁也动弹不得。
义妁的腿脚不再痉挛了,她站了起来,冲了过去,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女囚的手掰开了。女囚跌倒在地上,突然狂笑不止:“哈哈,哈哈……”
赵婕妤紧紧抱住义妁,因为恐惧而痛哭起来。
义妁拍打着赵婕妤的后背,泪流满面地安慰她:“没事了,娘娘。没事了,娘娘……”
此时的女囚却“哎哟,哎哟”地叫了起来。
义妁望去,只见女囚坐在地上,双手不断按揉她的膝盖,脸上有疼痛难忍的表情。
义妁放开了赵婕妤,向女囚走过去。
赵婕妤在背后叫唤:“义妁,你要干什么?”
义妁走到女囚的旁边,蹲下身子,好心地问:“大婶,请让小女给你把把脉看看。”
其实义妁知道女囚得了骨痹,为她把脉是想知道女囚是真疯还是假疯。
“滚开!臭丫头!”
“大婶,小女是侍医。”
“侍医?”女囚抬起了头,脸上的表情有些惊讶,随即又用嘲弄的口吻说,“如果你是侍医,老娘就是皇后。”
这确实是疯子才敢说出口的话。
“本宫可以证明她就是侍医。”赵婕妤忍不住说道,又劝义妁,“她是疯子,不要管她了。义妁!”
女囚斜睨了一眼赵婕妤:“你又是谁?”
义妁替赵婕妤答道:“她是赵婕妤赵娘娘。”
女囚狂笑了一声:“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
“这是什么意思?”
义妁越发觉得女囚并没有疯,疯子不会有那种复杂的眼神,她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什么秘密。
女囚并没有回答义妁的话,义妁不再追问,再次请求为女囚把脉。
“请相信我,我可以治好你的病。”
女囚将信将疑地伸出了手。
义妁把完脉,暗惊,女囚果然是伪装的,不是真疯,而是假疯。可是她为什么要装疯呢?义妁陷入了疑虑,但没有立刻戳穿女囚,不动声色地说:“你得的是骨痹,是受了湿邪所致,由于小女无法拿到汤药,现在只有一个法子能治好你的病。”
“什么法子?”
“请大婶跪下来。”
“什么?!”女囚惊怒道,“你竟然侮辱本宫……”
“本宫?难道你是皇上的……”义妁大惊。
女囚一时激动说漏了嘴,改口道:“臭丫头,竟然要老娘向你下跪,你反了不成?”
“小女只是让大婶跪在褥子上行走,将气血引入你的膝盖,并非让大婶向小女下跪。”
女囚把头扭向一边,气呼呼的,不再理义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