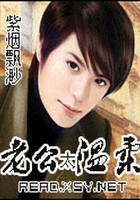如此的标致男子,谁见了都会怦然心动的,何况我这个乡下姑娘呢?我妄想着,只见他又说了一声:“姑娘,你没事吧?”他等了我半天见我一直盯着他的脸目不转睛地,不由得有些惊异,最后又似笑非笑地问我,我这才清醒过来:“哦,公子,你快请进来!我去叫家父去!”刹那间,我的脸一片绯红,一路小跑着高声地直唤着屋内的老人家出来:“爹!大哥有书信回来了!”
老人家在屋里听到我的喊声,兴奋地步出屋来:“什么,元郎有消息了!”“是啊,爹!这是大哥托人送回来的书信,女儿说的梦没错吧!果真有应念了!”我欣喜着,把信塞在爹的手里,倒把身后的送信人给忘却了。可他却没有埋怨,只静静地站在我身后,看着我们为远方亲人而欢呼。“我该对他们怎么说呢?”见我们如此的上心,他高兴不起来,脸上止不住地颦眉叹息,并不时地抚摸着腰间别着的一支骨箫。
“是谁带来的书信?”爹高兴得四处寻找送信人,我这才想起了身后之人,忙把他引荐给爹:“就是这位公子送来的,他也是大哥的同僚!”“是吗,我看看是谁?”爹高兴着,朝着他上下打量起来:“不错!一表人才!请问公子贵姓啊?”爹眯缝着两眼,笑嘻嘻地看着来人,把他看得怪不好意思的。“老伯、今顺道来拜访贵舍,我姓陈名琪,与孟元兄同属关宜将军麾下。”他向爹一供手,毕恭毕敬的说道。“好,谢谢你送来孟元的家书,陈公子,孟元在边塞可好啊?”
“孟元兄吗。”一见爹问到大哥,他就面带难色,而爹又催得急:“难道孟元不好吗,又惹是生非,又打架了?又,”爹连珠炮式的发了一大通的话,惹得陈琪接连摆手:“孟老伯,你误会孟元兄了。”“你不懂,我就说他是憋不住性子的------”可爹哪里肯听,他深知大哥是个管不住的主。最后把陈琪急了:“孟元兄不是这样的人,您老还是先看看书信吧。”听到这些,爹才猛然想起:“对,我都忘了,我儿写的信,女儿快给爹拆开念念。”我撕开书信,怦然可见一行行苍劲有力的字迹,显然不是哥的手书,他连自己的姓名都写不好,何以写家书呢?我还差点忘了哥临走时的情景,那一日他整装待发,一边想上战场上跃跃欲试、一边又对家人恋恋不舍,还对我唠叨个不停:“妹子,哥写不好字,就不写家书了,每日见好就画个圆圈,表示哥平平安安,大家都团团圆圆,好不。”“好,就这样,哥,记得常画圈圈啊。”我望着他宽阔的脸庞,调皮的说道,并目送他到道上,直至了日落西偏,人影遁去,我才返回了家中。那就是我的大哥,虽然有点莽撞粗鲁,但不乏报国的的热忱以及对家人的承诺。而且不管他到了何地,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些思乡的影子。
“爹、妹子,吾于边关一切安好,现托军中同营陈琪兄回乡探望,望爹见谅。”
不孝儿:孟元 书
我念到,寥寥数语间,尽显了大哥对家的一片真挚之情。可当我念毕,爹却意犹未尽,还想继续听下去:“芙儿,怎么就这些啊,你大哥也太简练了,没说啥时候回家啊?”见爹这般渴望,我也无法,大哥的书信就只写到这些:“是啊,当初哥连字都写不好呢,现在这已经很不错了。爹有什么要知会的,还是问问这位陈公子吧。”我朝着面前的这位陈公子笑道,爹马上就拉起他的手,急切地问道:“陈公子啊,我家孟元有不有说何时归家啊?”
“这个。”陈琪的话出嘴边,又退了回去。见他这般犹豫,爹实在按捺不住心情:“你倒是说话啊,他何时才能回家一趟啊?”看着孟老爹如此迫切的眼神,陈琪只好说道:“孟元兄现在位居校尉要职,军务繁忙,暂时脱身不出,看近年关之时有了假期再回吧,还望您老体谅才是。”听到他这番解释,爹才转忧为喜:“好好好,现在孟元是官阶在身了,我们也不便打搅了,只要他在边关平安无事就好了。”爹喜笑颜开,今天没有比得到自己儿子的消息来得更高兴了,于是他抱出了陈年的佳酿,并吩咐我杀鸡宰鸭,好好地款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
接下来的爹极尽所能,将家里所有的珍藏都堆上了台面,几乎摆满了一大桌的丰盛菜肴。虽然这里地处偏僻,但不乏民风淳厚,直至了杯盘皆空、酒缸见底大家方才尽兴。而陈琪再经过一番推杯换盏之后已不慎酒力,摇晃着身躯想站起身来告辞:“老伯,酒宴已毕,天色不早了,我就此拜别了。”他满面见红,话还没说完,身子就不支地滑倒在桌子下面,昏沉沉入睡了。只惹得爹一阵开怀拍笑:“说你不要逞强吗,你偏不信,不知深浅地还跟我喝五大盅;还好这不是三十年的陈酿,否则你小子非睡个十天半月不可,哈哈哈哈------”爹开心地笑着,从新又拾起了他的酒坛子,继续着他还未完了行酒令:“夜长天、风烟起、角鼓号、一梦归西望------”声音苍凉而浑厚,宛若行进的军歌,而地上的青年已酣睡正浓,恍惚间又梦回到了那个风雪连天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