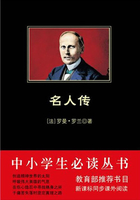“主上和娘娘正值春秋鼎盛,如此?”我探寻的望着吴尚宫,以期她能给予更多的消息,“即使两位上殿隐退,”吴尚宫欲言又止,她明显已觉着自己说的太多了。
不知何时卢尚膳已站在我和吴尚宫的身后,一双三角小眼半眯着:“吴尚宫,看来我们也得准备归隐之处了。”他的脚步声可真轻,我在心里暗暗揣夺道,像一只轻手轻脚的狐狸。
“尚膳大人,听说您的养子姜内官早已准备好随时接替您的位置,这归不归隐,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吴尚宫倒是言语直白,丝毫不拐弯抹角。
“啧啧啧,话不能这么说,”卢尚膳在笑,阴阳怪气的在笑着:
“您这么恼火,又这么不安,无非是后继无人罢了,您洒在东宫的种子,白白的浪费,倒不如留在身边,出仕宫中女官之路,兴许还能走得更长久,吴尚宫,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
吴尚宫微微抽动了嘴角,自是有些难堪,很快她打叠起笑容:“三殿尚宫,素来以大殿为尊,大殿尚宫岂不比我这个中宫殿尚宫更为忧心,如此看来,我倒还真是乐得丢开手。”
“姜到底是老的辣,”卢尚膳咂了咂嘴皮子:“这个时候,我们两个老人家在这里耍嘴皮子,”他转了转眼珠,目光虽然扑朔,其眼神却并不迷离,他像是不经意的瞟过我一眼。
“尚膳大人,娘娘,奴婢先退下了,”见此情景,情知是我在这里碍事了,遂微微欠身,“郑尚宫越来越聪明知事了,”卢尚膳的声音尖细:“用不了多久,您就不会再向我等弯腰行礼。”
纵观朝鲜开国历史,曾发生过三次禅让事件,之后所有王权的更迭俱是国王身后之事。定宗和端宗皆是迫于形势,是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为求自保不得已将王位禅让予王世弟太宗和世祖大王。
而太宗则是唯一一位在世的时候,将王位禅让予世子的国王。
依据吴尚宫所说,看来严宗是将效法太宗大王将王位禅让于东宫殿下,我提起笔有些犹豫,想必此刻天大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传回宫廷,如此不过是多此一举。
宫庭里嫔宫披着唐衣走匆匆走出纱帐,借是晕黄的烛光看完书信,迅速掷在香炉里;
奇尚宫衣衫单薄,她只穿着中衣,双肩冻得微微发抖:“娘娘,这件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权利一项集中于宫廷,为什么是在小小的温泉郡?”
嫔宫紧盯着香炉,直到书信渐渐化为灰烬:“此次离开宫廷,绝非是温行这么简单,难道是要试探东宫的忠诚?”她蹙着两道远山眉,百思不得其解:
“主上虽命领议政何琼直接向东宫禀报政务,然兵曹和吏曹这样掌握着军队和人事的实权仍由主上牢牢控制着,不应该啊。”
她有些烦燥,在寝殿来回踱着步子,素练的群摆如晨霜扫于明黄色的地板,“娘娘,您是否应去谒见东宫大人?”奇沙宫已沉不住气,她的双颊冻得殷红,如香炉内的明炭。
“不行,殿下为了王内官的事情,心中已与我存了芥蒂,”嫔宫驻足,她扬起泠泠的凤目:“这个时候去,他只会愈发厌恶我。”
奇尚宫摆摆手,一幅不以为然的样子:“坐在一条船上,难道还为了一个鼓子(内侍的俗称),置身于危险之中?”
嫔宫从水翁里拾起一把忍冬,捧在手心里深嗅了一口气,她仰起头,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
“太宗大王当年禅让出王位,是在废掉前世子的情况下,拥立了世宗大王,世宗大王坐上宝座,领相沈温,难道?”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不,不可能的,应该不至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