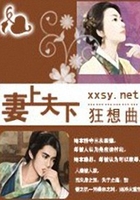尽管宫廷传得沸沸扬扬要废除徐氏君夫人之位,却自敬妃醒来后一连数日,都不曾有教旨颁布,敬妃经过十来日的调养将息,已能站起身,由吴尚宫与我掺着,在中宫殿外的院子里小步走走,活动筋骨。
暖暖晨光中,敬妃的精神影儿分外清明:“连日卧病在内殿,可我把这把老骨头给闷坏了,”吴尚宫皱纹丛深的眼角堆起笑意:“奴婢这心呀,到了此刻才算是落了地的石头,踏实。”
敬妃蕴着笑意,轻轻拍着吴尚宫的手:“有你在,我就是闭了眼,也没什么事不放心的,”“娘娘切莫再让奴婢受这样的惊吓啦,奴婢也是有了春秋的老婆子,”
吴尚宫略板起脸,一幅满是不悦的样子,倒令敬妃打叠起言语开解她:“罢、罢、罢,一会儿喝那难喝的汤药去,省得你拿脸色给我看。”
我二人正要扶敬妃回到内殿,却见恭嫔领着徐氏,姑侄二人都穿着素服,两人伏在地上行大礼:“请求中殿娘娘,治大不敬之罪。”
敬妃扬起下巴,冷漠的望了望恭嫔身后的徐氏,一言不发,搭着吴尚宫的手转过身。
内殿里,吴尚宫接过药碗,我奉上手帕,给敬妃擦了擦嘴角,即使是在病中,敬妃仍是很讲礼仪的,她小心的吃药,嘴角只浸了些药汁,这便是出身名门世家闺秀的风范,到底是出生不同。
吴尚宫陪敬妃聊起家常:“娘娘,荣源府院君大人前日进宫请安,那神情,见到娘娘,老泪纵横啊!”敬妃歪在抱枕上,未免有些心酸:“自我搬进这中宫殿,府院君离开都城,距离我越来越远了。”
“府院君都已是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了,也不知道主上这一次召他回来,是否能让他多些时日留在都城,”敬妃摇摇头,叹了口气:“听主上说河城府院君也请求回到都城进宫问安呢!”
吴尚宫将手拢在唐衣里,一脸好奇:“哦,那么主上恩允了吗?”“我劝主上让金大监回到都城,自嫔宫嫁入宫廷后,他离开都城已有七年了,七年来不曾返家过一次,也够有违人伦的。”
敬妃转着念珠:“唉,世人都道皇亲国戚,却不曾知,外戚们若当不好,甚至连身家性们都保不住。”她半眯着,花白眉的毛微微颤动:
“昭宪王后的父亲,曾被太宗大王赐了死药,母亲沦为官婢,直到儿子登上王位,才予以平反,为了宝座,为了王权的稳固,只能任妻子的眼睛含恨流血。”
“这在本朝自是不会,主上最是英明,如此安排,令王室与戚臣们都能和睦呢!”吴尚宫软言开解道;看来越是有家世背景,越是令龙椅上的君王坐立难安。
原来,主上即提防着敬妃娘家的势力,也牢牢遏制着嫔宫娘家的势力,所谓将金正翰留在身边做同副承旨,也应是一种操控。
渐渐的,对于宫廷的人和事,我能够慢慢想到更深一层,又或者,因为接触到了权利,对于政治,已有一种觉悟。
“娘娘,恭嫔娘娘与君夫人跪在殿外呢!日头这么大,足足有半天了,”吴尚宫终于坐不住,讨敬妃示下,敬妃转过身,面向里侧闭养息,
如此,吴尚宫再不言语,她极力保持着平静,而嘴角却泛着冷笑。
到了用午膳的时刻,宫人们正要抬进膳桌,恭嫔张惶的闯入内殿:“娘娘,您听小妾说上一句,君夫人,不,顺凤这孩子,她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再这么跪下去,恐怕就要一尸两命了!”
“什么?”敬妃与吴尚宫顿时面面相觑,我闻言亦是一阵错鄂,敬妃自是扶着吴尚宫的手去看徐氏,她二人刚离开内殿;
恭嫔昂起头,之前的张惶倾刻不见,她的菱唇泛起狞笑,毫不介意,我还留在内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