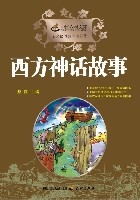看来,吴医生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尽管我赶到医院时,他正巧又被院长叫去开会,但他让吉医生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以前我对他讲过,医院里如果发生有趣的事或有什么有趣的人,让我去接触接触,搞写作这行,脑子里得装满奇事才行。看来,这吴医生够哥们儿。
吉医生给我们介绍后就走了。这个叫做龙大兴的27床的病人望着我,似乎要从我的白大褂上看出什么破绽似的。我不像医生吗?不,连这里的护士也说,我穿上白大褂的样子,至少也是个主任级的专家。当然,这也许有点恭维我的意思。
我沉住气,对着这位病人说:“我上次在花坛附近见到你时,你正念念有词地往前走,你当时看见什么了呢?”
“记不得了。”他说,“清醒后是记不得病中的所作所为的,只有半清醒的时候所看见的东西才能记住一些。”
“你看见过什么呢?”我问。
“唉,不说那些了,都是假的。吴医生说过,那是幻觉。可当时却像真的一样。我老是看见红旗,医院里的墙啊树啊什么的,我有时看去都是红色的,还在飘动。每当这时,我心里就很激动,我忍不住要到处走,有几次都走到了一个悬崖上,我伸头往下一看,天啊,崖下躺着一个女学生,已经死了。我感觉是我把她推下去的,于是又惊又吓,忍不住大吼大叫。吉医生说,每当这时都给我注射镇静剂,我睡过去后才会忘记这些情景。”
我望着这个五十多岁的病人,略微发胖的身体表明他住院已经很久了。我说:“听吴医生讲,这些都是你在‘文革’中的经历沉淀下来的东西。都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些东西怎么还会缠着你呢?”
“咳,我也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我便常犯这毛病,这医院进进出出,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太深了吧。我那时刚读大学,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儿。武斗期间,我有两支枪,可威风了。晚上睡觉,我的枕头下也放着一枚手榴弹。为啥?防止对立派组织攻进来嘛。如果遭遇突袭,也不能束手就擒,实在不行了,伸手往枕头下一拉,嘿嘿,同归于尽,这才是好样的。唉,那时的日日夜夜可精彩了……”
说到往事,这个病人的眼中开始放光,很兴奋的样子。
“你打死过人吗?”我突然问道。
“没,没,”他连声否认说,“武斗时双方对着楼房什么的对射,子弹都打在砖墙上,没伤着人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幻觉中曾出现过一个女生死在崖下的画面,我想探寻这与他的经历有没有联系。
想到死者,我突然问道:“这里以前有个叫严永桥的病人,你知道吗?”
“噢,”龙大兴仰起脸回想着,“个子高大,三十多岁,是搞桥梁建设的,对,他叫严永桥,以前就住我隔壁的病房。唉,偷跑出去干什么呀?黑灯瞎火的,在高速路上被车撞死了。”
“他为什么要逃跑出去呢?”我问。
“这就不太清楚了。你知道,我多数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清醒的时候,在走廊上我听他说过,他没有病,他早就该出去了。”
这时,吉医生走进了病房。他附在我耳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吴医生开完会了,叫你去他那里。”
走出病区,我沿着走廊向吴医生的办公室走去。走廊的顶部是拱形的,显得安静肃穆。一百多年了,这座法国人留下的医院几经整修,原有的面貌得以保存。走廊一侧的窗户很大,上端是半圆形,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将夏日的阳光隔离在窗外,只有些斑斑点点的光影洒在走廊上。
此时,我已在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应该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我必须弄清楚严永桥从住院到死亡的全部真相,这样才能解开那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之谜。况且,我现在住在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那个握着黑雨伞来拜访我的人搞得我日夜不宁。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如直接住到这旋涡的中心来。
“这事情有点麻烦,”吴医生听到我的想法后,说,“以前有搞电影电视的人在这里待过,结果搞得很不愉快,院长很生气,说是搞写作的人再不接待了。”
我说:“以朋友的名义,你跟院长通融通融吧,就说我要写的东西绝对正面,救死扶伤、精神关怀等等,只住上一两个月就行了。”
院长姓蔡,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当吴医生将我带到他办公室后,刚说明来意,他便看也不看我,对着门外吼起来,“写作?我知道你们的意思,精神病院嘛,铁门!大锁!把人关起来,像监狱一样!哼,就冲着这个来,就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蔡院长为何发这样大的火。我赶紧声明我对精神病院的理解,说这里所做的是一份崇高的工作,面对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让我钦佩,所以想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以便写出真正感人的东西来。
蔡院长似乎没听我的解释。门外有人叫他,他便径直出去了,将我和吴医生留在他那显得很大的办公室里。
我正不知所措,吴医生拍了一下我的肩头,说:“咱们走吧。”我说:“这事怎么办呢?”他笑了笑,说:“这不已经同意了吗?蔡院长就这习惯,只要他没明确否认,就是表示已经同意了。”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经过一片草坪,就是吴医生所负责的病区了。这幢两层法式楼房此刻有一半被遮在树荫下,另一半暴露在阳光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明暗交错的风景画。
吴医生说:“院长虽说是同意你待在这里了,但你只能在我负责的这个病区活动。这里的底层是男病区,二层是女病区,在这个范围内,你可以以新来的医生的名义走走看看,与病人交谈什么的,都可以。但晚上最好不要去病房,因为天黑以后,有的病人病情发作,怕伤着你。你知道,有的躁狂型病人发作起来是很厉害的。”
我想起了二楼尽头的那间黑屋子,董枫就是在一个雷雨之夜看见里面突然有了烛光的。并且,在这间长期闲置的病房里,那夜的烛光中还出现了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尽管吴医生将此事解释为是董枫的幻觉,但我总觉得另有蹊跷。此时,吴医生对我的告诫是对我的关心呢,还是暗含警告?
不管怎样,吴医生对我的写作还是很支持的,不然他不会同意我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以便在龙大兴这样的病人中搜集写作素材。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永桥死而复生地到我家拜访我,这事实让吴医生也无法解释。现在他让我住到医院里来,也许是想与我联系得更紧密些,以便为这个谜团找出答案。
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成了我的临时住处,一张小床、一张简易写字台和一把木椅就是室内的全部家当。吴医生说,这是他上白班午休和上夜班时休息的地方,现在提供给我了。凑巧他这段时间不上夜班,所以夜里我可以独自享用这个空间。
我说过,这幢法式楼房里全铺着老式的地板,我在这小屋里哪怕轻轻地走动,地板也会发出咚咚声。不但如此,屋外的走廊上,包括不远处医生护士的值班室里,只要有人走动,我在这小屋里都能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如果距离稍稍近点,还能感到地板的轻微震动。
我突然想到,严永桥逃离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就是踩着这样的地板溜出去的,怎么没人发现呢?
吴医生正为我整理这小屋里的一些凌乱东西,听到我的疑问后,他说:“那天我没上夜班,听值班医生讲,他是趁医生查房打开了病区的铁门后溜出去的。从病区出来到楼外,根本不经过值班室这一段走廊。”
我哦了一声,想着这楼房的布局:进门后往右是医护人员值班室的走廊,往左是通向病区的小铁门,正中间是一道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的女病区。
“不过,”吴医生望着我,说,“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精神病人逃出医院的事发生过不少次,生生死死也见了不少,但死后又出现的,还是第一次听说。要不是被你遇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当然,理论上说来,人绝不可能死而复生。因此,你遇到的严永桥是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起了在严永桥家里看见的遗像,他绝对就是撞进我家来的那个人。我知道吴医生心里其实也很困惑,但是,这一切现在确实无法解释,我只好点头同意吴医生的判断。我说:“但愿那是另一个人。”
这天晚上,第一次独自住在精神病院里,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有点莫名的紧张。吴医生回家去了,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我还不熟悉,也就没出去乱窜。躺在这小屋里的铁架床上,我想到了我家里的寂静,那个供我独自写作的居室现在应该是一片漆黑。我得离开它一段时间了,如果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再次登门,他会发现那里已暂时无人居住了。
我突然产生了往家里打一个电话的念头。我知道电话就在我的写字台上,如果此时铃声大作,没人的屋里也可趁机热闹一下。
抱着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我在这医院的小屋里向家里拨通了电话。天啊,电话刚一拨通,就有人拿起了电话,我听见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喂,喂!”我冲口而出,“你是谁?”就在这一刹那,那端放下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