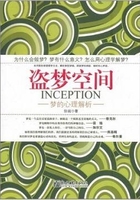菲利普叫醒了我,跟我说布露奈特的情况。昨天夜里,他还看过它,它的呼吸还很均匀。
可是,从今天早上起,它的状况就变得很糟糕,让人着急。
他在它面前放了干草,它不吃。
于是他为它割了很多鲜嫩的青草,在平时,那可是布露奈特最爱吃的。然而现在,它却连碰都不碰一下。甚至,它连自己的小牛犊都不看一眼。小牛犊站起来,伸着脑袋想要吃奶,用鼻子乱拱,它觉得很不耐烦。
菲利普只好将小牛犊拴得远远的,不让它打扰妈妈。布露奈特似乎压根儿就没注意到这回事儿。
菲利普来回踱步,他的不安情绪传染给了大家,连孩子都想起床了。
兽医来了,人们把布露奈特牵到了他面前。它被门槛绊了一下,身子撞到了墙上。它看起来随时都可能摔倒,只好把它拉回牛栏。
“它病得很重,”兽医说。
我们大气都不敢出,甚至不敢问它得了什么病。
他担心她得的是产褥热,这种病经常夺去牛的生命,特别是良种奶牛。他回想起那些人们已经放弃了希望,但他又将它们救活的病牛,于是取出一个装着液体的小瓶子,用一个小毛刷蘸着液体在布露奈特的奶头上刷。
“这是一种发疱药。”他说,“这是从巴黎弄来的,里面的确切成分还不清楚。如果病毒没有蔓延到脑子,我就能用凉水疗法治好它。普通农村人看到这种疗法可能会大吃一惊,不过我知道我在同谁讲话。”
“那就按您说的办吧,医生。”
布露奈特侧躺在草铺上,抬头都变得很勉强。它停止了咀嚼,似乎在屏住呼吸聆听别人讨论它的身体状况。
它的犄角和耳朵都发冷,人们于是拿了一张羊毛毯子过来,盖在了它的身上。
“等到耳朵耷拉下来,”菲利普说,“就有希望。”
布露奈特想要站起来,但失败了。它又挣扎着试了一次,最终放弃了。它的呼吸越来越沉重,呼吸间距也越来越大。
它的头一下子歪了过去,撞在了自己的左肋上。
“病情恶化了,”菲利普蹲在地上,半天说出了这么一句。
它又抬起了头,却一下子撞在了食槽边沿上,发出了巨大的响声。这一下撞得太重了,大家都被吓了一跳,甚至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
我们在布露奈特的身子底下又垫了一些草,使它能够更舒适一些。
它趴在地上,脖子和四只脚都伸开了,就像大雷雨到来时趴在草地上的样子。
兽医决定给它放血。但是他离它有些远。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医生,不过胆子却有点小。
几木槌下去,柳叶刀扎到了血管。他又用力地敲了一下,血一涌而出,流到了锡桶里——那只锡桶平时都是装奶汁的。
布露奈特的身子开始放松下来。我们找来一块布单子,用冷水浸湿了之后,盖在它身上。布单子很快便发热了,得经常换。它躺在那里一动都不动。菲利普紧紧地拉住它的角,免得再撞到左肋。
布露奈特温驯地有些可怕。它究竟是好了些呢,还是病情加重了呢?我们丝毫都不知道。
大家都很难过,菲利普显得更加忧郁。看他的样子,简直就如同自己在受苦一样。
他老婆给他端来了早餐,他就坐在一张踏步梯上吃,甚至都没吃完。
“完了”他说,“布露奈特胀气了!”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有些疑惑,但菲利普说的是正确的。布露奈特的腹部眼看着就胀了起来,而且不再憋下去,仿佛空气进去之后便不再出来了。
菲利普的老婆问:
“她死了吗?”
“你看不出来吗?”菲利普的口气十分生硬。
“我还要去看看另外一个,离这儿不远。”菲利普说。
“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布露奈特。”
“我喊你的时候你得过来。”我用了一种主人的腔调说,这连我自己都感到诧异。
我们费尽力气地让自己相信:布露奈特死了。与其说是烦恼,不如说是我们被激怒了。布露奈特真的死了。
晚上的时候,我遇见了村子里教堂的打钟人,不由自主对他说道:
“喂,我们家的布露奈特死了,我给你一百个苏,请你为它敲一次丧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