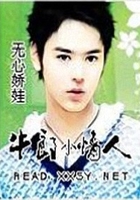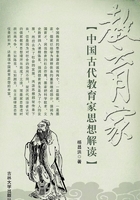这回闯入眼帘的依然一堆做工考究的金丝楠木架子,但这次堆放的不是木匣子,而是一个个八仙桌大小的圆竹匾。介于先前的经历,余然在原地踌躇了好一会,才迈步向前,探头一看,她愣住了。
一条条浑身上下白色,大约七八公分左右长,像大青虫一样的软体动物在竹匾里蠕蠕滚动。
“原来是蚕!”
余然恍然大悟。那之前看到的应该是没有孵化的蚕子。她脑子里回忆起余奶奶给她讲过的年轻时养蚕的事。说如果那年早春天寒的话,就得把那些布满蚕子的纸片,用丝绵包好,放在贴身的肚兜袋子里,用体温来孵化。记得当时她听得是又恶心又发痒,实在难以想象,人怎么能把虫子贴身揣着睡觉?而且不是一只,是一堆。后转念想想,在奶奶那个时候,这些都是家庭生活的来源,是她们的宝贝,观念不同,对待的方式自然也不同。心里也就释然了。
撇撇嘴角,余然瞅了几眼密密麻麻拥挤在一个竹匾里的蚕,转头打量了下四周一层层搁放在架子上的竹匾,看着一竹匾一竹匾五颜六色的蚕宝宝,她忍不住长吁一口气,忽略脊背处麻麻痒痒的感觉,转身离开,前往下一个屋子。
一边走一边嘀咕:“这些蚕宝宝的生命力可真强!没有人喂食桑叶,竟然还能活到现在。它们的颜色也真漂亮,好像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的颜色一一俱全。”
没几步路,余然走到下一间屋子,根据先后的顺序,她笃定这间屋子里堆放的是蚕茧。推门进入屋子,还是一堆金丝楠木架子,上面堆满了纸做的匣子。余然上前拿起一个瞅了一眼,些许惊艳之色浮上。
太奇妙了!这世上,竟有红色的蚕茧。只见白色的匣子四角,各自结了一个泛着微微红色光泽的蚕茧。
忽地,余然想起刚才那间屋子里五颜六色的蚕宝宝,小嘴微张,一下明白过来。心道,这倒好,什么颜色的蚕宝宝,结什么颜色的茧子,省去了将来染色的功夫。
接连看了几个纸匣子,余然恋恋不舍地离开,心里盘算着,等绣艺成熟了,来拿这里天然的彩色丝线绣东西。只是,这样得天独厚的丝线,要配同样材质的绣布才行那?她想想家里学习用的绣布绣线,抿抿嘴角,目标遥远,还需努力。
八十年代,物价低廉,市场上几乎没有假货,做生意的人都比较实诚,但那时候月收入也不算高,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
走到门槛前,余然回过头,深深地凝望一眼堆叠满纸匣子的金丝楠木架子,重重地叹口气,坚定地关上门离开,前往下一个屋子。
来到门口,有了前几次的经历,余然不假思索地推开门,果然同她想象的一般,特制的木架子上,套满了一绞绞色彩斑斓的丝线。一眼瞧过去,眼花缭乱,震撼至极。
“不知道在阳光底下晒丝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绮丽景致?”眨了好几下眼睫毛,才勉强缓过神来,余然走上前,伸出手,指尖碰触到丝线的霎时,她停住了,心里一阵惶恐,摊开双手,仔仔细细检查了好几遍,才安下心来,抚摸一绞绞挂在光滑的架子上的彩色绞丝。
“真是太美丽!要是奶奶也能见到这些,该有多好?”
余然睁大双眼,赞叹似的自言自语。她不知道,这个乞巧殿是不是只能由她一个人进出,或是能够带其他人一起进?就算能带其他人进,余然也不敢带。不是她私心太重,而是像乞巧殿这样奇妙的东西,一旦泄露到外面,难保不会给她和奶奶带来杀身之祸。
她暗自决定,这个秘密宁可烂在肚子里,带进坟墓里,也不能告诉其他人。最多是把这里的丝线带出去用。
推开东侧偏殿沉重的殿门,一间类似于古代书房布置的屋子映入余然的眼帘内。
她在门口踟蹰了会,跨进殿内,走到用紫檀木精雕细镂的博古架前,伸手拿下一块好像刮痧板一样的薄玉板,盯着看了好一会,凭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学后世流行的玄幻修仙小说里般,将薄玉板轻轻贴住额头。
霎时,脑子里涌入海量的信息,庞大的信息量立马折腾得余然头痛欲裂,痛吟不断。
她忍不住蜷缩起小身板,躺在冰冷的水磨石地面,满地打滚。
滚了一会,余然实在痛得受不了,握紧小拳头,爬起来跪在冰冷的地面,拼命将头撞击坚硬的的石地,企图以痛止痛,不一会的功夫,白皙饱满的额头淤青一片,渗出丝丝鲜红的血液,汗水几乎浸透了她全身,如果现在给余然把刀,她保不准会拿起刀将脑袋一劈两半。
也不知过了多久,剧烈的痛感如来时一样陡然间终止,余然整个人像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死狗,四肢平摊着躺在地上,小脸惨白,无神的凤眼瞪得老大,小嘴张开,呼呼的喘着粗气。
乞巧殿是织女的全部家当,现在余然所见到的部分,不过是乞巧殿的千分之一大小,要想要成为织女的传人,乞巧殿的真正的主人,余然就得修仙。
修仙的第一步是洗筋伐髓,用具有洗髓效果的丹药或仙果将人体内的杂质排除干净。
余然休息了会,动动酸软无力的手脚,见四肢稍稍有些力气了,赶紧一鼓作气爬到博古架前,撑着博古架站起,眼光一溜,看到贴有洗髓丹便签的白玉小瓶,打开瓶盖,一丝勾人的清香扑面而来,她深吸一口气,倒出瓶内拇指大小的一粒丹药,丢进口里,囫囵吞进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