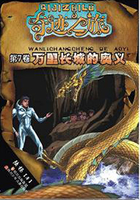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他说:‘嗯,我就是知道它是一个酒桶,我以前就见过好几百次了。他们说它是一个被诅咒的酒桶。’
“我把其他的守卫叫来站在我旁边,然后我把狄克说的这件事告诉他们。现在它在我们的正前方漂浮着,并没有到我们这里来,离我们大概有六七米远。有些人说把它捞上来吧,可是其他人并不想。狄克说冒犯过它的木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守卫长说他才不相信呢,他说他觉得这个酒桶往我们这边来是因为水流的关系,它会渐渐离开的。
“于是我们又继续说着别的事情,唱歌,然后休息。休息过后,守卫长又唱起了另外一首歌,然而现在天空乌云密布,水桶依然漂浮在那儿,歌唱声也似乎没有办法把气氛带起来。后来大家又试着扯些闲话,有一个人说了一个笑话,但是那笑话实在一般,甚至连说故事的人都没笑,真是不寻常到了极点。我们都坐了下来,看着酒桶,心中没来由地焦躁不安。它仍然浮在那儿。突然间,起了一阵狂风,接着雷电交加,眨眼间暴风雨就接踵而来。木筏上有一个人在逃跑的时候颠了一下,摔倒在地上,扭伤了脚踝,大家都摇着头。而每一次当有闪电的时候,酒桶旁边就会闪着蓝光。我们一直看着它,后来天快亮的时候它就漂走了。当天亮的时候,我们到处都找不到它,当然也不会觉得惋惜。
“但是第二天晚上大概9点半时,当我们唱着歌,气氛很热烈的时候,它又回到了原先的地方。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一句话也不说。人们什么也没做,只是坐在那儿看着它。天空的云又开始聚集了,当守卫换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立刻去睡觉,也都跟着守夜。暴风雨肆虐了一整晚,又有一个人跌倒扭伤了脚踝,必须躺着休息。天亮的时候,酒桶又离开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明白它的去处。
“接下来的一整天,大家都显得清醒安静,我说的并不是那种不喝酒的清醒——并不是那样。他们很安静,但是喝酒喝得比之前还凶——并不是一起喝——而是各喝各的。
“天黑后,交了班的守卫并没有进来睡觉,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更没有人四处闲逛。他们都靠在一起,在那儿静静地坐了约两个小时,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同一个方向,不时地发出叹息声。突然,酒桶又出现在老地方,它整晚都在那儿漂着,没有人睡得着。午夜之后,风暴又来了,天空一片漆黑,大雨滂沱,还夹杂着冰雹,雷声怒吼,狂风肆虐,而闪电照亮了一切,使得那木桶的身影清晰得如同白天所见一般,河面被闪电照着,如同牛奶般洁白,绵延好几英里,而那酒桶依然浮在那儿。船长命令守卫去掌后桨,因为快到渡口了。可是没人敢去——他们说不想再扭伤脚踝了,他们甚至不肯走路。就在这时,闪电将天空划开,劈死了两个守卫,还使另外两个人受了伤。你问怎么受伤的?当然是扭伤脚踝啊!
“在天快亮的时候,那酒桶又在雷电交加之中消失了。可想而知,那天晚上没有人吃得下饭。饭后船上的人四下散开,三三两两地低声谈话,但是没有人和狄克坐在一起,他们都给他脸色看,如果他走近他们,他们会立刻分头散去。他们不想跟他一起摇桨,船长把所有的帆都收起来放在帐篷边,不肯把那些尸体运上岸埋葬,他不相信水手们上了岸还会再回来,而他说得也的确没错。
“夜晚又来临了,很明显,如果那酒桶又回来的话,就意味着又有麻烦到来——大家都私下讨论着。有些人想要杀了狄克,因为他以前就见过那个酒桶,而且他长得很难看,有些人叫他滚上岸,而有些人说如果酒桶再来的话,大家就一起上岸吧。
“这样的耳语暗中传播着,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寻找酒桶的踪迹。突然间,它又出现了。缓慢而平稳地从上游漂下来,又回到了它的老地方。四周安静地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于是船长走上前说:
“‘兄弟们,不要像一群白痴一样,我可不希望让那酒桶一路跟我们到新奥尔良,你们也不想吧?那么,阻止它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烧了它,就是这样。我要把它拖上船。’在大家都还来不及表达意见的时候,他就跳下河去了。
“他游到酒桶那儿,把它推向木筏,木筏上的人都退到一边。船长把它搬上木筏打了开来,里面竟然有一个小孩!没错,一个赤裸裸的婴孩。那是狄克的婴孩,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没错。’他上前靠在酒桶上,‘没错,那是我可怜的死去的孩子查尔斯,’他结结巴巴地说着。他说他以前住在这个河的上游,有一天晚上小孩大哭大闹,他不小心把他闷死了——这可能是个谎话——后来他害怕了,把孩子放在一个酒桶里,在他太太回来之前出了门,向北边走,当起船夫来。这已经是酒桶跟着他的第三年了。他说这个厄运开始来时总是很轻微,直到死了四个人之后才会罢休。他说大家如果再忍一晚——像之前一样——可是大家已经受够了,他们打算乘船把他带到岸上,对他处以私刑。然而他突然抓住了那个小孩,流着泪,紧紧地把他抱在胸前,跳入河里。而我们这辈子再也没有见过他和他的小孩了。”
“谁在哭啊?”鲍伯问,“是狄克还是那个小孩?”
“当然是狄克啊。我不是跟你说那个小孩已经死了吗?死了三年了怎么能哭啊?”
“嗯,你不要管他为什么能哭。他为什么能一直跟着狄克呢?”
大卫说,“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啊。”
“我不知道。”艾德说,“反正他就是会跟——我只知道这样。”“他们把那个酒桶怎么了?”灾难之子问。“他们把它丢下船,它像块铅一样沉到河底了。”“艾德,那个小孩看起来像是被闷死的吗?”另外一个人又问:“他的头发有分边吗?”“艾德,酒桶上的牌子叫什么?”一个叫做比尔的人问道。“艾德,你有书面的证据吗?”吉米说。“艾德,你是不是他们其中被雷劈死的一个啊?”大卫说。“他?不,被劈死的两个都是他。”鲍伯说。他们都吃吃地笑着。“艾德,你不觉得你应该吃药了吗?你的脸色不好噢,你不觉得你脸色很苍白吗?”灾难之子说。
“别这样嘛,艾德。”吉米说,“证明给我们看嘛,你身上一定保留着一块酒桶的木板当证据才对啊。拿出来给我们看嘛——快——那我们大家就会相信你了。”
艾德气愤地站了起来,叫他们全部都给他小心,然后骂骂咧咧地走开了。其他的人则对着他起哄,喊声和笑声2英里外都听得见。
“兄弟们,我们切个西瓜庆祝庆祝吧!”灾难之子说。然后他摸黑走到我的藏身之处,伸手碰到了我。这时我全身温暖柔软,而且什么衣服也没穿,他吓得“唉哟!”一声跳到右面。
“兄弟们,拿个灯笼过来,这里有一条和牛一样大的蛇。”
于是他们带着灯笼围过来看着我。“给我出来,你这个死乞丐。”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谁?”另外一个人问:“你来这儿干什么?给我好好回答,不然就把你丢下船。”
“兄弟们,把他抓出来,抓住脚跟拖出来。”
我开始求饶,在地上爬着,浑身颤抖。他们看了我一下,窃窃私语,然后灾难之子说:“原来是个他妈的贼,把他丢下船吧!”
“不。”大鲍伯说,“拿油彩来把他全身上下涂成天蓝色,然后再把他丢到河里。”
“好,就这样办!吉米,去拿油漆来。”
当油漆拿来的时候,鲍伯拿起刷子,大家都笑了起来。正当他想要往我身上涂下去的时候,我开始哭了起来。这招对大卫似乎有点奏效。“给我住手,他只是个小鬼而已。谁敢碰他我就把油漆涂到他身上。”
于是我往四周看了看,他们有些人嘴里咕哝着。鲍伯把油漆放下,其他人也没有再说什么。
“到火边来,让我们来看看你到底来这儿做啥。”大卫说,“坐下来自我介绍吧,你来船上多久啦?”
“先生,还不到25秒呢。”
“那你怎么这么快身体就干了啊?”
“我不知道耶,先生,我总是这样。”
“噢,是吗?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才不打算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呢,于是我说:“查尔斯,先生。”
他们全部大喊了起来,我很高兴我这么说,因为如果他们笑了,心情应该会好一点。
当他们笑够了,大卫说:“不会吧,查尔斯,五年你不可能长这么大吧。你从酒桶里出来只不过是个婴孩,而且早就已经死了。现在跟我们说实话吧,没有人会伤害你的,如果你没有心怀不轨的话。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爱力克·詹姆斯,先生。爱力克·詹姆斯·霍普金斯。”
“好,爱力克,你从哪儿来的啊?”
“从一艘货船上来的,它就停在弯道的那一边。我在那上面出生,老爸一辈子都在这条河上从事贸易,他叫我游来这儿,因为当你们经过的时候,他想要请你们传话给在凯洛城的一位乔纳斯·透纳先生,然后告诉他——”
“少来了!”
“是真的,先生,我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老爸说——”
“噢,你祖母可好!”
他们都笑了起来。我试图往下说,但是他们制止了我。
“你给我听清楚了。”大卫说,“你很害怕,所以你乱说话。但是从现在开始要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你住在船里是真的吗?”
“没错,是一艘商船。它就停在河道的另一边。只是我不是在那艘船上出生的啦,这次是我们的处女航。”
“这才像话嘛。你来这儿干吗?偷东西吗?”
“不,先生,我不是。我只是想要到木筏上来玩玩嘛,所有的男孩都会这么想。”
“嗯,我知道了。那你躲起来干什么呢?”
“有时候船员会把小孩子赶下船。”
“没错,因为小孩子可能会偷东西。你听好啦,如果我们这一次饶了你,你可以保证你以后都不再犯了吗?”
“老板,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再犯。”
“好吧,现在离岸并不远,你下船去吧,下次不要再这样胡闹了。小子,你可要小心啊,有些船夫可是会把你打得鼻青脸肿的呢。”
我连再见都来不及说,立刻跳下船向岸边游去。后来当吉姆划过来的时候,那艘大木筏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我爬上木筏,很高兴再次看到我的家。
现在我们没什么事好做,只有仔细留神不要错过那个小镇。吉姆说他一定会小心察看,因为到了凯洛城就代表他成了自由之身,如果他错过的话,他将永远是别人的奴隶,而享受不到自由的滋味。每隔一会儿,他就跳起来喊着:“是那里吗?”
可那并不是,那不过是鬼火或萤火虫罢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又像以前那样望着。吉姆说一想到他离自由这么近,就全身颤抖发热。老实说,听他这么说我也激动起来了,因为我突然想到如果他自由的话——这该怪谁呢?是我!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逃脱良心的谴责。它使我心烦,无法静静待在一个地方坐着。这感觉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然而现在却发生了,而且时时跟随着我,不断地折磨我。我试着安慰自己说我并没有错,因为又不是我帮吉姆从他主人那里跑出来的,然而这并没有用,我的良知每次总是对我说:“你可是清清楚楚知道他是为了自由而逃跑,而你大可以上岸告诉大家这件事。”没错,就是这样——我就是没有办法不自责,我的良心随时提醒着我说“可怜的瓦特森小姐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啊?你亲眼看见她的黑奴逃走了,却一句话也不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呢?她还教你读书,要你学乖,尽她所能地对你好,她就是这样子对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真是卑鄙极了,希望自己死掉算了。我心神不宁地划着船,吉姆也是。我们谁都安静不下来,每次他跳着高喊:“那是凯洛城!”我的心就好像被子弹射中了一般。我想如果那真的是凯洛城的话,我一定会悲惨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