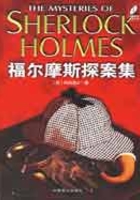蝶舞目光转锐,语声低缓沉凝:“正房那边,这院子里只有我能过去晨昏定省,而近来我身患重病,连门都出不得,夫人那里不管丢了什么,都与我期云阁无关。这是三岁孩童都能想的到的事。你还是快些带人走吧,我身子不适,脾气就难免变得有些怪,吩咐人将你一通打,你岂不是太过冤枉?”
那婆子一时答不上话来,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若回去,就是办事不利,从夫人那里一分好处也拿不到;若不回去,期云阁的几个婆子个个如凶神恶煞一般,这慕容姨娘也不是个善茬,即便不走,也只是一味僵持不下。
此时静荷眼中现出一丝戾气,走到那婆子面前,冷笑道:“我家姨娘的话说得很明白了,您还想怎样?”说着唤小丫鬟过来,“我们把这位妈妈送出去,不要扰了姨娘的清静,否则,将军怪罪下来,谁都消受不起。”语毕,和小丫鬟把那婆子强行推出了门外。
有两名小厮匆匆走进院子,也不说话,只是站在厅堂的台阶下,冷冷地看着从正房过来的几个人。那婆子这才如梦初醒,连声告罪,带着人灰溜溜的走了。连将军身边的小厮都过来了,任谁也看得出,慕容姨娘在这府中,谁都动不得。意外之财,谁都想要,但若因此赔上了差事甚至性命,就太蠢了。回去的路上,她才幡然醒悟夫人说的那句“期云阁那儿,试试吧”是什么意思,原来,夫人根本就没对此事抱什么希望,这一番闹腾,不过是投石问路,看看将军是否还是格外厚待慕容姨娘。
蝶舞被这场小小的风波扰得躺不住了,站起身来,缓步走进书房,坐在书案后的椅子上,看到那幅闲居图,神色一恍。怪不得总觉得和寒烨昭之间有些隔阂,原来意识里,一直不能忽略画中这女子。
这女子到底是谁?是不是他难以放下的曾经?
她介意,因为前世的思想根深蒂固,致使情绪一再与现状脱节,不能安心享受现状,不能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这个男人,不能主动迎合他、回报他对自己的好。她知道这样是自寻烦恼,也知道在这个社会无从选择,更明白自己已足够幸运,可还是会怅然若失。
“蝶舞呢?”
听到寒烨昭的声音,蝶舞意外之余,慌忙胡乱拿了本书摊开在桌面上。她不愿意对他流露太多小女儿的心态,前世虽没时间没缘分经历情场的风花雪月,却听过看过太多,感情这场仗,谁付出的多,谁就会在失望时伤得更重。她的悲喜,只想妥当的收藏在心里,独自品尝。他再优秀,也是土生土长的古代男子,对男人三妻四妾的观念根深蒂固,保不齐哪日就开始冷落她,到那时,即便心里失望痛苦,也能伪装出一个好看的姿态。
偶尔,她也会痛恨自己想得太多,可这些问题都是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容不得不时刻记挂在心。她只是个妾,身份卑微,这是她致命的弱点,必须从最初就为一生步步为营,其中也包括感情。
寒烨昭走进来,凝眸打量蝶舞,笑,“好看。”又摸摸她的脸,“闲时多下床走动走动也好。”
蝶舞扯出一个笑脸,看到笔墨,忽然想起给大老爷和顾姨娘写信之事,忙不迭就要起身。
寒烨昭却按住了她,“去做什么?”
蝶舞道:“去找丫鬟来研磨,这一病就忘了写信报平安之事。”
“坐着就是。”寒烨昭亲手帮她研磨,继而调侃道,“要我回避么?”
蝶舞失笑,“难道我还会向家里说中毒之事么?”说着拿出信笺,提笔书写。
寒烨昭道:“你自然不会说,我只是怕你说面目可憎。”
蝶舞就推他,“一边去!我本就没什么力气,你再闹,我连笔都拿不稳了。”
寒烨昭不再逗她,静静看她写完,之后从她手里拿过笔,坐到对面,伏案疾书,片刻光景,也写完了一封书信,取出一枚印章,在落款处盖印。
蝶舞起身,探头过去,就皱了皱眉,又是狂草!她得承认,这种字体让她很头疼。
寒烨昭等墨迹干透,将两封信折好,放进一个信封。
蝶舞就问:“你写的什么啊?给我爹写的么?”
寒烨昭解释道:“儿女写信,自然是报喜不报忧,谁都晓得这个道理。我若不帮你佐证,你娘家恐怕还是不能放心。”
这细节都帮她想到了,蝶舞为之叹息:“你一旦好起来,怎么这么好啊!”语声不自觉地有了几分孩子气。
寒烨昭捏捏她的鼻子,“你一旦笨起来,是真笨。”
蝶舞气哼哼的,“少说一句也不碍事的,偏要处处挤兑人。”
寒烨昭由她抱怨,唤来静荷,吩咐她把信交给管家。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都没有提及钟离薇今日的举动。事情已经过去,就无需再提。钟离薇要闹的日子还长着,花样也会越来越多,若次次铭记在心,不气死也会被累死。
晚间,寒烨昭要出门赴宴,蝶舞吃罢饭,喝了汤药,没多时就倦得睁不开眼睛了,于是漱洗就寝。药效之故,她近日睡眠强悍,好处颇多,一是第二日醒来神清气爽,气色一日好过一日;二是寒烨昭喝得微醺时回来,她亦不知,任他偶尔孩子气的胡闹,也是咕哝几句就继续埋头大睡。
腊月二十四,扫尘日,寒府上下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蝶舞已经能四处走动,静荷带着小丫鬟收拾房子时,就把寝室让了出来,让她们一次忙完,自己和含桃漫步至院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