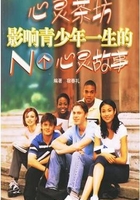初春,傍晚依然凉意沁人,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开始往回家的路赶。
暮色前,一个瘦弱的布衣少年背着画板急步前行。少年衣着普素,身形瘦弱,脚步却迈得坚定。少年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的年纪,皮肤白皙。头上绑着成人头髻,可以看出少年已弱冠。
不多时,少年进了村庄,村口不远处站着另一个小男孩,十岁左右的年纪,五官倒是和少年极相似。见少年出现,小男孩赶紧跑向前帮他提手中的行囊。
“哥,你可回来了,娘亲都等急了。”
“嗯,今天的活接晚了,娘亲可还好?”少年见了小男孩,会心的笑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的笑容。
“娘亲还好,只是……”
“只是什么?”少年急行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脸色凝重。
“哥,你别瞎想,不是娘新的事儿,是你的事儿。”小男孩一听便知道自家兄长又误会了,自小他便是个机灵的孩子,不像哥哥总是那般沉稳。
但凡是关于娘亲的事儿,哥哥总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我的事?”少年更加疑惑了。
“嗯,今天村长来过咱家了,说是征兵的事,边关打仗,哥哥也在征兵名册之中。”
“征兵……”少年眉头深锁。
“怎么办呀哥?”
“这……”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毕竟“他”只不过是“她”而已呀!
十六年前,身为律师的她因为打赢了一场官司而招来杀身之祸,喝孟婆汤,过奈何桥,再世为人,却不知道为何仍然保留着前世的记忆。
再世为人,投胎成了这户农家的女儿,农家男主人,也就是她的父亲姓梨,父亲原本乃是富贵人家的公子,一届大好前途的书生,舞文弄墨的料子。却因为喜欢上贴身婢女枊儿,也就是她的母亲。二人本是主与婢的关系,要结为夫妻自然会遭到梨家家主的反对,无奈之下,二人只得私奔到了别处生活。
于是有了她,梨画。也就是投胎进入枊儿肚子的她。
一家三口本来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六岁那年,母亲又为梨家添得一子。也就是弟弟梨庚。父亲本是富家公子,只会舞文弄墨,日子也就靠着父亲卖字画过活,再加上母亲做的女红也不错。一家四口和和美美挺不错。至少梨画是这样想的。
但是好景不长,梨画十岁的时候家中闹饥荒,父亲却在此时得了重病,家中本就过得清贫,哪里有银子给父亲治病。就这样,梨画失去了父亲,她怪自己没有能力养家……
后来,母亲带着她和弟弟说是要回梨家认祖归宗,哪里知道梨家不但不认他们,反而命下人将他们赶走,母亲从那时便郁郁害寡欢,终日以泪洗面。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女扮男装,继承父亲的事业,在街头卖字画。
他们在父亲老家城外的小村庄里定住了下来,村里都是些老实人,见一个寡妇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很不容易,又是帮建房子,又是送好吃的。大妈大婶见母亲身体不适,也会经常过来帮忙做些什么。
再说梨庚,三岁多四岁的年纪,根本不记得自己原来有一个姐姐而非哥哥。
梨画十岁开始男儿装扮在外买卖字画。母亲原是不答应的,但见自己身体每况日下,所做的女红也卖不了几个钱,而梨画在梨父的影响和教育下习得一手好字,画得一副好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再者家中实在已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梨画能有这样的画功,全赖前世爷爷的熏陶,爷爷是有名的国画大师,而她则喜欢画肖像画,或素描,但凡是画,她皆钟爱,她甚至可以把画画得如同照相机照出来一般。后来转世投胎后跟着梨父学画,梨父去逝后她便使出前世自己的才华,将古代不可能完成的画让它在这异世呈现。
梨画在城里没有摊点,他只是用那十岁的身体背着父亲生前的背囊,坐在街角等生意上门。他记得以前父亲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不同的是,他不会像父亲那样傻等,苦等。而且人家不会平白无顾的相信一个十岁的小孩子能画出什么好画来。照此下去全家都会被饿死。
于是他特意跑到有名的茶楼面前,对着作账的掌柜画了整整一个下午,当作礼物送给掌柜,掌柜对梨画的肖像画爱不释手,本打算拿回家好好收藏,但是梨画的要求是挂在茶楼最显眼的地方,否则他宁愿将画撕了,梨画的用意可想而知,看过她的画的人,还没有不喜欢的,连她的父亲都甘拜下风呢!
茶楼里人来人往,皆是些有钱又有时间的大爷,只要他们来必定会看到这画,而后然后问作画之人,他只要经常到茶里瞎逛便能接到生意。自然,他不会经常作画,常言道物以稀为贵,而且他画画的手工费还不少。
不出一个月,他梨画的名字响彻全城,而他的画则是由原来的百两一副到千两一副,许多京城里幕名而来的都不一定得到他的画。
梨画可以为任何人做画,只要你付得起这个钱而他又刚好有时间,唯独梨家之人,他不画。其中的愿由可想而知。
梨画想过要将母亲接到城里住,可是母亲怎么说都不肯,因为城里是梨家的地盘。而梨家不许他们母子三人生活在城中。梨画思量着母亲的话自己有礼,他现在只是个画师,画得再好,再受达官贵人喜爱,那些达官贵人也不会为了区区一副画和梨家对上。
就这样,梨画和母亲,弟弟在小村子里生活了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