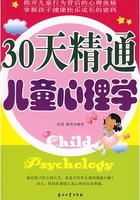马卫国、铁头、四化一起来到铁头的家。铁头家住在一座山上,属于城乡结合部,他们仨站在土墙上面对脚下的县城,享受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斜的开阔与豪迈。君临天下、指点江山一番之后,不知是谁的主意,仨人比赛向对面的墙上屙尿,看谁的射程最远,尿的最高。
三股浑浊的颜色发黄的水柱从楼顶喷射出去,马卫国不忘自己文艺青年的本色,摇头晃脑地吟诵着:“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四化凑过来,讨好地说:“老大,应该是‘黄河’。”
马卫国愣了一下,皱着眉头认真地思考了片刻,忽然惊喜地拍了一下四化的肩膀,“对、对、对,是‘黄河’,改的好,改的好,一字千金、画龙点睛啊!”
四化正想得意一下,一阵风将尿吹了回来,仨人手忙脚乱,提着裤子纷纷躲避。
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仨人无所事事地坐在墙头上,有节奏地晃荡着腿,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他们面面相觑。身为老大,马卫国觉得自己有责任活跃一下气氛。他跳下来,面对两个人,清了清嗓子,大声喊道:“马卫国个人演唱会现在开始!”
铁头一脸的紧张,连忙撕纸团塞耳朵,嘴里嘀咕着:“又来咧又来咧……”四化也是一副欲哭无泪、无可奈何的表情。
马卫国扯开正在变声的公鸭嗓子,嘶哑的、让人难以忍受的声音已经撞击过来:“我曾经问个不休……啊你何时跟我走,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铁头和四化表情木然地看着又唱又跳、自得其乐的马卫国,其实早已经习惯了。“他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额们的痛苦之上!”四化对铁头说了一句。
马卫国在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上跳着唱着,一副乐此不疲的样子,终于唱完了《一无所有》,大汗淋漓地一屁股坐在台上,感觉似乎很爽。
铁头从耳朵里掏出纸团,走到一座钢条搭成的架子前,笔直地站着,比照上面画着的横线量自己的身高,确认自己最近是否长个了。他不知听谁说了一句,“女生未必在乎男的长相英不英俊,但个子一定要高”,所以最近对自己的身高格外在意。“如果我一米八大个,高大威猛地站在葛洲坝面前,她不开闸才怪!”铁头美滋滋地想着,脑海里是葛洲坝发呆的眼神望着自己,不自觉地吞咽口水的情景。
铁头转向马卫国:“老大……”
马卫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随口道:“身上长了个儿没长?”
铁头五彩缤纷的肥皂泡被马卫国无情地戳破了,失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四化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马卫国:“老大,那两货说要两块钱,咋弄?”
马卫国抓起一块砖头,用力掼在地上,砸出一串火星子:“给球!”
这时,从铁头家门外传来一个中年女人古板的声音,“喂……你们仨……”
仨人回头,看到一个带着酒瓶底眼镜的中年妇女正在往里张望,是他们的班主任吴桐。仨人慌忙把头缩了回来。四化低声道:“狼外婆。”马卫国作出一个“嘘”的禁声动作。
吴桐站在门口,气定神闲地喊道:“别躲咧,我看见你们了,你们仨快下来集合……”
仨人无奈地相视,马卫国再次探出头,苦兮兮地说:“今日个可是礼拜天啊!”
马卫国、铁头、四化垂头丧气地走出门,吴桐像押解犯人一样跟在后面,把这个捣蛋三人组押下山,一脸的得意。走在路上,马卫国的脑海里忽然蹦出北岛的一首最短的诗《生活》:网!他觉得就这一个字,精确地道出了生活的真谛。他扬起脸来,望着那依旧病怏怏地没有一丝生机和耀眼光芒的太阳,觉得自己就是活在一张网里,老师在学校里张着网,回到家里,老爹马建设那张时刻板着、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面孔又是一张让人窒息的网。自己像条无助的小鱼一样,偶尔从网孔里钻出来,自由地浪荡一阵儿,马上又会被他们逮回去。
“网!”马卫国脱口而出。吴桐诧异地问道:“你说啥哩?”马卫国苦笑着没有回答。
星光瓷厂的大门口,红色的横幅在风中摇曳着,上面是几行醒目的大字——“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的步子要加快”、“欢迎杨胜利厂长上任”。
星光瓷厂全体职工庄严肃穆的站在厂门口,翘首以待,马卫国的父亲马建设和姐姐马红梅都身在其中。马卫国和四化、铁头被班主任吴桐押送到班级的队伍中,成为欢迎新厂长上任的群众大军中的一员,每个人都被抹了红脸蛋,手里拿着一把塑料花。在星光子弟学校的方阵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马卫国开始不安分地东张西望,不远处,姐姐马红梅挺着自己丰满的胸脯,高昂着头,一副鹤立鸡群的骄傲姿态。马建设身为车间主任,和其他干部一起在欢迎队列中间的夹道上来回踱步,不时向自己车间的职工发号施令——“站直哩,站直哩!”“左右看齐,连个队都站不齐!”“老李,你少抽一根吧,让新厂长看到哩,多不严肃!”他不时地撩起袖子看手表,神情忐忑不安。
马卫国一见他那副溜须拍马、媚上压下的样子,心中就止不住地厌恶。马建设刚刚做了一个深呼吸,舒缓了一下焦虑的心情,就听到身后的欢迎方阵里忽然冒出一个又尖细又高昂的声音:“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随之是人们的哄堂大笑。
马建设愤然地转过身,顺着笑声的来源搜寻过去,原来是子弟学校的学生方阵里发出的。马卫国用假嗓子把大家逗乐了,见自己的恶作剧得逞,更加得意,把一把塑料花举在空中摇摆着,用更加尖细、更加妩媚的女生继续卖力地吆喝着。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马建设那张凶神恶煞似的脸出现在他的面前,因为愤怒整张脸都扭曲了。
马卫国被吓呆了,举着塑料花的手僵在空中。“啪”的一声,马建设掴了儿子一个响亮的耳光,清脆的声音传出很远,让哄笑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对仇人似的父子身上。马卫国被煽红的脸上没有任何感觉,他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巨大的屈辱感让他无地自容,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根木头一样戳在那里。他用恶狠狠地目光刺向马建设,仿佛面前这个人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血海深仇。
站在不远处的班主任吴桐推了一下厚厚的眼镜,用指头向马卫国做了个制止的手势,暗示他不要冲动,但马卫国愣了一阵,还是生气的掉头跑开了。四化和铁头无奈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他们本想跟自己的老大共进退,但被班主任吴桐一手薅着一只耳朵,乖乖地回到队列中。
夹杂在人群中的铁头时不时地偷窥一眼不远处的葛洲坝,李芳察觉到铁头居心不良的目光,高傲的地把头摆开了。铁头生气地收回目光,盯着地面,意淫似地把李芳想象成一只骄傲的、胖乎乎的小母鸡。
远处,一辆北京吉普缓缓驶来。马建设招呼大家打起精神,双手打着节拍,学生和星光瓷厂的职工有节奏地抖动着手里的塑料花,整齐划一地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冲出人群的马卫国一口气跑回了家,他觉得自己简直没脸活在这座小城里了。跑回家就是要躲起来,躲在一个没人看到的角落里。冲进自己的房间,马卫国一头栽倒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牙咬得“嘎嘎”响,内心的愤恨无处宣泄,只好用拳头狠狠地擂着床板。
傍晚时分,小城笼罩在夕阳金色的光辉里,相比白天的沉闷和压抑,多了一份惬意的温馨、闲适。人们三三两两地骑着自行车,从街道上驰过,洒下一串串的欢声笑语,车筐里买来做晚饭的蔬菜和肉随着自行车的颠簸跳跃着,仿佛急着一头扎进锅里,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诱逗得人胃口大开。
马卫国一家住在一栋那个年代典型的集体宿舍——筒子楼里。楼道中堆满了杂物,从家家户户的厨房里散发出饭菜的香味,极具生活气息的各类声音迎面飘来,邓丽君柔美的歌声若隐若现。马红梅拎着一篮子菜穿过走廊,不时地跟邻居打着招呼,走进自家的房门。她在星光瓷厂四分厂的贴花车间做技术员,因为年纪大了不爱和父母一起住,就搬到职工宿舍去了。今天是星期五,所以她回来跟父母和弟弟一起吃饭。
在这个家里,她和母亲都对马卫国宠爱有加,这让马卫国总是有零花钱在四化和铁头面前显摆。只有父亲马建设对儿子横竖看不顺眼,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马建设有一句时常挂在嘴边的经典台词——“我做了一辈子的高档瓷器,唯一的残次品就扔在家里”。马红梅也搞不清楚老爹和弟弟关系怎么就那么僵,完全不像是一对父子,仿佛是两个上辈子有着化解不开的冤仇的人因为命运的捉弄转世投胎到一个家里;又或者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自然法则在发挥作用;要么就是中年男人的暴躁脾气、喜怒无常和小孩子的叛逆心理在一起碰撞出了耀眼的火花。她在父亲和弟弟之间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只不过今天事发突然,自己这个和平使者还没来得及行动,战争就爆发了。
屋内,马母踩踏着缝纫机,正在给马卫国缝裤子。一条裤子伤痕累累,经过反复的漂洗颜色泛白,磨破的地方被马母细心又熟练地缝合在一起。
马红梅放下手里的菜,对母亲说:“额这个月发了饷给弟买个新裤子!”
马母头也不抬地说:“给他穿个铁裤子也没用。”
马卫国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下午,现在已经醒过来了,但内心的波澜还是无法平息。他坐在自己的床上继续生着闷气,想不到如何把这口恶气宣泄出去,就拿起钢笔在手臂描了一个大大的“忍”字。
马红梅推门进来,挨着马卫国坐了下来,看了一眼他手臂上的字,劝解道:“算了!”
“他当不了厂长就拿我撒气!”有人陪自己说话,马卫国憋在胸中的那口气终于找到了出口。
“你咋能瞎想,大一辈子奉献给了厂子,失落是正常的。”
“我就看不惯他拍马屁的呕样,一点尊严都没有!”
马卫国的话把马红梅逗得“咯咯”地笑了起来,用指头在马卫国的额头杵了一下,嗔怪地白了一眼马卫国。“他是把尊严都给了你,你瞧你那小心灵全是自尊心!”
马红梅起身走到脸盆旁边淘毛巾,忽然爬在脸盆架子上干呕起来,马卫国关切地跑过去给姐姐拍背。“姐,咋了?”
马红梅掩饰地摇摇手,“么撒么撒……”
马卫国顿了顿,说:“给我2块钱。”
马红梅头也不抬地问:“又要钱干啥?”
“么撒么撒!”
随着夜幕的降临,家家户户的窗口亮起了灯光,喧嚣的街道终于安静下来。马红梅喊了几声,叫马卫国吃饭,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她起身走进马卫国的房间,才发现马卫国又躺在床上睡着了,身上放着一个半导体,里面传来歌声。马红梅薅了一下马卫国的耳朵,说“吃饭了”。马卫国这才睡眼惺忪地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调台,选中音乐台后终于满意了。
饭桌上已经摆好了简单的菜肴,马建设和马母已经吃上了,马卫国走过去,将半导体放在桌角,埋头吃饭。马建设不悦地看了一眼儿子,伸手拿过半导体,换了一个秦腔,继续吧唧着嘴狼吞虎咽,马卫国厌恶地撂下筷子,重新调回音乐台,没好气地说:“我在听《每日一歌》。”
马建设硬邦邦地顶了回来:“能当饭吃?”
眼见父子之间的战火又要重新点燃,马红梅不想看到好好的一顿饭演变成掀桌子、摔碗筷的全武行,连忙出面打圆场:“大,你就让卫国听吧,些许以后能成个歌唱家呢!”
马母插话道:“别亏先人了,把书好好念,考不上大学跟你死大(爸)一样没出息。”
马建设又把收音机调成了秦腔,翻着怪眼道:“额咋没出息了?”
“当了35年的工人还是个车间主任,就这出息?”
“额这也是铁饭碗,咋叫没出息了?”
“你也就这点出息,你看看人家四化他爹……”
“四化他爹好,那不是靠歪门邪道上去的……”
“那新来的厂长也是歪门邪道……”父子之间的争吵转眼变成了夫妻两个拌嘴。
马红梅无奈地劝解说:“吃饭吃饭,一到吃饭的时候你俩就吵。”
马卫国放下筷子,站起身就往外走。马红梅在身后喊道:“吃饱了?”
“饱饱了!”马卫国头也不回地摔门出去了。马建设白了一眼马卫国的背影,把他的名言又重复了一遍,“我做了一辈子的高档瓷器,唯一的残次品就扔在家里”。
马红梅放下筷子,望着马建设说:“大,额们车间的老张师傅毛笔字写的好哩,要不要让他给你写幅字?”
马建设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写啥咧?”
马红梅很认真地说:“‘我做了一辈子的高档瓷器,唯一的残次品就扔在家里’。写成字挂在墙上,你就甭天天念叨咧,跟背毛主席语录一样,我耳朵都磨出茧子咧!”
马卫国蹬着自行车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知不觉来到了铁头家附近。他站在铁头家创下吼了一嗓子——“我曾经问个不休……”便蹬上自行车,到巷子外面的街道上等铁头,身后响起铁头母亲的一声骂——“半夜三更地狼嚎个球!”马卫国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不是因为挨骂,而是对自己美妙歌喉的否定。尽管自己声音嘶哑、五音不全,可崔健不就是凭着一副沙哑的嗓子成了摇滚巨星?所以,马卫国不仅不为自己变声期的公鸭嗓子烦恼,还很担心哪天这副公鸭嗓子消失了,变成低沉、富有磁性的成年男人的声音。如果是那样,他就唱不了摇滚,成不了崔健了。
昏黄的路灯下,马卫国拖着长长的影子,靠在电线杆上无聊地吐着烟圈,远处的路灯下有几个老人下象棋,争地面红耳赤。城市上空的喇叭里若隐若现地飘来广播声:“工业总产值13780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农业总产值4447亿元,比上年增长4.7%……”改革开放的形势一片大好,可是自己的前途却一片渺茫,生活乏味得就像没有盐味的馍一样,难以下咽。
有年轻的姑娘骑单车路过,马卫国兴奋地吹了声口哨,泼辣的姑娘骂着“臭流氓”,扬长而去。马卫国无聊而又执着地哼着:“我曾经问个不休……你啥时跟我走……”街道上成双成对晒月亮轧马路的情侣让马卫国眼红,如果有个漂亮女孩跟自己并肩散步,在朦胧的月光下、树林里卿卿我我、诗情画意,他也用不着这样无聊这样迷茫了。可是,自己魂牵梦绕的情人在哪里?长的什么样?马卫国感到很模糊、很遥远,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姑娘从他面前驰过,马卫国发现那个男的就是那天追打自己和四化、铁头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而车后座上姑娘的背影竟然很像自己的姐姐马红梅。他想再看个仔细,自行车上的两个人却已经消失在车头尽头的阴影里。
铁头趿拉着鞋从胡同里跑了出来,手里来回翻倒着火烫的洋芋,嘴里一边“呸呸”吹着,把自己烫得呲牙咧嘴。跑到马卫国跟前,他慷慨地掰了一半给马卫国,马卫国摇摇头,拍拍肚子,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
“咋又吃这?”铁头的家境在三人组中是最差的,吃饭的嘴多,挣工资的人少,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窘迫的处境让铁头很自卑,不仅在兄弟中没有发言权,在葛洲坝面前也抬不起头来。他大口地吃着热气腾腾的洋芋,脸上沾满了黑乎乎的炭灰,习惯地说:“额家又断炊了。”
“走,去额家吃!”马卫国仗义地说。
“我都吃饱咧!”铁头憨厚地一笑,谢绝了老大的好意。
马卫国也不勉强,伸手从兜里摸出刚问姐姐要的两块钱,塞到了铁头手里。铁头愣了一下,摇摇头说:“大不了再被他们揍一顿,可不能白白给他们2块钱。”在那个时候,两块钱可不是个小数。
马卫国把钱塞进了铁头的口袋里,“给你奶买包奶粉”。
铁头眼圈一红,声音有些哽咽,“老大……”
马卫国很有魄力地一挥手,把铁头那些感激的言辞堵在了嘴里,“甭废话!”
铁头抿了一下嘴唇,像是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随后对马卫国神秘地说:“走!”
马卫国茫然地问道:“去哪啊?”
“去了你就知道咧!”
新上任的厂长杨胜利家的楼下,围墙上依次露出马卫国、四化、铁头仨人的脑袋。马卫国低声问:“哪一家?”
铁头指了一下三楼一扇亮着灯的窗户,窗帘上映出晃动的人影。原来,白天的欢迎仪式结束后,四化和铁头就开始密谋晚上的行动计划,一来是为了给老大出口气,既然事情是因这个新厂长而起,那就只能把气撒在他的身上了,总不能去敲马卫国自己家玻璃吧!二来,他们对那个耀武扬威地从自己面前走过,鼻孔朝天、目中无人的新厂长也确实有些看不惯,所以决定给他个下马威。他们事先对这次行动的风险进行了评估,一致认为:新厂长肯定会怀疑是哪个想当厂长没当成、心怀不满的家伙干的,根本不会怀疑到子弟学校的学生娃头上。
铁头掏出弹弓,把一块石子放到弹窝里,把皮筋拉得满满的,瞄准了厂长家的窗户。四化赶紧把眼睛捂上,惊悚地等着玻璃破碎的声音,结果只传来一声不大的闷响,没打中。马卫国一把夺过弹弓,“我来!”
他弯弓搭箭,石子就像破口而出的利箭,射向那扇窗户。深夜中,玻璃的破碎声清晰可闻。四化和铁头险些兴奋得叫出声来,马卫国也一脸得意,觉得自己就是古代的大侠,驰骋沙场,箭无虚发。
一个一个人影走到窗边,打开窗户往外看,仨人连忙从围墙上跳下来,顺着墙根猫腰撤离。那一刻,马卫国也不明白是为了什么,鬼使神差地掉头看了一眼,窗户里探出一个苗条的身影,只能看到脸和五官的模糊轮廓。马卫国的直觉告诉他,那是一个女孩,而且是一个很清秀、很漂亮的女孩子。他不知道那女孩是否看到了她,但他很清楚地感觉到,如果有缘遇到这个女孩,自己可能会喜欢上她。马卫国的梦中情人就这样模模糊糊、出人意料地闯进了他的生活。
铁头拉了一把马卫国,示意他赶紧跑,要是真的被新厂长逮到,麻烦可就大了。“看什么呢?”铁头觉得马卫国神色异常,随口问道。
“爘火!”(cánhuò,牛 逼),马卫国答非所问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