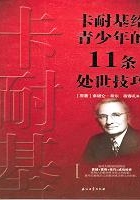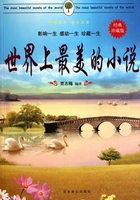绿岛,郊区,城里有名的富人墓地,我从没踏足过的地方,尽管那里面埋葬着我最亲爱的舅舅、妈妈还有安叔。
今晚,在我无处可依的时候,我唯一想到的地方就是那里。
司机师傅脸色惊疑的看着我,犹豫不决。
我苦笑了一下,这么个雨天,到处黑不隆冬的,还有人去绿岛,也难怪司机师傅会是这个表现!
“师傅,不用怕,您看我能打过您吗?”我自嘲的说。
司机师傅咳嗽了一声,被我问的有些尴尬,他一个彪形大汉,我一个狼狈的小妞儿,这实力对比一看就了然,没有悬念。
“妞儿,不是我害怕你把我怎么着,关键是现在这个点儿绿岛也关门了啊——”师傅苦口婆心的说。
我一愣,对啊,这个点儿已经关门了,可现在,我心里强烈的想要去那里,就算在大门口蹲着,那也是离我舅舅和我妈最近的地方。
“师傅,你开车吧,就去绿岛——”
司机师傅看我意已决,叹了口气,开车去了城郊。
我手支着车窗,看着雨滴争先恐后的砸在车窗上然后落地,尸骨无存,就好像我们这些男男女女一样,疯狂的陷入爱情,撞得头破血流,最后剩下什么呢?
“妞儿,有什么事儿都别往心里去——”司机师傅看着一路上沉默的我,劝起我来,“人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想开了,这辈子就活的乐呵些,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转头朝他笑了一下,这个时候还有人对我说这么句暖人心的话,甭管他是随口一说还是为了打发时间找人聊天,我都挺感激他的。
“年轻的时候啊,什么事儿都能遇着,现在想来,也挺精彩的,哈哈——”司机师傅也没嫌我不和他对答,自顾自的说。
“我看你这个小妞儿,面带福相,也不是个担不起事儿的人,把心搁在肚子里吧,什么事儿都会过去的,这人啊,还是活着好啊,不是有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呵呵,没事,我就想来看看——”我怕司机师傅再往下说,就会劝我别寻死了。
寻死?怎么会?我撇撇嘴,这么些年来,身边的人一个个离我远去,我都告诉自个儿,要好好活,连同他们的一起活下去,活的快乐,活的精彩。
所以,就算遇到再大的冲击,我也不会有寻死的念头的。
最早舅舅在我面前跳楼,一地的血水,我每晚都做噩梦,只有在妈妈怀里,才觉得安心,那时,每当舅舅的祭日或是清明节,妈妈都希望我能和她一起去看看舅舅,但我抵死不从,我不愿看冰凉的墓碑和墓碑上笑如旧的人。
后来,妈妈和安叔出了车祸,也走了,安姨办理的后事,把他们葬在舅舅的旁边,三人相邻,再到祭日和清明节的时候,安姨和安臣都会去,可我依旧从没去过。
或许我心里懦弱的认为,只要不看见他们的墓地,我就觉得他们一直在我身边,看着我,笑着看着我。
但是今晚,当安臣崩溃的时候,当安姨的巴掌重重的下来的时候,我唯一想来的地方就是这里,我想亲手摸摸他们的墓碑,想亲眼看看墓碑上还是微笑着看我的舅舅和妈妈。
“司机朋友们,请注意,请注意——”收音机传来的DJ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通往郊区的国道由于大雨,暂时关闭,司机朋友请注意——”
“妞儿,你看,路都封了,咱们还是回吧——”司机师傅又劝我。
可我现在的执念非常深,“师傅,你就往前开吧,能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
师傅又长叹了口气,“没见过你这么拗的人!”
终于车子停了下来,前面不能再通车了,司机转头看着我,那意思我明白,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我摸摸口袋,掏出钱,“谢谢你,师傅——”打开车门,下车。
“哎——你等等——”师傅叫住我,从车窗递给我一把伞“拿着吧,顺着这路往上爬,就能到门口——”
“谢谢你——”我再次道谢,但还是果断的转身。
瓢泼的大雨,没有要停的迹象,泥泞的山路上,我深一脚浅一脚的,慢慢往上爬。
思绪转到安臣身上,安臣有躁狂症,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事情,曾经那么阳光那么温柔的人,怎么会?
安姨显然是知道的安臣的病,所以,她一直鼓励安臣出国,也对,国外没有这些事,没有这些人,没有安臣崩溃的诱因,安姨的做法是对的,那,为什么他们要瞒我?我不该知道安臣的事吗?
这就是为什么安姨在安臣回国后对我若即若离的原因吗?她知道我是安臣的劫难,所以她看见安臣吻我会有那么大的反应,所以她选择移民。
我确实不能陪伴安臣,两个心里都受过严重伤害的人,两个身上都布满刺的人,两个都需要别人包容别人安慰的人,怎么能相互依存?两只刺猬怎么能拥抱?
看来,安臣出国这些年,不仅仅是学习这么简单的事儿,而且他还学的心理学,对了,导师还是顾丹漾的妈妈,也是……顾念的妈妈。
想到顾念,我深深的吸气再呼气,脚已经冰凉,鞋子都进水了,但这些,都不如我此刻心里的悲凉。
想到顾念,想到傅蕾给我的那些照片,想到顾念的死,想到顾丹漾的话,想到顾妈妈冰冷的语气,其实,我还挺佩服顾妈妈的,看到我居然都没甩我一巴掌。
呵,我想起傅蕾曾经骂我的话,“苏绣儿,你就是个丧门星,你看你周围的人哪个得好了?”她说过很多难听的,但就这句我始终记着,我对自己都有了唾弃感。
我跟只蜗牛一样,还在一步步的爬着,终于眼前看着了星星灯火,和冰凉的大铁门。
我没有敲传达室的门,只是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头顶上的伞,并不能阻止伴随着冷风的雨水敲打在我同样冰冷的身上,我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出什么是疼什么是痛!
我就这么坐着,不知什么时候没了知觉,直到被人推醒了。
“你怎么坐这儿啊?身上还这么烫?不是病了吧?哎,你没事吧?要叫救护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