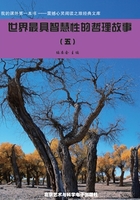片刻的沉寂,侍卫们噔时反应过来。爷今天的反应有些反常啊,却不知道是为何?真是因为这个赵国公主吗?
彦大快马连夜出府,不到半柱香的时候,便从流云居把诸葛流云给请了过来。
诸葛流云一袭月白色的锦袍,长发束冠,腰间束一条蓝绫长穗绦。眉如墨画,面如桃瓣,见到祁钰之时,脸上是温和的笑意:“我说,钰,听彦大说你情绪激动,说什么人命关天,十万火急?”
祁钰长袖上扬,墨眸凝视着紧闭双眸的阿阿荨,女子脸上是痛苦的表情,额心的菱花痣妖治而清远。男人的心里突然冒出一股烦躁的情绪。朝着诸葛流云冷道:“看她死不死得了!”
“你紧张?”诸葛流云闻言弯唇浅笑,纵肆而大胆。
“诸葛流云!你想让流云居变成平地?我可以成全你!”祁钰眸中渐暗,暗深的目光里泛过一丝凶狠。
诸葛流云轻叹:“心若一动,情意千行!”说完上前摸着女子的脉象,脸色渐渐暗沉下来。
祁钰蹙眉,墨袖一挥,负手而立,深邃的眸光清寂疏冷,看到她倒下的那一刹那,确实有那么一瞬的惊慌与手足无措。当时那女子的眼神凄婉,似狂,似嗔,似绝望。火光映在女子那如玉般绢秀的脸上,那朵淡雅的菱花竟是生生扯痛了他的心。
他的绛儿死了!眼里的这个人是赵国公主!害死绛儿的是赵人,他不应该如此!
“死不了!不过是伤口离心脏很近,伤口又太深,失血过多,脉动微弱。我看,你当真是下得了手。那刺客死了?”诸葛流云吩咐身边的医奴包扎了女子身上的伤口后,缓缓地说道。
“死了!”祁钰眸光寂静。她还死不了!听到诸葛流云这么一说,心里莫名的安心下来。
那流云居的医奴是个十三四岁的小丫环,长得清秀灵慧。手脚麻利处理完伤口之后,这才开口说道:“公子,三王妃好像梦魇了。看起来很痛苦。”
“三哥……”阿荨呢喃出口。额上的汗珠更是浸湿了青丝,女子藏在被子里的手倏然握紧,泛起淡色的青白。
漫天的血腥,郁郁暮色下,映着狰狞的红光。冬风肃杀,呼啸一掠飞卷落叶绫纱。细云迭峦积压苍穹,夜空阴霾,如黑得望不见底的凄迷。
然后是剑起剑落,血流成河。
少女站在空旷的廷墙处,漫天弥漫的是腾腾的煞气。她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还有蜿蜒逶迤流在脚边的鲜血,浓郁血色是灼烫而幽深。孤独与恐慌袭卷全身,仿佛灵魂就会离身体而远远地离去。
“父王……”
祁钰眸光幽深,墨玉般的眼瞳映着湖水浮光,折射出与平素毫不相同的锋芒,走到床前看着一脸酡红,神色痛苦的女子。
开口道:“该死的女人!烦死了!”说罢,出手如闪电般点上女子的昏睡穴。女子顿时深深地沉睡过去,脸上的痛苦也渐渐缓和了过来。
诸葛流云笑意深深,薄唇勾起。吩咐身边的医奴道:“去把这方子上的药买来。叫王府里的奴婢煎来。”看来这赵公主身上的蛊,他也没有必要下。说不定这女子正是解救祁钰的人,而此时的流云公子更是笑得纵狂。
窗外的树叶被风吹得呼呼作响,小亭下湖水随风荡漾,一波一个圈纹,一圈一个回旋。
祁钰凝眸看着眼前的女子,明亮的烛光浮出他俊朗的眉目,星一般明亮疏狂的眼。男人抬起手里的药灌入女子嘴里,片刻工夫又全部从女子的唇边流了出来。
“哐!”的一声。祁钰将手里的药碗一丢,朝着旁边的丫环冷道:“再去煎一碗来!”
他就不信喂不进去?先前丫环们说王妃紧抿着嘴,根本就灌不进去!这本来也不关他的事,他就是鬼使神差的亲自来喂。
丫环战战兢兢地再次端来一碗黑染染地药汁,男人扬手接过。提起女子的头,再次灌进。药汁再次一滴不剩的从女子的唇边流了出来。
祁钰狠狠将药碗往地上一摔,眸子里盛怒的火光在跳动。吼道:“再去煎一碗!”这赵公主一点儿面子给不给他!等她清醒之后,再好好地折磨她!
阿荨细长的睫毛突然颤动了一下,谁这么缺德给她灌这么苦的东西。打死也不喝!谁要是再喂她,她醒来一定直接抽了他的筋!
有人捏着她的鼻子,轻柔细致。然后是冰凉气息扑上她的唇,软软的贴在她的唇瓣,那浓郁的苦味便顺着喉咙一点点流入肚中。阿荨想开口大骂,可是张不开嘴!
等到不知多久,那浓郁的苦味才停了下来。女子的眉宇皱得更紧了。
祁钰将空了的药碗往丫环手里一放,拂袖而去!
端着药碗的丫环疯狂了,尖叫一声。半摔半滚地爬出了枫轩,见人就吼:“知道吗?王爷亲自给王妃喂药。而且还是嘴对嘴。”表情如何如何,神态如何如何,这丫环再添点油,加点醋,再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如何如何。
“真的吗?哇噻,天大的新闻,咱们赶紧卖给宫廷狗仔队去,传到皇上耳朵里,能捞一笔不少的钱财呢。”一厨房洗菜丫环一脸的欣喜。
“苔儿,你说爷的其他夫人要是知道了,对怎么对付新王妃?”另一烧火丫环说道。
“毒?杀手?暗器?诽谤?”洗菜丫头摇了摇头,这府里的夫人好久没用新招式了。
“还有陷害,夫人们好久没有使用了。真是怀念啊……”另一洗碗的丫头一脸的憧憬。
“来来来,买定里手。赌夫人们用新招式对付新王妃的押这边,赌用老招式对付新王妃的押这边!”王府里的家奴也聚众了。
所谓,一山更有一山高。一驴更比一驴笨!北苑住着的夫人们绝非善良之罪,如虎狼般开始蠢蠢作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