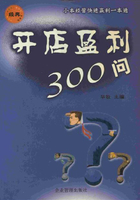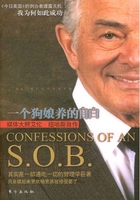眸光一转,唇边笑容清冷如寒冰,沉声道:“你们主子屡次陷害我,如今,我也没法子了,只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人之常情,怨不得我。”
采蘋冷冷一笑,凝视着抱琴,道:“你倒是忠心,落到这个地步,还想着为元贵人求情。哼,这事情你难脱干系,还是自求多福吧。”
抱琴呆了一呆,以手掩面,轻轻哽咽起来。黛玉不为所动,轻轻拍了拍手,便有宫娥快步行近,屈膝道:“四皇妃有何吩咐?”
黛玉浅浅一笑,温婉地道:“这个时候,太后应该醒了,劳烦姐姐去永寿宫走一趟,将太后请来,不许惊动其他人。”
宫娥闻言,不解其意,却又不敢追问,立刻转身去了。采蘋凝睇着黛玉,杏眼微瞪,讶然道:“姑娘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自己去永寿宫,将事情说清楚就行了,何必劳烦太后过来?”
黛玉轻轻摇头,眉宇间透出淡淡的无奈,长叹道:“事情涉及八皇妃,岂能草率?姐姐别忘了,她毕竟是八皇子正妃,又是西宁王府的郡主,身后的势力,极是强厚。何况,如今形势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单凭这件事,怎能撼动她半分?不如将太后请来,悄悄处置一番,也便是了。”
拉住采蘋微凉的手,压低声音,徐徐道:“姐姐,你要记得一句话,路要一步一步走,方能稳当。我实在没有本事,一口气扳倒那么多人,太后也不会容许后宫因我而乱。再者,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我必须退一步,将来,便无可预料了。”
采蘋沉吟良久,颔首道:“姑娘所言极是,罢了,借着这件事,扳倒元贵人,也很不错。”
抱琴听了,脸色煞白,整个人僵在地上,如木雕一般,黛玉也不理会,让紫鹃、采蘋将抱琴拖进正殿,用布塞住嘴,一同退到屏风后面,自己端坐在窗下,品着香茶,静候太后到来。
过了半盏茶的功夫,便听得一阵喧哗声,宫人簇拥着一脸雍容的太后,款款行了过来。黛玉忙放下茶杯,扶着侍婢,起身行礼。
待见完礼后,太后挽住黛玉,满面慈爱之色,含笑道:“玉儿有事吗?”
黛玉颔首,明眸流盼,四下一望,敛容道:“请皇祖母屏退左右,玉儿有话要说。”
太后沉吟片刻,挥了挥手,吩咐道:“都出去吧,待哀家与四皇妃说说话儿。”
众人听了,忙依言退出,见安排妥当,紫鹃、采蘋方拉着抱琴,从屏风后转了出来。
太后见状,很是惊讶,指着泪流满面、呜呜咽咽的抱琴,皱眉道:“这是怎么回事?”
采蘋敛衣跪下,恭声道:“太后容禀,这是元贵人的贴身侍婢,元贵人命她过来,给我们姑娘送了一样东西。”拜了一拜,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叙了一遍,又奉上红麝串。
太后满面震惊,不待听完,早已脸色铁青,拍案道:“竟敢在哀家眼皮底下施用阴谋诡计,算计玉儿,这还了得!”
说着,便立起身子,看向窗外,扬声喝道:“传旨,即刻将凤澡宫的元贵人带来见哀家。”殿外的宫娥听了,忙答允下来,踏步如飞地去了。
太后转过头来,拉住黛玉的手,怜惜地道:“玉儿,你受苦了。”
默了片刻,秀眉微轩,迟疑道:“元贵人好说,婉儿的身份,却非同一般,不能……”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声音转低,渐渐止歇。
见事情如自己所想,黛玉心中长叹,面上却只得不动声色,起身行了一礼,恬然道:“皇祖母说的是,想来婉儿不过是一时糊涂,才行差踏错,我又是她嫂子,实在不必计较。”
太后闻言,容色转霁,摩挲着黛玉的手,语气缓和:“玉儿,你果然识大体,今日暂且罢了,若婉儿不知悔改,敢再有下次,哀家绝不会偏袒,你放心罢。”
黛玉抿起纤柔的唇,笑靥明澈动人,温婉地道:“多谢皇祖母。”
两人叙话之际,宫娥已经拖着元春,行了进来。数月不见,元春已与从前判若两人,容色憔悴,上颌变尖,白皙的皮肤隐约现出青玉色,带着淡淡的轻纹,仿佛一朵秋风里在枝头寒颤的花,形销骨立,不复昔日的花容月貌。
黛玉看得分明,笑容淡淡,一脸的风轻云淡。元春略一打量,见太后神色清冷,抱琴俯伏于地,不禁目瞪口呆,忙跪下道:“太后唤臣妾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太后挥了挥手,摒退宫娥,似笑非笑地瞧着元春,语气森冷如冰:“这原因,你自个儿不清楚吗?”说着,冷哼一声,将案上的手串掷下,沉声道:“这是什么东西,请元贵人解释解释。”
元春见状,惊得冷汗涔涔而下,叩首道:“臣妾惶恐,不明白太后的圣意,还请太后指点。”
“不明白?”太后抬手抚一抚鬓发,目光如剑,在元春身上周旋打转,不紧不慢地道,“你的贴身侍婢已经招认,说你想用这红麝串算计四皇妃。哼,四皇妃是你的亲表妹,亏你也下得了手,也不怕天打雷劈。”
元春听了,面色微乱,却很快恢复过来,磕了一个头,急急地道:“太后明鉴,臣妾从没见过什么红麝串,更不敢算计四皇妃。这抱琴虽是臣妾的侍婢,但前几日她办事不力,被臣妾训了一顿,想必她怀恨在心,借此来报复臣妾。”
眼睛滴溜溜一转,拉住抱琴的衣袖,皱眉道:“平日里本宫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本宫?这样黑心陷害本宫,你也忒狠了。”说着,伸出右手,朝抱琴挥了一巴掌。
抱琴一日之内,挨了三巴掌,又惊又恼,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元春以手掩袖,啜泣道:“这贱婢一派胡言,太后千万不要听信。”
见她在片刻之间,便将事情推得干干净净,紫鹃、采蘋互看一眼,均有惊愕之意。黛玉依旧淡然处之,瞧着元春,冷笑道:“皇祖母面前,元贵人竟敢打人,如此嚣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太后横目看着元春,不带丝毫感情,冷冷道:“元贵人,哀家在这个地方,已经呆了几十年,虽然称不上慧眼如炬,却也能瞧出孰是孰非,谁对谁错。今儿之事,全是你指使,你少惺惺作态,在哀家面前演戏,哀家瞧着恶心。”
说着,站起身来,拂一拂衣袖,居高临下地道:“你十三岁进宫,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事情,也做了不少。前几年,你爬上妃位,背地里,施用了不少手段吧?这些事情,哀家心知肚明,却一直都不想理会。毕竟,这是皇宫常有之事,实在不能太计较。但是,今儿个你竟敢算计四皇妃,这便罪无可恕了。”
元春闻言,不禁面如死灰,呐呐说不出话来。太后微眯了双眼,目光骤然变得锐利而清明,冷然道:“罢了,事到如今,哀家也不说什么了,以你之罪,本要立刻处死,但哀家念着你服侍皇帝一场,如今,只除了你的封号,你去冷宫里过日子吧!”
听了这番话,元春吓得身子发抖,脸色发白,冷汗直流,咬着朱唇,讷讷说不出话来。
这时抱琴已回过神来,侧头瞧了元春一眼,眸中含怒,不忿道:“奴婢十岁起,便跟在贵人身边,一直尽心服侍,忠心耿耿,不曾有一丝违逆。今儿个贵人让奴婢送东西过来,奴婢还一心记挂着贵人,特意求四皇妃念在表姐妹的情分上,助贵人一臂之力。如今事发,贵人却将所有责任推到奴婢身上,贵人如此心狠,真真枉费奴婢一番忠心,让奴婢心寒!”
说到这里,悲愤至极,面上泪水直流,点点滴滴,不可抑止,吃力地爬到太后、黛玉面前,涩声道:“太后明鉴,四皇妃明鉴,此事奴婢并不知情,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若是知晓了,奴婢便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算计四皇妃,求太后、四皇妃念在奴婢愚昧无知的份上,开恩放过奴婢罢。”
太后眯起眼睛,瞧着满面伤悲、容色凄楚的抱琴,淡淡地道:“以你今日之行,本当立刻打死,罢了,哀家不是心狠手辣之人,姑且将你发往浣衣房当差吧。”
抱琴听了,呆了一呆,只得含泪叩首,恭声道:“多谢太后。”
太后双目轻合,神色微倦,挥手道:“罢了,事到如今,哀家也不愿多言,究竟也没有什么意思,你们主仆,该进冷宫的进冷宫,该去浣衣房的去浣衣房,别再在哀家面前晃悠了,哀家瞧着心烦。”
元春听了,面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难看到了极点,颤抖着嘴唇,急急地道:“太后娘娘,臣妾有话要说,这条红麝串,并不是臣妾之物,而是八皇妃给的。这件事情,也并不是臣妾的主意,臣妾不过是听命行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