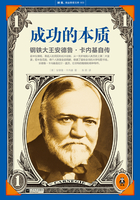“小姐,小姐,这边。”
待那人走近些时她才想起他是跟随父亲多年的司机刘师傅。她离开D城也有四年了,所以这回乍一眼看过去,愣是没认出来。
“刘师傅,你怎么在这里?”她笑笑,其实心里已明了,定是父亲派来的。毕竟电话是他打给她的,自然知道她得知了消息定会马上赶过来。
消息,是的。四年来她的父亲第一次打电话给她,是为了告诉她一个消息:她的母亲,病危,正在急救室抢救。
她从未听过父亲会用那种语气与她说话。慌乱的,语无伦次,甚至是濒临崩溃的,仿佛即将失去一样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
那一刻,她甚至几乎要忽略掉母亲病危带给她的巨大痛苦,心中竟是隐隐觉得快意的。人都是这样吧,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直到快要失去的时候才恍然觉悟。
果然,刘师傅神情有些急切慌张,“小姐,是老板让我来接您的,您跟我上车吧,太太她……”话没能说下去,因为她已经快步朝着机场门口停着的那辆熟悉的凯迪拉克走去。
几年没回来,D城果然是大变样,俨然就是一繁华大都市。车子行驶时,经过的明明是她以前念书每天要走的地方,或是时常逛街压马路的地段,可如今却都早已变了样,所谓人非物亦非,说的,大概就是如此了吧。
“小姐,到了。”车子在一家私人医院门外停了下来,刘师傅率先下车,绕过车子给她开了门。
她见到父亲的时候,他正坐在医院走廊上的塑料椅上,拿出一根烟点燃,大概是又马上想起医院内是不允许抽烟的,又急急地掐灭了丢进边上的垃圾桶,随后将脸埋在掌心里,一副颓然不知所措的样子。
其实她的父亲还很年轻,她出生的时候他不过二十来岁,如今五十不到,正是男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可待她走近了看他,却发现他鬓角已冒出不少白发。
心紧了紧,可还未等她回过神,他就似察觉到有人走近般,抬头望了过来。
见是她,有那么一刻,李涟漪可以肯定,她在他眼里看见有波动的光,但转瞬即逝。他仅是站起身来,淡淡的道,“回来了,你妈现在已经转到重症病房观察,暂时没事了。”
她悬了很久的心终于稍稍落下,嗯了声,又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妈怎么会突然……”虽然母亲以前的情况也并不容乐观,可那毕竟……怎么会突然病危?
李腾飞顿了下,冷硬的面容出现一丝裂纹,似有些烦躁的,他道,“服用安眠药过量,导致呼吸和心肺功能出现异常,还好发现得早。”
李涟漪抿紧了唇。
又听他道,“我以为自那次过后,她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事情……”
一股烦躁不耐就这样生生地窜出来,她打断他的话,“任何一个女人遇上了那样的事,都会崩溃的!”撩撩唇角,她看着眼前这个愣住的男人,语带讥讽道,“而妈只是做出了寻常女人的反应罢了。”
良久,李腾飞才慢声道,“涟漪,你还在恨妈妈和……爸爸吗?”他的神情有些戚然,看上去竟要比实际年龄要老上好几岁。
此刻李涟漪几乎连抬眼皮都懒得欠奉,淡淡说道,“什么恨不恨,再怎么说你们也是生养我的父母,恨爹妈是要挨雷劈的。”有些父母总是这样,以爱之名义伤害子女,但本身却浑然不觉,或许直到死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可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说不清楚。或许本该就是这样的。是冥冥中已安排好的命运,所有一切在还没发生的时候就已注定,怪不得其他人。
下午六点左右,她的母亲终于醒过来。其实抢救过来后本就不需住重症病房的,只是李腾飞执意要求,院方也只能照做。
李涟漪心里明白,父亲是担心母亲的罢,他害怕失去她,所以竭尽所能的近乎惶恐的想要留住她。
可有些东西,不是单这样就能弥补回来的。
她的母亲,宋轻蝶,当年风光无限的香港电影巨星,在二十一岁那年荣获影后称号后毅然隐退,出人意料地下嫁给一个事业刚刚起步的毛头小子,曾一度掀起轩然大波。而今,她已经在精神疗养院接受强制性治疗长达四年。
她睁开眼睛时,李涟漪守在她病床边已有一个多小时。此时日影西斜,天空中流动的薄云逐渐被染红,暮色笼罩下来,有橘红色的阳光撒进病房,暖暖的映在两人脸上。
宋轻蝶的瞳孔慢慢清明,待看清了床边的人时,眼睛有东西开始发亮,干裂的唇轻启:“涟漪?”很平常的,并不像时隔四年后才再次见面该有的语气。
“嗯,妈,是我。”李涟漪握住她蜷曲的手指,心莫名地有点酸,记忆中母亲的手是不沾阳春水的,像青葱般细嫩好看。可现在已经布满细细的皱纹,有点干巴,摸上去还有些粗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渴吗?要不要喝点水?”她放开手指,起身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清水。
却见宋轻蝶蓦然慌张起来,瞳孔迅速放大,抖着声音迅速缩进被子里,“涟漪,这是哪里?有药水味……是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打针!”
李涟漪拿着杯子的手僵了僵,片刻,她坐到床边,对着已明显受惊的母亲,以诱哄的口气轻声说道,“好,不打针,妈,来,我们喝水,喝完水……”她稍稍停了下,继续道,“我们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