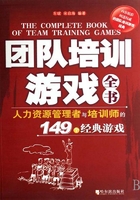那日回到含鸾殿,乳娘见到我甚是惊讶,我说了声,“晦气!”便进内室换了一身衣裳,铜镜中,又是那个桃腮泛红,眉俏眼魅的沐雪琉了,只是脸上多了几道伤痕,我也不甚在意。乳娘自然注意到了我的手受伤了,她默默拿来小药瓶,然后抓住我的手,“公主,忍一下,怕是脱节了。”我点点头,然后,一瞬间的苦痛过去,我额头渗出冷汗,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乳娘笑了,“公主,你真是个特别的孩子。”话落,低头娴熟地帮我包扎,她的动作很快又很熟练,我不禁问道,“乳娘,你过去一直受伤吗?”
不知为何我从她眼中看到什么一闪而过,她笑了笑,“在宫里待多了,受些皮肉之苦是在所难免的,也习惯这些了。”我点点头,不想揭乳娘的伤疤。
“但是乳娘我一辈子,还是有人对我好的。”她眼睛闪着,“为着那个人,我做什么都可以。”我看着她,“乳娘,你说的是母后吧?”那个人,一定是母后。乳娘愣了一下,笑道,“是啊,尹妃娘娘对我,真的无可挑剔。”
此时,翠儿从外面莲步进来,“公主,方才有人从曲溪林苑送来了这个。”她摊开手掌,是一条长长的锦盒,我打开后,发现里面竟是一株血人参!我睁大了双目,“曲溪林苑?那不是,宜妃娘娘居住的别苑?”我当时觉得事情有些奇怪,据说血人参长在雪山高原,当今皇朝只有凌家拥有,那么,这一株,又何来?
“既然宜妃娘娘有这个心,我们就收下它吧,就当是欠宜妃一个人情,公主,难得在宫中有人愿意伸援助之手,何乐而不为呢?多一个朋友,总是好的。”乳娘的话句句有理,加上当时我急于母后的病,于是没有往更深处去想,让翠儿将人参磨碎了入药。当第二日晨曦微露的时候,母后睁开了双眸。
那些日子里,我悉心陪伴母后左右,但始终有个心结,就是凌夏。我不知这些日子过后,他对我是否依然避讳,然而做错事情总是要承认的,那是我自小从母亲那里接受的为人之道,但自那日碰见他与夭华在一起,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一眼。
花开花落,转眼竟然已是两个寒暑,母后身体早已恢复,在此之间,我曾踏足曲溪林苑,也终于见到了苑中的主人,宜妃。宜妃清新淡雅,像朵水仙,眉骨秀丽,不掩脱俗之色,大家风范,见我第一眼,她与我皆一愣,她说,我简直就是她年轻的模样,我们一件如故,甚是投缘。宜妃娘娘膝下无儿女,当年的一跤,摔掉了她在父皇面前的宠爱,也让她从此静心呆在林苑,不问他事。
“那株血人参,是当年刚进宫时,陛下待我踏雪,我留下的,这么些年,我仍然保存着。”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双目凝望远方,似乎在回忆某些美好的往事。宫中的女人,悲哀在此。
皇朝并非一派安然景象,从边关不断传来消息,似乎正在战争。母后知晓这些消息时叹了口气,“又要开始了。”
那年正月,边境骚动不断,远在南方都城的父皇坐立不安,整个皇宫都戒备森严。而我呢,天天面对铜镜中的自己,越发的秀美,察觉自己身体的变化,母后感叹地望着我,让我把头靠在她膝上,说道,“琉儿,我的琉儿长大了。”
那日傍晚,我从曲溪别苑回含鸾殿,乳娘一见我就迎了上来,“快点,公主,陛下召集所有宫人还有臣子去增辉殿,听说是给凌将军送行,我到处找不着你。”
我一愣,为凌将军送行?“凌将军,要去哪?”
“去边境,打仗。”乳娘接着说道,“听说他们凌家除了女眷,男丁都要从军,跟着队伍去边境。”我没有听乳娘说完,提着绸裙,飞奔进了含鸾殿,傻傻地坐在铜镜前,许久我才发现自己居然流泪了。那一刻,我揭开了埋在心里许久的感情,原来,那个初见时笑脸迎人,温文有礼的少年早已驻足心底。而此去经年,又何时才能想见?误会未解,何时才能解开?
乳娘不知何时已经来到我身后,“公主,你怎么了?”她从镜中看见伤感的我,“如果不舒服,我让翠儿通报一声,咱们不去增辉殿了,反正就是饯行。”
“不,我要去增辉殿。”即使远远的,看着他,知道他此时安好,也足以,至少,我还可以期待着下一次的见面。我换好华服,纤纤细腰裹于绸缎之中,乌发缀上我最喜爱的琉璃,我缓缓走出含鸾殿,走向增辉殿。
增辉殿已是座无虚席,我仰望着高高在上的父皇,他左边变坐的是云妃,右手边空出一个位置,我踏进殿内那一刻,感觉所有人都把目光放在了我身上,我想,凌夏也是吧,只要他知道我来为他践行就好。
我走过去像父皇行礼,然后坐在了母后的身边。
“琉儿,你去哪疯了?此刻才来?饯行大典都快开始了。”母后在一旁说道。
“今日,传朕旨意,奉命凌治淮将军为元帅,段重天段将军为副元帅,凌将军的长子凌琪为做护卫,次子凌夏为右护卫,即日起朝西京启程,但愿早日归来。”父皇坐在威严的龙椅上,大声且平静地宣读着他自己的旨意,城门外立刻响起了号角,这是士兵出征的号角,雄壮却又凄凉。
我的头往右瞥了一下,凌将军的脸甚是威严,我不明白,他为何一定要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都送上战场,却可以眉眼不动?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平静吗?
我正在沉思之际,父皇居然开口叫我,“朕的皇二女,多才多艺,舞文弄墨,舞剑骑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今日,可否赠一曲,以慰那些将要远征的将士?”父皇侧目望着我,眼含笑意,这是他第一次当着所有的宫人和大臣面前提起我。
我没有犹豫,一下子站起来,微微蛾首,“当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了殿中央,接过宫女给的古筝,席地而坐,将古筝放在腿上,开始拨音。“祭江”一曲,开始柔怀备至,到后来,山峦叠嶂,起起伏伏,哀婉悲壮,缠绵悱恻。我专心致志地看着那古筝,整个殿内只有我手指拨弄的音律,淡淡传出宫墙。
拨下最后一个音,我抬头注视周围。整个大殿内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