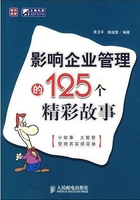世界如此之大,阑珊却觉得无容身之所。冷冽的风,一排排昏暗的路灯,路上的车子寥寥可数,阑珊沿着公路毫无目的地往前走,走得累了,停下来,往回看自己的走过的路,竟是一大片寂寞。
休息好了,又接着走,不断重复,像一个赶路的老妇人。
她的行李与钱包全在秦少毅办公室里,她是不可能回去拿的,更没有勇气往回走。在一个十字路的路口,她终于停下来了。
左右是路,前后都是路,她该往哪里去?
眼泪早已风干了,但双眼的酸涩让她十分不自觉,阑珊揉了揉眼睛,又似是擦亮眼睛选择对的方向前进。
可是何为对的方向呢?阑珊问自己。她一开始也以为自己找到对的路了,可以一往无前,但是现在才发现,现在又有一条分叉路。她犹豫了。
人可以错一次,但不能一错再错。
突然,一阵喇叭声把她魂魄勾回来。一辆车子停在她跟前。
车子里的降低了窗:“赵小姐?”
阑珊正在思量着,一时间反应有些不措,她看向他,眼神迷惘:“嗯?”过了一会她才反应过来:“顾先生?”
顾先生就是顾涵森,是北泰公司的总经理。
阑珊没有想过,竟在这里遇见他,更在这样的情况下遇见他。
阑珊想了想俯下身子,与车子齐平,向他请教:“请问这里的路怎样走。”
顾涵森微笑:“赵小姐迷路了?”说着又开了一边车门,邀请:“我载你一程。”
这个时候,又冷又累,阑珊的意志早被磨灭,她没有推托,娴熟地坐进副架,也许冻了太久,关节都僵硬了,动作变得不麻利。
顾涵森一踩油门,车子在寒夜里奔跑起来。
车子里的暖气开得足,早被冻得僵硬的阑珊打了个激灵,心酸突然涌上来。她别过头去,窗外一幕一幕的风景迅速地消逝,头疼欲裂。
车子在小区停下来,阑珊却大喊:“我不要回去。”
顾涵森不解,但他是个聪明人,比别人更快地联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夫妻争吵乃常事,他开解:“有什么不愉快的,就平心静气解决。”
阑珊突然沉默,头埋得很低。顾涵森以为她在哭泣,正不知所措中,隔了好一会,阑珊推开车门欲离去,身子背着他低低地说:“谢谢你。”语气里是强抑着悲伤,顾涵森怎能听不出。
阑珊往楼上走去,走了两三步,在楼梯后停下来,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远离,又从黑暗中走出来。
那个家是回不去的了。
她在A市无依无靠,而且现今身无分文,确实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只身在宁静的小区里游荡了,在喷水池前坐了一小会,风继续吹着,发丝在风中忧伤地飘着,无穷无尽的寒意遍布全身。
阑珊的脑海里响彻着一句话:我们一直在一起。
他说,他们一直在一起。
“要来一杯吗?”顾涵森递给她一瓶啤酒,又介绍:“这是好东西。”
阑珊望向那罐啤酒,默不作声,没有接手的意思。顾涵森用食指扣着拉环,一扯,啤酒“吱吱吱”地流出去,一地泡沫。
“哎啊,精华都跑了!”顾涵森感叹。
阑珊这时才发话:“借酒消愁愁更愁。”拒绝了顾涵森的好意。
顾涵森赞同,但辩驳:“逃得一时得一时埃”
阑珊又说:“可是逃不了一世。”
“那你又能逃得一世吗?”顾涵森截中她的要害。
阑珊这时才明白,顾涵森兜兜转转为着就是让她说出其中的道理。
阑珊讪讪一笑,避重就轻:“你怎么在这里?”
顾涵森不答反问:“你怎么又在这里?”
阑珊解释:“我没带钥匙。”
“那你打算一晚上坐这里当雪人?”
阑珊沉默,如果还有去路,她怎会坐在这里呢?
顾涵森是个聪明人,径自站起来:“我在这里有个小房子,装修好了,就一直没搬进去,若果你不介意就屈就你一晚。”
阑珊不拒绝,她没有路可走,看到一点曙光,自然扑过去。更何况,伤心归伤心,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像林黛玉,矫揉做作,难不成在风霜中寒蝉一晚上。
顾涵森口中的小房子真是不一般的“斜,面积比她家的更要大,阑珊一个人住倒显得十分空旷,连走路都会形成回音。单位坐北向南,冬暖夏凉,的确是好位置。全屋只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卧室,一个是书房。
卧室的设计简单大方,柔和的光线显得整个房间隐约中有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不明显但能真切地感觉到,真是物似主人形。双人床在卧室里静静地立着,床单印着蓝色的格子花纹,给人柔和的美。这张床是他睡的,阑珊倒显得为难:“这不是打扰了你吗?”
顾涵森微笑说:“这个房子,我偶尔才来祝”
阑珊心头大石落下,她多怕他说他一直住这里。
顾涵森为她打点好一切,凌晨两点多才离去。阑珊觉得十分不好意思,又叮嘱他:“路上小心。”
顾涵森笑笑,脸上一片温和:“早点休息。”
顾涵森走后,阑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夜无眠。风从窗户吹进来,吹开了窗帘,外面的天空一片幽幽的蓝。天开始发亮了,阑珊闭上眼,假寐了一小会,又醒了过来。在床上翻来覆去。借着微亮的天色,阑珊伏在窗台边,眺望着远处。
天刚刚苏醒,带着朦松的睡意。顾涵森的房子所在的楼层不高,从上望下去,清晰地辨清每个人的五官。阑珊的视线突然落在一辆黑色轿车上。车子停在对面的楼下,前后灯同时一辆,走下来一个人。
即使她瞎了,她也认得出那个人是谁,秦少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