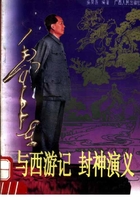哈代,厌世的,不爱活的,
这回再不用怨言,
一个黑影蒙住他的眼?
去了,他再不露脸。
八十八年不是容易过,
老头活该他的受,
扛著一肩思想的重负,
早晚都不得放手。
为什么放著甜的不尝,
暖和的座儿不坐,
偏挑那阴凄的调儿唱,
辣味儿辣得口破。
他是天生那老骨头僵,
一对眼拖著看人,
他看著了谁谁就遭殃,
你不用跟他讲情!
他就爱把世界剖著瞧,
是玫瑰也给拆坏;
他没有那画眉的纤巧,
他有夜鴞的古怪!
古怪,他争的就只一点——
一点灵魂的自由,
也不是成心跟谁翻脸,
认真就得认个透。
他可不是没有他的爱——
他爱真诚,爱慈悲,
人生就说是一场梦幻,
也不能没有安慰。
这日子你怪得他惆怅,
怪得他话里有刺,
他说乐观是“死尸脸上
抹著粉,搽著胭脂!”
这不是完全放弃希冀,
宇宙还得往下延,
但如果前途还有生机,
思想先不能随便。
为维护这思想的尊严,
诗人他不敢怠惰,
高擎著理想,睁大著眼,
抉剔人生的错误。
现在他去了,再不说话。
(你听这四野的静,)
他爱忘了他就忘了他
(天吊明哲的凋零!)
旧历元旦
(1928年3月10日《新月》第1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