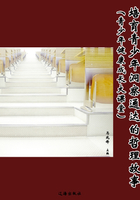弄月有些吃惊于她的话,又见她这般严肃,左右探望,确信没有旁人听见,才小声的道:“姐姐也发现不妥了吗?”
“入宫前,我就见过家中新欢不久的姨娘也是这样见了食物便呕吐不喜食,连着数日都是这样,请了村里的大夫来瞧,才知道原来是怀孕了。如今,我们娘娘也是这样,太医却说是肠胃不适,可喝了几日的药,也不见好转,会不会是太医把错脉了?”剪影与弄月是一道入宫的,所以交谊情分都比其她宫女来得深,所以也不怕对她说出自己的猜想。
弄月悄悄将剪影拉至无人的角落,小声说道:“姐姐可还曾记得,前两年,德妃也是这样月事迟了十数天也未来,见了食物也这样干呕,当时请了太医院的太医来瞧,那太医只说是肠胃不适,开了一剂药吃下,呕吐才止了。可是没过几日,便传出德妃小产的消息。”
剪影一听,红润的脸上浮着一丝白,黑眸凝着窗外那一池败落的清荷,有着深深的哀色,幽幽道:“如何不记得,当年我便是伺候在德主子跟前的,也因为这件事才被贬了去盥洗室清洗了一年的衣服。”
弄月却没有注意到她眼底的哀色,继续道:“还有一件,只怕姐姐是不知道的。那被皇上谪出宫的太医,当年也是经常为皇后娘娘瞧诊的。”
窗外——
层层浓重的铅云密布,沉沉压着整个纳桑后宫,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剪影恍然了悟的轻阖禽兽,道:“如今这一位张太医,也是经常替皇后娘娘请脉的,妹妹的意思是……”
“不知姐姐听说过宫中的一个传闻没有。”弄月如山林清泉般纯澈的眸中多了一抹谨色,“当年,皇后还是淑妃的时候,曾经小产,而自那之后,皇后便失去了生育能力。”
剪影深受震惊的摇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个传说的。”
“你没有听过,也不出奇。当年我是皇后寝宫凤翠宫里的宫女,才听了这一消息。那之后,恐是皇后怕我们将消息传出去,所以除了她贴身的几位,凡伺候左右的宫女都被贬出了凤翠宫。”弄月瞧着窗外的阴阴天色,仿佛在说很久以前的一个古老故事一般,眸地也多了一份凝重。
“姐姐您瞧,我们这皇宫之中,有几个怀孕后是能顺利生产的?便是顺利生产了,左右再瞧瞧小心如林贤妃,到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剪影了悟的点点头,亦知弄月这番话背后的含义。
“这些时日下来,我们都知道,梅妃娘娘性子是极和善的,待我们这些宫女又如亲姐妹一般。难道,我们便这样瞧着娘娘被人设计陷害吗?若娘娘腹中果真怀有龙胎,这焦三仙可是不能常吃的。”
弄月轻轻拍了拍剪影的手,一派的镇定自如,虽说她年岁上教剪影小一年,但若论起行事能力来说,倒比她强去许多。朝外挤了挤眼色道:“这冷香馆的宫女,除了姐姐您,我是一个也不信的,那个秋菊行事稳重,一眼便知是精明之人。喜儿虽俏皮活泼,待人真诚,但是我与她接触也不深,保不住内里是否含着城府。所以,方才我们的对话,姐姐你可千万别与她们二人说去。至于梅妃娘娘,妹妹想唯有找个时间,待皇上来了,委婉些将娘娘的事说与他知,咱们再请个太医院里不曾替皇后请脉的太医来瞧瞧。”
剪影见弄月这般有把握,又是这样清灵聪慧,促狭的笑道:“我自然是不会讲这些事情出去乱讲的,只是,从前竟不知,妹妹是这样冰雪聪慧的,若妹妹是个男儿身,指不定今日已经是我们纳桑的状元郎儿了。”
弄月垂下二弯眼帘,两颊生起如夕阳暮色般的红晕,啐了一口,道:“姐姐就使劲的嘲笑妹妹去吧,虽说这世上女儿便不如男了?世上男子皆是薄幸的,妹妹我才不稀罕那劳什子男儿身。”弄月在皇宫中所瞧见的不是东宫得宠便是西宫失势,多少不得宠的妃嫔日夜对烛暗自垂泪,小时候又听大人们说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所以便认定男子皆是薄幸,唯有女子至情至圣。
这一日,暗香吐了好几次,秋菊接了太医院送来的焦三仙来,弄月转身便将药水泼在屋外泥土地上,只说是已经服侍梅妃喝下,秋菊也没有起疑。
如此,过了几日,皇上来探视,却见暗香依旧食不下咽,并且面色青黄,心中忧心不已。剪影则接着机会带着喜儿和秋菊去盥洗室领衣服,只留了弄月一个人在跟前服侍着。
“香儿,吃了几日张太医的药也不见效吗?”御天宇扶着暗香在紫色海棠雕花椅上坐下,爱怜的瞧着暗香,她身上穿着一件乳黄团纱绣鹅黄锦长衣,更是衬得脸色青黄难看。心就像被人用极细的铅片划过一般,两行浓眉纠结成一线。
暗香连日来吐得极是厉害,又常觉头晕身子乏,这一刻见了皇上来,只得强撑着,努力的想要挤出一个微笑,却程一个比哭看着还让人难受的笑容,柔声道:“臣妾没甚大碍,只是见了这些吃食有些犯恶心罢了。皇上已经轻太医唯臣妾诊视,左不过在多吃两日药,便能好了。”
她是不忍皇上为她这样操心担忧的,她不过是些小毛病,皇上日理万机,此刻该好好休息才是。
“皇上,”一旁的弄月见时机到了,福了福身,上前二步道:“娘娘这病也有多日了,吃了药也总不见好。奴婢听说,太医院的御医,都是有自己擅长的一方病症医术,或许娘娘这病正好不是张太医擅长一方也未必。瞧着娘娘这几日身上如此不好,奴婢也极是焦心,奴婢斗胆恳请皇上再请一位御医来替娘娘瞧瞧,或许合二位太医之力,便能将娘娘的病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