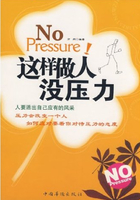1505年7月4日
晚上10点30分
斯道特海姆
乔纳森·瑞克林把身子紧紧地蜷作一团,缩在家里最黑暗的角落里。他的一只手屈成杯状,捧着一只小麻雀,另一只手抚摸着麻雀的小胸脯。小麻雀已经死了。今天早些时候,乔纳森在路边发现了它,见它用一只脚爪跳着,一只翅膀也折断了。每次遇到受伤的小动物,乔纳森都要把它们带回家里照看。这次他照常把受伤的小麻雀带回家,喂它东西吃,准备等它养好了伤,再将它放飞。这只小麻雀恢复得挺快,乔纳森当时以为它肯定可以再飞起来。不料他的继父回到了家里,又是喝得醉醺醺的,满身臭气,脾气火暴。他听到了小鸟唧唧啾啾的叫声后,就走到乔纳森跟前,二话不说,抢过小鸟,单手一用力,就把它捏扁了,顺手给了乔纳森一个嘴巴。
乔纳森瞅着这个称为继父的男人一屁股坐在壁炉旁边的一张粗陋的木头桌子上,活像一坨肉山。屋外,夏季的暴风雨肆虐着,刚从外面回来的他浑身透湿,如同落汤鸡一般狼狈。雨水顺着房顶上的裂缝不断地流下来,滴在地板上、桌子上,就连摆放在屋子中间的那张大床,也被打湿了一角。
乔纳森的脸上挨了一巴掌,如今依然火辣辣地疼痛。他擦掉脸颊上的眼泪,看着那个老畜生又举起已经见了底儿的大号啤酒杯,往嘴里面控着,想喝到最后几滴酒。男孩将视线从继父身上转向他身后的墙上,看到墙上映出他那扭曲的身影,不禁猛地吸了一口气。乔纳森已经怀疑好几个星期了,现在终于能够确定了。他心里想:“没错,他虽披着人皮,其实是头怪兽。”
“以圣安妮和圣母的名义,”这个满身皱巴巴的老家伙口里喷着唾沫星子,盯着自己的老婆,气急败坏地说道,“这小子已经六岁了,已经足够大了,玛塔。有比他更小的鼻涕孩儿都下矿井干活了,每周能赚进一两块银币呢。再看看你养的这只蠢货,他除了会弄回来半死不活的鸟儿之外,还带过什么东西回家?他这么不争气都因为他是你的崽子。”
乔纳森转脸去看他的妈妈,发现妈妈也正看着自己。突然,妈妈霍地从条凳上站了起来,身子直挺挺地站着。
妈妈想要干什么?要跟这头怪兽说话吗?妈妈此前跟乔纳森说过她有话要跟继父说。但现在可不是时候啊。妈妈你可千万别开口啊,谁知道这头怪兽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呢?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既然继父是一只怪兽,妈妈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冒犯他,因为怪兽是会吃人的。
怪兽吃人,这正是发生在乔纳森的亲生父亲身上的事。虽然妈妈坚持说在五年前的那次矿井塌方事故中,是矿井而不是怪兽吞掉了爸爸,但是大伙都这么说。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无论矿井深处是什么东西吃掉了爸爸和其他矿工,那个东西却没有吃掉继父克劳斯·雷斯涅,而是把他吐了出来。人们再也没有找到爸爸和其他矿工,这个克劳斯是唯一一个活着从塌方的矿井里出来的人。现在,乔纳森知道这是为什么了。怪兽们不会自相残杀、吃其他怪兽的。
塌方之后没过几周,克劳斯就娶了乔纳森的妈妈。妈妈曾经这样告诉他,说她是为了救他们母子俩才嫁给这个男人的。但是这话在乔纳森听起来更像是她在为她做过的什么不好的事情向他道歉,特别是在她说自己心乱如麻,如果在再婚之前多花些时间考虑考虑就好了的时候。
不过,妈妈在几天前对他说,她现在想清楚了,这就是她现在终于可以直面这只怪兽,敢于开口说话的原因。很快,正义将战胜邪恶,一切都会回到正轨上来;很快,那个她寄予了所有希望的预言就会开始变成现实了。到那时,这个浑蛋男人就再也不能伤害他们了。乔纳森注意到妈妈偷眼扫了一下屋门上方的储物架后部的包袱,随即站得更直了。
克劳斯一动不动地在听玛塔讲话,她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有底气。“他还是个孩子,雷斯涅先生,你看看他的样子。”妻子按照他的要求称呼他的姓氏。“乔尼(乔纳森的昵称),站起来。”她又向儿子使了个眼色,低声道。
乔纳森把死麻雀放到稻草上,从角落里站起身来,浑身发抖。玛塔伸手将儿子拉到自己身边,一只手搂着儿子的肩膀,让他跟自己并肩站在一起。
乔纳森瞪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他那长长的头发用肮脏的黄色头绳胡乱地捆扎着,几乎遮住了他的那张脸。乔纳森看得胃里一阵翻腾,他急忙攥紧拳头,屏住呼吸,努力克制着以免呕吐出来。他感到妈妈搭在自己肩上的手在颤抖。她继续说道:“他还太小。都怪你的那些故事,先生,你的那些关于矿井的故事吓得孩子好多夜晚都睡不着觉。”
仅仅是提到那些故事,就已经让小乔纳森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如有蚁爬了。他们家里只有一张睡床,一家三口都是一起躺在那张大床上睡觉的。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当他半睡半醒之时,继父就会在他耳边低声给他讲故事:那些矿井其实是无底的坟墓,专等着人来填满;天上打的雷是上帝在搬运天堂里的大石头,总有一天,天会塌下来,那些大石头就会掉下来,你会无处可逃,所有人都会被砸扁。
玛塔话音已落,克劳斯却毫无反应。
玛塔很紧张,五指的指甲都嵌入儿子肩头的皮肤里了,但她丈夫却一动不动,连身体都没有扭动一下。她继续说:“矿井会害死他的,雷斯涅先生,会像吞掉罗伯特一样吞掉他的。”这话刚一出口,玛塔就倒吸了一口冷气,没想到自己居然提到了前夫罗伯特的名字。乔纳森至今还记得五年前,妈妈当着继父的面提过一次爸爸的名字,结果就被他打折了三根肋骨,敲掉了两颗门牙。这是乔纳森孩提时代的最初的记忆之一。从那以后,除了在上帝面前和当着自己的面,妈妈就再也不敢在别人面前说起他的生身父亲的名字了,哪怕是小声说都不敢。
乔纳森的眼睛望着窗外,假装自己什么都听不到,真希望自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暴风雨越发猛烈和嚣张。狂风裹挟着暴雨狠狠地击打着他家的石灰岩墙壁。天空中电闪雷鸣,看来是准备好把天空撕开一个大口子了。一阵劲风冷不防顺着烟囱倒灌了下来,卷起壁炉里的炉灰,化作一小团烟云从炉膛里冒出来,在空荡荡的屋子中央翻滚,变幻着姿态。过了一会儿,烟灰落定,稻草铺就的地面上像盖了一层肮脏的黑雪。而烟气则在壁炉的四周盘旋,随后飘升到房椽之上,寻找着出路。一只老鼠噌地一下掠过地面,贴在墙边,一转眼就消失在一小堆发了霉的干草之下。乔纳森好奇地想,那只老鼠是不是知道一条通往屋外的秘道?
克劳斯将空酒杯倒向自己张开的大嘴巴,居然控出了一滴啤酒,不过也是最后一滴了。看到继父轻轻地将酒杯放到桌上,乔纳森浅浅地吸了口气,越发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他感受到了空气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克劳斯慢慢地牵动一边嘴角,超大的嘴巴向旁边一咧,露齿而笑,嘴角旁也随之出现了皱纹。但他的笑容一现即隐。“你过来,小子。”
玛塔轻轻将儿子向前推了推,乔纳森向前挪了挪,垂下眼睛看着地面,双手背在身后,绞着手指。
克劳斯用鼻子粗重地吸着气,然后咳嗽一声,一口痰吐在了地上。“你还记得天上是怎么打雷的吗?”
“雷斯涅先生,别这样。”玛塔祈求道。乔纳森从来没有听过妈妈用这样一种语气说话。
克劳斯从桌子旁突然跳起,乔纳森愣了一下,没想到一个像继父这样肥胖的男人居然能够动作那么迅速。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克劳斯猛地向妻子冲了过去,她还没来得及作任何反应,就被丈夫一把揪住了头发。乔纳森闭起了眼睛,不敢再看。没有人说话。只听得条凳砰然倒地的声音、一声急促的呼吸以及头发被撕扯掉的闷响——那声音使乔纳森联想起地里的草被镰刀割掉的情景来。但是,即便如此,妈妈却没有发出一声尖叫。她挨打的时候就算再疼,也从来不会叫唤出声。那个野蛮的男人把她拖到屋子的另一边,打开家门,将她扔到屋外,正落到房前的粪堆里。
克劳斯未及关门,一阵风夹杂着雨就吹了进来。克劳斯“咣当”摔上门,“哗啦”一声插上门栓,转身回到屋内,把倒在地上的条凳挑起来放好,又一屁股坐了上去,表现得好像他刚才不过是用指头弹开了一只跳蚤那样。乔纳森浑身颤抖,体若筛糠,努力地抑制住啜泣声,心想这个怪兽男人接下来肯定要来吃掉自己了。他知道妈妈这会儿一定正趴在门边,听着屋里面的动静,并为他祷告。这至少会带给他些许安慰。有了妈妈的祷告,也许自己被吃时不会觉得那么疼呢。
克劳斯抬起头,梗着脖子看向一侧,见乔纳森那小小的身躯站在自己的面前。老家伙用力摩挲着他那红红的蒜头鼻,然后用拇指和食指使劲挤捏。乔纳森偷偷抬起眼睛飞快地看了一眼他的继父。他脸上纵横遍布的皱纹令乔纳森吃惊。妈妈告诉过他,矿工都短命,大多数活不过40岁。但是克劳斯·雷斯涅今年都已经42岁了。只有怪兽才会活这么久。
一记炸雷震撼着他们的房子。透过脚下地面的颤动,乔纳森分明感受到那雷的威力之大,他害怕得缩了缩肩膀。克劳斯再次咧开大嘴,露齿奸笑,从桌上剥下的一根木刺,拿来剔着牙缝。他身体后仰,打了一个响亮的嗝。
然后,低哑的声音从他的嗓子眼里挤出来:“你这小无赖,我看你就是个笨蛋!不对,你还记得天塌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样,整个世界就会变得像三号矿井的隧道那样一片漆黑。看来你小子挺聪明的啊。那次闪电,整个天空几乎要裂开,还有那雷声,就是我们听到的大石头滚动的声音,这些你都记得。真是奇怪,那天晚上那些大石头居然没有滚下来,没有从天上的裂缝里掉下来砸在我们身上,就像砸住三号矿井里那些可怜的死鬼一样。当然,你挺聪明,晓得他们为什么会死。”乔纳森当然知道:是怪兽们把他们吃掉的。不过他可不会这么说出来,因为如果照实说了出来,他就没办法继续假装不知情了,那继父就会当场把他给吃掉的。
“你妈说你年龄还小,不能当矿工,我可不这么看。照我说,男孩子只要能提得动水桶就能提得动矿石。这才是上帝的真理。”他大声吼叫着,好让门外的玛塔也能听到。“有比你小的男孩已经在矿上干活了,而你这五年一直在靠我的努力工作来养活你。看这边,看着我!如果你想继续待在这个家里,你就得自己赚钱交你的伙食费。我手里得有钱,小子,你得去干活给我把钱赚回来。否则的话,门就在那边,你就给我滚。离开了这个家,我看你怎么活?”
乔纳森不知所措,只会站在那里不住抽泣。要在斯道特海姆泥泞的大街上流浪,他可想象不出来那种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而且除了斯道特海姆,他所知道的其他城市都是继父在故事里提到的鬼村庄,在现实中他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这个时候,他特别想去问妈妈他该怎么办。他真希望自己年纪再大一些,如果他现在十岁,那么面对眼前的情况,他就会知道问题的答案,也会知道该做些什么。
“怎么样?想好了吗?”老家伙逼问道。他的话音刚落,“刷拉拉”一道闪电就撕裂了天空,紧随其后的雷在他们的房子周围炸响。由于雷距离他们的屋子实在太近了,以至于屋子里的空气都跟着噼啪作响。屋外传来妈妈的尖叫声,乔纳森立刻冲向房门。天空的霹雳声让克劳斯一时间失去了防范,对乔纳森的突然行动反应得慢了半拍。即便如此,他还是在乔纳森把门栓从插销里滑开的那一瞬间抓住了他,把他猛拉回屋子里。乔纳森一个踉跄跌倒在地,脑袋撞在条凳的凳角上,破了个口子。
就在这时,门突然大敞四开。一个年轻男人站在门口,沉重地斜靠在门框上,耷拉着脑袋,一只胳膊搭在玛塔的肩膀上,支撑着身体的重量。他的衣服上面满是泥巴和撕破之处,但看起来质料很好。乔纳森看到他这个样子,知道他受了伤。雷斯涅则依旧是满脸涨红,暴跳如雷,他一脚把继子踢翻在地,紧跟着朝他的腹部补了两脚,又狠狠地一脚踢在他的头上,将他踢得飞了出去,跌落在墙角里。“乔尼!”玛塔撕心裂肺地尖叫着扑到儿子身边,俯身捧起儿子流血的头,放在自己的臂弯里。乔纳森抹了一把流到眼睛里的鲜血和眼泪,紧紧地抱住了妈妈。
克劳斯转向那个不速之客,吼道:“这里没你的事!出去!给我滚出去!”同时伸手想抓住他的斗篷,却笨手笨脚地落了空。陌生男子以手捂头,踉踉跄跄地倒退,身子靠在敞开的门上。
克劳斯原地转过身来,想把妻子玛塔拉开,但是继子乔纳森紧紧拽着她。于是克劳斯挥起拳头狠狠地打她,又揪住她的头发将她朝屋子里面扔了出去,逼得她不得不松开儿子,被丈夫一掼之下,从屋子这边甩到那边,撞到房门旁边的墙上又弹了起来。还没等克劳斯跟过去继续打她,年轻男子早已冲他扑了过来,把这个五大三粗的矿工拉得转了个身,将他牢牢摁在了墙上,前臂紧紧地卡在他的咽喉,用力之猛,甚至胳膊都陷进了对方下巴底下的肥肉里,使他动弹不得。“你再敢欺负他们!”他逼视着克劳斯的脸一声怒吼。克劳斯震惊不已。
也许是刚才用力过猛,使脱了力气,触动了伤口,年轻人拼命眨着眼睛,又甩了甩头,试图保持清醒,口中继续威胁道:“你要是敢再动这女人和这孩子一根指头,我就……我就……”他抬起左手一抚额头,原本紧紧钳住克劳斯的手放松了,双膝一软,便向后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砰”的一声重重地瘫倒在桌子旁边的长条凳上。
克劳斯一见年轻人晕倒了,立时又找回了自己的勇气,他从墙上抓过一柄沉重的手杖,高高举起,朝着入侵者的头上狠狠地砸了过去。
“不!”乔纳森耳畔听到他的妈妈惊声尖叫,旋即见到一个身影飞快地闪到继父克劳斯身后,紧接着只听得一声令人厌恶的脆响——“咔嚓!”乔纳森定睛再看,但见继父手中的手杖滑落了下来,人也跟着瘫倒在地,不省人事,脑后鲜血直流。在继父身后稍微靠左一些的地方,站着他的妈妈。铁火钳从她的手中跌落到地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对不起。”玛塔走回来照顾自己的儿子,嘴里面不知道是在向谁道歉。此时,昏迷的年轻人悠悠醒转,他从条凳上坐起身来,愣愣地瞅着倒在地上的那个男人。“一时半会是叫不醒他的。”玛塔对他说,“明天早上他就会醒过来了,啥都不记得。你来帮我挪一下他。”于是玛塔抓住克劳斯脚上满是泥巴的靴子,年轻人拽着他的两只手腕,两人用力把他拖到茅屋最里面的角落里,把昏迷不醒的他安置在一堆稻草上。
随后,陌生男子关上屋门,坐到桌子旁边,对女主人说:“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玛塔正跪在儿子身旁,瞥了他一眼,没吱声。“我该做下自我介绍。我叫马丁,马丁·路德。谢谢您帮助了我。”
“玛塔·雷斯涅,该我向你道谢才对。”女主人一边抱起儿子,走向屋子中间的大床,一边答道。
“孩子怎么样了?”
“你说他吗?哦,没事,这孩子很快又会活蹦乱跳了!”玛塔说着,笑向自己的儿子。然后她找出一罐药膏,打开盖子,用指头蘸着药膏,轻轻地抹进儿子头上深深的伤口里。乔纳森疼得“哎哟”一声叫了起来,脑袋下意识地偏向另一侧。“嘘,嘘。”妈妈轻声地安慰他,给他唱起一首摇篮曲,手中不停,从炉边的一个袋子里抽出一些窄布条,给儿子包扎伤口。
乔纳森感到胃里一阵翻腾,很不舒服,但是只要侧身面向炉火时就会感觉稍微好一点。“你睡一会儿吧。”他的妈妈语声温柔地说,将一床粗毛毯子盖在儿子身上,并在他的额头上印上一吻。乔纳森乖乖地闭上眼。但当玛塔从床上起身时,他又睁开了眼睛,看着妈妈拿着药膏走到坐在桌子旁边的路德先生面前。
“您总是对陌生人这么好吗?”当玛塔把布条摊开在桌子上的时候,年轻人问道。
“您救了我和我的儿子,路德先生。那么您呢?您总是对陌生人这么好吗?”玛塔把两根手指蘸到药膏之中,“现在,让我看看您的伤口。”
乔纳森本来已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却被继父一阵特别响亮的鼾声吵醒。他睁开了双眼,见继父还在角落里呼呼大睡呢。他的妈妈正坐在条凳上,在路德先生的旁边。路德头上缠着一圈绷带,妈妈正在处理他眉弓处的一个大口子。
“这孩子好奇心太盛,总是异想天开。”乔纳森听到妈妈声音平静地说,“他爱想事情,也想学习识字。但是雷斯涅先生不想让他读书,而是想让他下矿井干活赚钱。请问,”妈妈不给路德先生回应的机会,紧接着说,“您说的闪电是怎么回事?”
乔纳森在床上转了一下头,以便能听得更真切。只听路德先生说:“请您再说一遍。”
“在外面我扶您起来的时候,您说了一些关于闪电的话。”
“哦,抱歉。我还有些晕呢。我正在去爱尔福特的路上,暴风雨来了,一道闪电把我劈倒了。”
乔纳森能看到他的妈妈侧过头去端详她的客人。“我还从没碰到过被上帝之火击中之后还能好端端地活着讲事情经过的人呢。不过,我父亲倒是认识一个这样的人。我父亲说闪电会进入人的血液和大脑,把人身体里面的东西都煮熟了,于是他的头脑就跟以前不再一样了。我父亲说,被天打雷劈,要么是出于上帝的审判,要么是来自于魔鬼的祝福。”
乔纳森看得清楚,路德先生的一双眼睛,看起来像是两颗闪闪发光的黑宝石。只听他说道:“我听到上帝说话了。后来是圣安妮救了我。”
“嗯,有人在注视着您,这倒是真的。”妈妈说。她让他的头稍微后仰,以便把药膏涂在另一处擦伤上。而路德先生则在看着房门上面的什么东西。房门上悬着一个高高的架子,上面放着一只布口袋。乔纳森根本不用挪动身体就能看到那只袋子,只见袋口已经松开了,里面露出一本书的泛黄的书页。乔纳森记得妈妈是前天晚上把那只口袋带回家来的,却不准他看,甚至连用手碰一下都不行。那本书有魔力,妈妈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我看出来您也是个有文化的人。”路德先生开了口。
“嗯?”玛塔继续清理着他的伤口。
“我是说那本书。”
玛塔闻言向房门上瞥了一眼。“我的前夫教过我识字和读书。”她平静地说。
马丁·路德将身子坐直了一些,向一旁昂起头,双眉一挑,问道:“真的吗?那么您从您所读的书中有什么收获?”
“秘密。”玛塔回答。她的一边嘴角微微上翘,似笑非笑地接着说:“那是一本图画书,没啥了不起的。画的都是海图和星图。”
路德先生点了点头:“我能看看吗?”
玛塔闻听此言,笑容立刻消失了。她低下头来,专注地把手指上余剩的药膏刮到药罐口的内壁上。“那可不是《圣经》,先生。”
“我只是想翻翻。”
“嗯。”玛塔轻声一笑,随即咳嗽了一声。她抬眼瞥了瞥那本书,又回过头来看着她的客人,严肃地说:“祸事就要来了,路德先生。但不是现在,不是立刻就发生。但是确实有祸患要来了,降临到所有做错事的人身上,降临到那些夺取了不属于自己东西的人身上。”
路德先生听了玛塔的话,柔声说道:“祸事是免不了的,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说话间,他身体前倾,将两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但我不认为祸事将至。我认为祸事此时此刻已经临头了,而且是我们发现的。我们径直走进了一场风暴的中心,就像今天下午我的遭遇一样。但是上帝会保护我们……”
玛塔抬起一只手,打断了年轻人的话。她慢慢伸出手去,抚上他的脸颊,喃喃说道:“追云者……”妈妈说话的声音太轻,乔纳森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不过他能看到路德先生皱起了眉,似乎是不明白妈妈的意思。
玛塔俯身向前,离得路德更近。“那么您是个受过洗的基督徒?”
路德犹豫了一下才答道:“是的,我是。”
“哪一天受的洗?”玛塔继续追问。
“圣马丁节那天。怎么了?”
玛塔定睛看着路德,没说什么,只是以手搓了搓前额。“很好。既是这样,”她飞快地说,“我会给您看那本书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警告您,知道真相是要付出代价的。您记好了。”说着话,她“噌”地站起身,并扶着路德从座位上站起来。随后,她拖过路德刚才坐着的那只条凳放到门下,登着凳子站了上去。“祸事很快就要来了,”她一边伸手够向房门上方的搁物架,一边说,“星星就是这样说的。”
玛塔小心翼翼地从破布袋里拿出那本书。但见已经破烂的书边锈色斑驳。老旧不堪的牛皮封套随着玛塔的触碰而开裂,露出了里面的木质书皮。玛塔坐在桌旁,打开书本,翻到做了标记的那一页。尽管视线有个角度,乔纳森还是能看清楚书里面的内容。那一页上是一幅木版画,上面画着一条鱼,有些东西正从鱼腹中流出来。
“这是什么,雷斯涅夫人?”路德先生疑惑道。
“这是一个预言。这一天会到来。就是在双鱼座回归本位的那一天,一切不公平都将被纠正过来。”玛塔看着她的客人,继续说道,“而您就是这个预言的一部分,路德先生。”
“什么?”
“您就是这个预言的一部分。今天晚上我才刚知道,就在今天晚上。随您喜欢还是不喜欢。您将是这一切的开始。”玛塔手指木版画,“星相就是这么说的。”
“星星可不会说话,雷斯涅夫人,而且我也不会站出来挑起一场战争的。”乔纳森看到他的妈妈将书合上,推到了一边。“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上帝能够借着闪电说话,却不能借着星星说话。”路德先生张开口想要说些什么,却欲言又止。玛塔慢慢站起身,把书塞进布袋里,放回到门上的搁物架上,并按原位放好。接着,她封好药罐,放回原处,再从门旁的一个挂钩上拿起一条披肩。在这个过程中,马丁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您的伤口还需要包扎,可我这儿没有那么多布条做绷带了。”玛塔说着话把披肩裹在肩上,打开房门。“外面雨小了一些。我这就跑到克莱拉家去要些布条来。”乔纳森本想开口叫妈妈不要去,但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出来,妈妈已经走了出去,并在身后关上了家门。乔纳森只好转眼瞅向路德先生,见他还是呆坐在那里,瞪着关上的房门。
乔纳森将双手紧紧抱在胸前,蜷缩在床上。马丁抬起眼睛看了看房门上方的搁物架,然后慢慢从条凳站起来,移动脚步,准备离开。
“哎!”乔纳森忍不住叫道,从大床中央坐了起来。
路德先生急忙转向他,说:“你妈妈出去找绷带去了,很快就会回来。”
“我头疼。”乔纳森说。
“我知道。”路德先生一边柔声说着,一边走到男孩床前,“但是你知道什么对缓解头痛最有效吗?那就是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来,现在快躺下。”
“别那样对我说话,别把我当小孩子看。明天我可就满六岁了。”
“啊,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您叫马丁·路德。我听到妈妈说话了。”乔纳森重新躺倒在床上,嘴里没停。
“没错,”马丁微微一顿,“不过你可以叫我马丁,乔纳森。”
“您居然知道我的名字。”乔纳森假装平淡地说,模仿着大人说话的口气。
“我还知道很多秘密呢。”马丁瞟了一眼乔纳森的继父所在的方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见他依旧鼾声如雷,这才回过头来对乔纳森唤了一声:“乔纳森,”马丁故意装出威严、高贵的贵族模样,压低声音,拿腔作调地说,“下面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你瞧,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六岁是承诺的年龄。”
“嗯……”乔纳森点头表示同意。
“所以,”路德先生接过话来。但在继续说话之前,他抿起嘴唇,清了清喉咙,打起了官腔,这才往下说,“我,马丁·路德,学者,委托你,乔纳森……”
“瑞克林。”
“乔纳森·瑞克林,遵守如下誓言:从今往后,要顺服和善待自己的妈妈,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你同意吗?”
男孩乔纳森把毯子拉高,掖到下巴底下:“是的,先生。”接着又问,“您是巫师吗,先生?”
“巫师?哇,对你这样一个小小年纪的男人来说,这可是个大词啊。不。”马丁笑道,“但是,我很快就将按照上帝的旨意成为一名修士。”
“修士知道秘密吗?”乔纳森问。
“啊,那是当然。现在睡觉吧。”马丁把毯子在孩子肩膀四周掖了掖。
“能告诉我一些秘密吗?”
“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不过首先我得先知道它们。晚安,乔纳森。”
“马丁?”
“嗯?”
“您为什么要去当修士?”
马丁将斗篷系紧,回答说:“因为我也有一个诺言要遵守。现在,晚安吧。别忘了你的诺言啊。”
“我不会忘的。”
于是马丁起身迈步,朝门的方向走去。经过桌子的时候,他从腰间的钱囊中掏出两枚硬币,留在了桌子上。然后他走到门前,打开房门,抬腿跨出门去,随手轻轻地关上了身后的房门,挺身走进细雨当中,向着爱尔福特的方向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