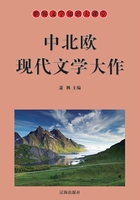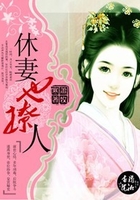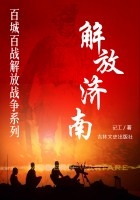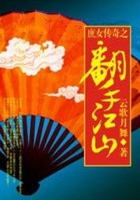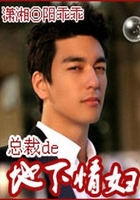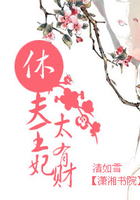“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
——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
钱理群
我们这里一说起就是导师导师,不称周先生,也不称鲁迅先生,你或者还没有机会听到,这声音是到处响着的,好像街上的车轮,好像檐前的滴水……
——萧红《致许广平书》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
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许广平《追忆萧红》
他与她,是如此的不同,又这般的相近。
当萧红用她纤细的手,略带羞涩地扣着文学大门的时候,鲁迅已经是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他们两人“历史性地”相见了。有人说,这是“左翼文化界一方面的主帅”和“游击战士的会师a”,毋宁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父”与“女”两代人的会合。——他们之间整整相距了三十年;但却有着最亲密的文学的血缘关系。
这是会见时许广平(一定程度上也是鲁迅)眼中的萧红:一个刚刚冲出封建家庭,在“五花八门的形形色色的天地里”有些像“张皇失措”的“娜拉”b。这观察是准确而深刻的:萧红正是鲁迅所十分关注的“走后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娜拉”。萧红的悲剧命运至今仍然牵动着国内外许多人的心,其原因大概也在于此c。
鲁迅同时也看出了在萧红的“柔弱”、“稚气”的外表下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d。“命薄于纸”却“心高于天”,正像茅盾后来所说,萧红在文学上是有“远大的计划”,并且充满“自信”的e。
请看,就是这位爱穿红衣服、扎着两根辫子的东北姑娘,竟是这样的出语惊人: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f这是真正的“萧红式”的语言:倔强,有气魄,又有几分无邪的天真,以至女儿的娇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她与鲁迅之间在思想、艺术追求上的相通。丁玲曾经感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g;在“寥如晨星”的女作家中,和现代文学的宗师鲁迅最为相知的,竟是最年轻的萧红。
一
请看这一番议论:“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h这思想,这魄力,简直就是鲁迅的;它使我们想起了鲁迅那历史性的召唤:“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i——然而,说这话的却是萧红。
不言而喻,鲁迅与萧红有他们自己的“小说学”。这是鲁迅的“自白”:“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而“难到可怕”的汉字、“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中国的百姓“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沉默“已经有四千年”!“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j……
这是一个面对世界新潮流的冲击、而“未经革新的古国”的觉醒了的战士灵魂深处发出的伟大叹息!这里有着最深沉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有着对阻碍民族觉醒的几千年旧传统不可抑制的憎恨;有着因民族的可怕沉默、麻木而产生的巨大民族危机感,更有着对民族未来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感。由此,产生了鲁迅式的文学观、小说观:以自己的笔权当人民的“代言人”,“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小说作桥梁,沟通人们互相隔绝的魂灵;作号角,唤醒麻木的魂灵,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一旦民族屈辱的时代结束,新的“民族魂”形成,沉默的人民自己开口,这样的文学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将“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
这文学观、小说观显然不属于鲁迅个人。它是列宁所高度赞扬的二十世纪“亚洲的觉醒”的伟大历史潮流的产物。l当然,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会出现这种文学观的,它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观息息相通,对中国和东方传统文学观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它代表了中国以至东方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
在中国,鲁迅的这种“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小说观)及文学,影响了整整几代作家。鲁迅在评价萧红的《生死场》时,一再赞扬萧红的作品沟通了“住在不同世界”的人们,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预言它将扰乱“奴隶的心”
鲁迅正是从“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这个角度充分肯定了萧红创作的思想和文学价值。当然,这是真正的“知人”之论。
二
文学观的变化必然带来题材的选取、人物形象的设置及塑造方法等一系列的深刻变化。作家着眼于整个民族的灵魂的改造,他们所关注、研究的中心,就不再是脱出社会常规的个别的、奇特的、偶然的事件与人物,而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鲁迅与萧红作品中的社会风俗画的描写,是一般读者都能注意到的,但人们往往把这看作是增加作品色彩的一种手段,而不能从作家对于生活的独特认识和作家文学观的全局去认识它的意义。人们也往往把这种风俗画的描写局限于富有地方色彩的风光习俗,而忽视了巴尔扎克所说的更“基础”的东西:民族的生活方式,“人的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n,这正是鲁迅、萧红笔下的社会风俗画的主要着力点。鲁迅把这种描写散落于全部情节之中,而萧红在《呼兰河传》等作品里,则不惜将情节的发展中断,进行集中的描绘。这确实有些破格,并且因此受到责难。萧红却置之不顾,她有着自己的追求;也许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萧红创作的主要特色。
萧红用她那忧郁的大眼睛,凝视着她的故乡人民“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o,用她那敏感的心灵捕捉着,捕捉着……然而,她看见、她捕捉到什么呢?没有,什么也没有。“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甚至于没有好奇心”p(这全是鲁迅的话;他们对生活的感受竟是这样相近!)。没有过去——“凡过去的,都算是忘记了”;没有未来——谁又去想它呢。生活失去了目标,“活着”——就是一切:“天黑了就睡觉”(连作梦也“并不梦到什么悲哀的或是欣喜的景况”),“天亮了就起来工作”;“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生,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就老了,“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死了,哭一场,“埋了之后,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q——这就是我们古老中国普通人民的生活方式。死寂到了失去一切生命的活力,冷漠到了忘记一切生活的欲望,一个人,一个民族到了这种地步,距离“死期”不就不远了么?于是,作者,以及我们读者都感到了一种“死的恐怖”!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捕捉到如此惊心动魄的东西,这不仅是艺术的才能,更是思想的才能;而这一切的原动力又是与民族命运生死与共的,刻骨铭心的爱国之情!
在死水一般的生活里,唯一起着作用的是历史的惰性力量。呼兰城的子民们正是无怨无尤地在祖先给他们准备好的“成规中生活着”r。稍有“反常”,就不能为人们接受,就连那小城里的牙科医生广告牌子上的“牙齿太大”,就使得人们“害怕”而不敢问津了。对统治古老中国的历史的惰性力量,鲁迅作了广阔的探索与开掘,萧红却只集中于一点,“不把人当作人”。一生受尽坎坷欺辱、创伤累累的萧红,对于“人”的尊严,有着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哪怕是最微小的无心的贬抑和伤害,都会引起她心灵的颤栗,无尽的哀怨。她不无恐怖地发现:在中国普通百姓中,“人”不是“人”,已经成了生活的常态、常规、常理,而“人”要成为“人”,却十分的自然地(用不着谁下命令!)被视为大逆不道,这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构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你看,《生死场》里那些“受罪的女人”被打、折磨、蹂躏,犹如“老马走进屠场”,“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有谁皱过眉、说声“不”字么?然而,《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因为“笑呵呵”的,因为“两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因为“坐到那儿坐得笔直,”因为“走起路来,走得风快”——多少有点“人”的模样儿,就被认为“不象个团圆媳妇了”!人们就有权骂她、打她,有权用烙铁烙她,把她放到热水锅里去烫去煮,一直到“伸腿”“完事”!而且这还是“为她着想”,出于一片“善心”。不要以为这里有半点虚伪做作,这一切确确实实充满了善良和真诚。然而,这搀杂着善良的残忍,不是更令人发指么?萧红的作品里,甚至像赵太爷、鲁四老爷这样的代表社会邪恶势力的反动人物都不曾出现,有的只是“柳妈”——“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善男信女们。正是这些善男信女和小团圆媳妇们的矛盾冲突,构成了萧红笔下的悲喜剧。这是更深刻的悲剧:吃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民族意识与心理之中,成为“历史”的力量,“多数”的力量s。这是更普遍的悲剧:古往今来,直接死于统治者屠刀下的人少,更多的却死于“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不见血的“谋杀”之中,这难道不是一个痛苦的、令人难以接受的铁的事实?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这又何尝不是一出民族的愚昧、人性的扭曲的喜剧?——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怎么也笑不出来的啊!茅盾说,读萧红的作品,“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人们从萧红作品中得到的感受,与读鲁迅作品竟是这样的相似!
然而,人们仍然觉得,萧红作品缺乏鲁迅作品那样强烈的冲击力量,感奋力量,却多了一点忧郁与感伤;鲁迅的忧愤也比萧红更为深广。萧红只是惊人真实地描绘出历史惰力的可怕力量,却未能揭示其原因:她在历史的现象面前止了步。萧红具有鲁迅那样的艺术家的敏锐的感受力,也许在思想家的鲁迅所特具的深邃的思想力方面有所不足。萧红在找到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队伍之前,没有经历过鲁迅那样的曲折的过程,这是历史的幸运;但萧红却缺少了在上下求索中对中国社会与历史进行深刻研究与剖析这一课。我们也毋庸回避,后期的萧红与时代的主人公工农火热的政治斗争所保持的距离对她的限制。“我羡慕你的伟大,我又怕你的惊险”,“世界那么广大,而我却把自己的天地布置得这般狭小”t,这是萧红思想与生活的悲剧,它严重地影响了萧红创作才能的发挥。时代对萧红是太残酷了,给她的时间竟这样的少;我们没有理由苛责她。但从萧红与鲁迅思想、艺术的差距中,后来者是应该而且可以得到许多教益的。
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毕竟提供了鲁迅所不曾提供的东西。鲁迅曾经把中国的历史划为“暂时做稳了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两个时代。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人们按照历史的惰力麻木地动物式地生活——这正是在鲁迅和萧红的笔下深刻描绘过的。但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人们可怜到连动物般生活都不可能,被逼到了生活的死角、绝境。但生活的辩证法正是如此,“必死之而后生”,随着生活常规的打破,人们心理上传统的信念终于缓慢地、被动地动摇了——这正是萧红所生活的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入中国的时代的特点。萧红用她那为鲁迅所称道的“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u和感受,最早敏锐地抓住了社会心理与社会关系上的微妙变动,用她那“越轨的笔致”写下了“人的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上“新鲜”的一页v。于是,我们终于看见了社会关系的最初解冻,那些互相隔绝的人们逐渐靠拢、汇集,“一起向苍天哭泣”,“共同宣誓”,“大群的人起来号啕”w——在共同敌人的铁蹄威胁下,人们也许是第一次发现彼此间有了休戚相关的命运,产生了心心相印的感情!而且,我们听见了那使“蓝天欲坠”的呐喊:“我是中国人!”x——麻木的“动物般”的人们第一次感到了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我们古老的民族毕竟是有生命力的,它终于获得了一颗“猛壮”的、“铜一般凝结”的“心”y!萧红以不可抑制的喜悦捕捉住了、并写下了这一切时,充满了一种历史感。她清醒地把这民族心理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看作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比之麻木、冷漠的过去,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的进步;然而,我们的民族与人民也没有在一个早晨就“突变”为英雄,它依然背着历史传统的重负。唯其如此,这个民族明天必然有更伟大的发展与前途。萧红所要完成的,正是鲁迅曾经提出过的历史任务;真实地、历史地写出我们的民族、人民从“个人主义”到“集团主义”其间的桥梁z。萧红的历史贡献也在这里。
三
鲁迅与萧红在艺术上都具有一种不受羁绊地自由创造的特质。他们不为成规所拘,总是努力地寻求与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形式。这构成了他们的“小说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萧红曾经理直气壮地引出鲁迅来为自己的小说辩护:“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7。这辩护是有力的:人们确实不难发现,鲁迅与萧红就是在创造介乎传统小说与散文诗之间的新的小说形式上,也是相通的。
没有谁比鲁迅与萧红更重视感情在创作中的作用的了。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8,萧红以为“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想的情绪”@9。他们从不以旁观、冷漠的态度进行创作,总是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倾注于描写对象之中;在塑造“民族魂”的同时,他们真诚地显示着自己的灵魂;在人物客观形象背后,分明闪现着主人公的主观形象,有时候两者甚至合二为一。——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与萧红的小说最接近诗。
萧红“明丽”的文笔最为鲁迅所赞赏#0。读萧红的小说,有谁能够忘记那在阴暗的画面中时时闪现的亮色: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象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这是诗,真正的诗,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诗。然而,这是萧红的诗么?她不是早就说过:“我的心就象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2么?而且,在人们的印象里,她的音乐诗的主调正是那“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一根发丝那样的小夜曲”#3呵。但是……且听一听萧红心的低诉吧:我向着“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4,“我们的灵魂难道不需要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吗?”#5:“我要飞……”#6。呵,这可怜的女人!生活在“原始的”、“本能的”、“野蛮”的人世间,灵魂却在那“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所在#7。丁玲说得多好:“她或许比较我适于幽美平静#8,”——她是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更“适于幽美平静”呵,可她的生活又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更阴沉更不幸!她“不甘”于在不幸中沉没,挣扎着,用带血的声音呼唤阳光、鲜花、自由与美。流溢在她作品中的“明丽”色彩,与其说来自生活的实感,不如说出自她生命的呼唤。——于是,萧红的小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
就是这“明丽”的色彩也让我们想起鲁迅,想到他的《好的故事》。人们往往忽视了鲁迅作品中这色彩明丽的“诗魂”。鲁迅也有一颗柔和的、富于幻想的心。“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在他的灵魂上留下了“荒凉和粗糙”的“瘢痕”#9,披上了坚强的硬甲。——这正是萧红所缺少的。如果说鲁迅的“明丽”之中更有一种深沉的力量,那么萧红的“明丽”里就有更多的天真。丁玲说,见到萧红,总能“唤起许多回忆”,她的“纯洁和幻想”都让人想到自己无邪的童年$0。也许正是这一点,使鲁迅对萧红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鲁迅自己就终生不失“赤子之心”。
然而,萧红也有粗犷。当《生死场》发表时,胡风就在注意到她的“女性的纤细的感觉”的同时,看到了她的“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1。许广平曾对此有所辩驳,她说:萧红“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赋予女性的柔和”$2。事实上,流露于萧红文字中的“英武”之气,正表现了萧红灵魂的另一面:萧军说的她具有“不管天,不管地”、“藐视一切,傲视一切”的“流浪汉式的性格”$3。萧红毕竟是大海般宽阔的东北大地孕育的女儿,东北人民特有的豪勇也浸入了她的灵魂。
诗人问:“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4?”真实地绘下了这坚强而软弱、响往着美却又在丑恶中呻吟的寂寞的“诗魂”的,正是萧红自己……
朱自清说过:“诗的特性似乎就在回环复沓,所谓兜圈子。说来说去,只说那一点儿。复沓不是为了要说得少,是为了要说得少而强烈些$5。”萧红正是通过这种“回环复沓”赋予她的“诗魂”以诗的形式。请看《桥》。人物的视觉、意念里,一再地重复着“桥”的形象:“颤抖的桥栏”、“红色的桥栏”……“这桥,这桥,就隔着一道桥”……“桥好像把黄良子的生命缩短了”……“这穷小鬼,你的命上该有一道桥呵”……“这桥!不都是这桥吗?”……呵,“若没有过桥……”像钉子似的强烈地打入读者的记忆里,逼得你不能不深思:这“桥”——难道仅仅是“桥”么?难道在那可诅咒的旧时代里,不是处处都“隔着”这“一道桥”:贫富的悬殊,心灵的隔绝;而这种悬殊,隔绝是另架一座新“桥”就能沟通的么?黄良子一家不是因为有了新桥就造成了更大的不幸么?黄良子的孩子最后“连呼吸也没有了”,难道你不会因此而联想到我们的同样被各式各样的“桥”窒息着生命的民族?当小说的结尾,再一次出现那“颤抖的桥栏”、“红色的桥栏”的形象,难道你不觉得一阵冰凉的颤栗猛地爬过你的全身?黄良子“这次,她真的哭了”,而你呢?……这是高度的艺术的“凝聚”:通过作者复沓回环的艺术手法,凝聚到一个形象焦点上;这同时是高度的艺术的“扩散”:通过读者的联想,扩散到无限丰富的时间与空间。——这正是“诗的艺术”。
心理活动的一再重现,更能强烈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桥》里,一种“幻觉”恶魔似的追逐着黄良子: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她总是觉得女主人在喊她。清晨,“在初醒的朦胧中”,她“清清楚楚”地“听得”女主人呼唤的声音,跌跌撞撞赶去,结果是一场虚惊,她害怕起来:“怎么!鬼喊了我来吗?”白天,她推着小车去看自己的孩子:却又“象”听见“女主人在她的后面喊起来”,她“吓得出了汗,心脏快要跑到喉咙边来”。小说没有写到女主人的任何凶言恶色,甚至女主人根本没有出场,然而,她所处的“主人”地位本身,就给这位善良的普通农妇以无所不在的、无形的,巨大的心理压力,足以使她终日生活在恐怖之中了。这样的心理刻画所具有的内在的深刻性与强烈性,使人想起了鲁迅的《离婚》。
诗人们常常借助于复沓回旋来加重诗的感情的浓度与强度,创造诗的氛围。在《桥》里,自始至终回旋着一种呼喊声,执拗的,凄厉的——在“雨夜”,在“刮风的早晨”,在“静穆里”,在孩子的哭声中;“受着桥下的水的共鸣”,“借助于风声”,“送进远处的人家去”,也送进读者的心坎里,给人以难以言状的重压,使人感到生活的残酷,生命的无助与人生的悲凉。但诗人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字句、感情的重复,她注意重复中的变调,追求着思想与感情在回旋中上升。从小说开始,主人“黄良子,黄良子”的“歌声般”的喊声,到小说中间黄良子的“黄良!黄良……把孩子叫回去……”的焦急痛苦的喊声,到小说结尾小良子“妈妈,妈妈”挣扎的喊声和哭声,小说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一步步发展,作品的控诉力量也逐渐上升到了顶点。应该说,这是一种更高的诗的境界。
……读着鲁迅、萧红的作品,像是捧着诗人的博大的心。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却还那样滚烫——烫得灼人。鲁迅早就期望他的、以及同类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随着民族的新生,“和光阴偕逝”,然而,直到今天,却依然如此“新鲜”。这是怎样的一种历史现象与文学现象?是我们民族与文学的幸与不幸?那由鲁迅、萧红及其同辈作家开了头的民族“人的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该怎样续写下去?……
人们,应当思索呵!
一九八一年十月写毕
注释:
骆宾基:《生死场,艰辛路》
许广平:《追忆萧红》
萧红的悲剧命运牵涉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及家庭、婚姻等一系列微妙而深刻的问题,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故仅在这里略说一句,不再展开。
鲁迅: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萧军、萧红书。
茅盾:《论萧红的〈呼兰河传〉》
,h聂钳弩:《〈萧红选集〉序》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鲁迅:《写在〈坟〉后面》
列宁:《亚洲的觉醒》,收《列宁选集》第二卷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
转引自瞿秋白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写实主义》
萧红:《呼兰河传》
鲁迅:《热风?为俄国歌剧团》
鲁迅:《坟?我之节列观》
《萧红自集诗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年三期)
萧红:《生死场》
鲁迅:《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聂钳弩:《〈萧红选集〉序》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
萧红:在《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上的讲话(《七月》三集三期一九三八年六月)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
萧红:《呼兰河传》
见萧军:《萧红书简存注释录》
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罗荪:《忆萧红》
绀弩:《在西安》
萧红:《无题》(《七月》三集二期,一九三八年四月)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
鲁迅:《华盖集?题记》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
许广平:《追忆萧红》
见萧军:《萧红书简存注释录》
朱自清:《新诗杂话?诗的形式》
原载《十月》第一期,1982年
关于萧红的纪念与研究
王观泉
年9月,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一封信中说:“前几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做了一回50岁的纪念,其实是活了50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a其时,左联成立才半年,但鲁迅先生“惟希望”的青年作家们却在这刚刚成立的革命文学大集体里,在鲁迅先生的领导下以自己的一支笔为“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的劳苦大众“发出战叫”。著名的女作家萧红(1911—1942)就是其中的一个。
年10月,当萧红与萧军从哈尔滨转辗青岛赶到上海投奔鲁迅,期望着鲁迅伸出救援之手时,左联五烈士中的女作家冯铿已逝世三年,丁玲正被关押在南京国民党监狱,生死未卜。因此,萧红是当时上海左翼文学阵线中唯一的女作家。但是初见鲁迅时的萧红还只是张迺莹,虽然已经头角初露有了两年的创作生涯,在东北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还和萧军合璧出版了一册《跋涉》,不过仅以此在上海没关系定居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萧红日后回忆所说的那样,鲁迅先生是萧红的长辈,他像萧红童年唯一的保护人祖父一样地爱护这位当时只有23岁的青年。鲁迅不仅为二萧的创作打开了发表的局面,还给介绍了聂绀弩、胡风、黄源、叶紫等左翼作家,使萧红能以生活在友情怡怡的集体之中安心创作。次年——1935年12月,萧红的《生死场》经鲁迅仔细披阅、修订并作了一篇序言,殿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之后,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立即轰动文坛。《生死场》属于最早将黑龙江人民的苦难和抗争公诸于世的重要作品。1936年8月,萧红出版了《商市街》,这是萧红脱离苦海开始写作生活的自传体记事文集,还是具有奇异都市色彩的哈尔滨市井生活的生动写照。写到这儿,我们的感情不能不与45年前的萧红一样陷入无限的悲哀之中,《商市街》出版后两个月——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萧红从此失却了最亲的亲人。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萧红转辗武汉、山西、西安又折回武汉,这之后是重庆,1940年到香港,两年后竟葬身于此。算来至今已经有39年了。笔者在一篇谈30年代青年作家的文章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叶紫说:‘个人的死是不要紧的,我虽然死了我精神不死。’这话真发人深思,然而,活着的人们如果不记得先辈作家的精神结晶——文学作品;被萧红深切思念着的故乡的人,不记得《生死场》、《呼兰河传》、《商市街》等等作品,不死的精神也活不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更成不了鼓舞我们追求光明的力量。最好的纪念还是要出版、宣传、研究……”
故乡的人民并没有忘却曾经为他们呼号过的女作家萧红,三年来,黑龙江省的文学史论研究工作和出版工作在萧红研究和萧红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以今年萧红诞辰七十周年和明年的萧红逝世四十周年为纪程,积极展开工作。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79年初提出了出版萧红著作、研究萧红生平和创作,建议在萧红故乡呼兰县保存故居、在哈尔滨设立纪念馆等数项建议。建议获得了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出版社、省市报刊以及省内各大专院校中文系教研人员的大力支持。省文学研究所于建议发出后,作为东北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影印出版了萧红和萧军合集《跋涉》,使这部已经绝版了47年的罕见书获得再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热烈欢迎。不久日本就出现了《跋涉》的复印本,在香港也重版了这册研究二萧的重要作品集。
萧红著名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和1980年先后出版,两部小说初版共印五十万册,旋即销售一空,盛况空前。这次出版的《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初版为底本,保留了鲁迅的序言和胡风的《读后记》,增添了萧军新写的《重版前记》。《呼兰河传》用的是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桂林初版,无茅盾序),收入了1947年上海环星书店版的茅盾的序言,骆宾基为黑龙江版作了一篇《后记》。
年来一直以为遗失了的长篇小说《马伯乐》续集,经过香港和美国的爱萧者的探索和发掘,终于找到。现在,连同1941年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的《马伯乐》(上部)合璧的“足本”《马伯乐》即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马伯乐》续篇是由美国朋友、《萧红评传》的作者Goldblatt(葛浩文)副教授复印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真是一片热忱。新版“足本”《马伯乐》还袭用萧红原设计的封面,使这本书更感亲切。
足本《马伯乐》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时,由葛浩文译成英文的足本《马伯乐》将在美国出版,这是近年来萧红著作出版中的大事。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实绩。
萧红31年短促一生在颠沛流浪中写作了九年,留下了近百万言,生前就出版了:《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小城三月》、《萧红散文》、《马伯乐》等十一部作品集。尚有《兆中国》、《后花园》等短篇小说,以及在哈尔滨、青岛、汉口、重庆等时期的一部分作品和数十首诗、两个剧本没有发表。这些作品都将在她的故乡面世。现在已经发稿的有《萧红散文集》和《萧红短篇小说集》,这两部作品都收入了一些湮没了40年以上的作品。这两部集子的出版必将推动萧红创作及其思想的研究。
为了提供萧红生平、思想和创作的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由老作家萧军注释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这是一部研究萧红1936年7月—1937年1月在日本生活时期的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资料,萧军的注释还为读者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萧红生平的资料。多难的萧军能够将这些信件保存了44年完整无缺,真是一个奇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由笔者编选的《怀念萧红》一书。此书汇集了鲁迅、茅盾、柳亚子、许广平、聂绀弩、丁玲、萧军、骆宾基、罗孙、锡金、绿川英子、史沫特莱等萧红生前师友朋辈和国际友人的有关文章和回忆录,书中还有一组萧红在香港逝世后的殡葬、延安悼念萧红逝世和1957年迁葬广州的资料。《怀念萧红》一书的出版还得到最近逝世的茅盾的热情支持,茅公在病中握笔挥毫:“怀念萧红茅盾题”。表现了文学先辈对于后生的缅怀之情。
黑龙江省的萧红研究大致分生平传记和作品评论两个方面。在传记方面陈隄、铁峰、钟汝霖分别作出了贡献,他们正在撰写评传,还有一些同志则协助萧红亲友、同学写回忆录。比如与萧红一同在东特第一女中读完初中三年的同学沈玉贤的《回忆萧红》c对萧红的中学生活提供了可靠而又生动的传记资料。铁峰的《萧红评传》片段在《文艺百家》第1期和《文学评论丛刊》第4期上相继发表,他对有关萧红生平事迹提出了和传统的看法有分歧的资料,引起了国内外的热烈讨论。
作品研究方面目前已出现了一些评论,如陈隄在评传中从黑龙江社会生活和人民斗争的角度研究《生死场》的篇章、锺汝霖对于萧红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探索、呼兰县和哈尔滨市的一些研究者对于萧红踪迹与作品关系的考索,都获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全面性的研究,从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和30年代文学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还不多,还有待努力。研究工作中对于萧红的重要著作如《生死场》的研究比较多,但是对《商市街》、《呼兰河传》这些乡土文学杰作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于短篇小说《手》、《牛车上》、《小城三月》等名篇佳作还没有引起评论家的足够的重视,而小说《北中国》、《后花园》,哑剧《民族魂》等在香港所作,以及《马伯乐》续篇,因长时期来没有能得到重版的机会,就根本谈不上研究。随着“双百”方针的贯彻,随着萧红著作的出版,萧红研究将打开新的领域,产生理想的效果,缺门也必定会引起重视而得到填补。比如长时期来文学研究工作中忽视艺术性,忽视对于构成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和作家艺术风格的研究,这个研究领域中的弊端在萧红研究中显得特别突出,《呼兰河传》、《商市街》等等非常优秀的作品就因为片面地理解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作品的社会效果等而受到不公允的批评或冷落。现在我们应当加强研究萧红小说和散文的艺术性、艺术感染力,包括文体结构方面的独到之处。一个作家所以能在文学史上、在广大读者之间有一席地位,必定具有与别的作家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可以这样说,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作家描绘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县城,其艺术感染力能超越萧红及其《呼兰河传》,犹之于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与黄河一样,至今无出其右!这是黑龙江省文学历史上的光荣。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郁达夫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d当我们吃够了四人帮十年文化法西斯统治之苦,再来细细吟味达夫的这段至理名言,该是多么发人深省啊!这证明我们已经摆脱了奴役地位,懂得了人的价值,懂得了创造文化的艰辛,懂得了应当尊敬那些创造了民族文化或者是为振兴民族起过作用有过贡献的先驱者。萧红就是一位值得尊敬、缅怀、学习的文学先驱。她以自己辛勤的文学劳动丰富了东北的也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宝库。
注释:
《鲁迅书信集》第284封。
《厄于短年的创作英才》载《电影?电视?文学》《萌芽?增刊》1981年第1期。
《哈尔滨日报》,载1981年6月16日。
郁达夫《怀鲁迅》,载《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一辑。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初版。
原载孙延林主编《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