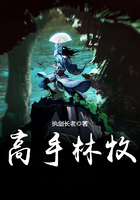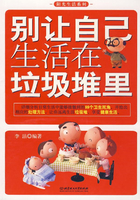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总算能够有力气下床了。但因为太久时间没行走了,双脚一踏地,就立刻仰倒在病床前。也正因为是仰躺在地面,我由下至上,看到紧贴病床下方的床板下,似乎有个什么古怪的东西。
那是一块黑黢黢的铁片,还闪着寒光。我摸了摸,指间顿时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还流出了鲜血。这是一把单面开刃的长刀,一端连在病床一侧,另一端则可以活动。
我试着移动这柄长刀,一端被我拆了下来,而连在病床一侧的则被固定死了。经过180度的回转之后,长刀转到了病床之上,刃口正好朝下。
看着这柄长刀,我不禁心惊胆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正是一把铡刀吗?如果病床上躺着一个人,铡刀则正好位于病人的腰部之上。如果铡刀落下,躺在床上的人无疑会被腰斩致死。
天哪,这间病房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我的脑海里,也不禁涌现出在镇口榕树下看到的蟑螂被腰斩的尸体。
我感觉到恐怖。如果我还继续四肢无力地昏睡在病床上,万一有人翻转这把铡刀,然后重重落下,我就会变作两截腰部分离的残尸。
是费雪把我送到这张病床上的,她想干什么?想腰斩我吗?我又想到了黑色小楼外停着的那辆面包车,车上会是费雪的同伙吗?我不敢再想了,我得尽快离开这里。
还好病床的门没有从外面锁上,门是朝外开的,我轻轻推开门,蹑手蹑脚走到了病房外的走廊上。
走廊两侧全是紧闭着的房门,大概有十多间,楼梯就在走廊尽头。
我无声无息地慢慢向楼梯走去,刚走了几步,就听到一间屋里传出了有人说话的声音。我朝那间屋望去,发现门是虚掩着的,难怪会从隔音这么好的房间里传出声音。
我静静聆听,屋里传来的是两个人的声音,一男一女,女的正是费雪。
男的问:“为什么还要骗那家伙他只是生病了?依我看,直接告诉他真相,然后捆绑在病床上,等到另一个试验品来了后,就开始动手。”
费雪答道:“这样不好,如果他因为得知真相而恐惧,心跳、血液、脉搏的数值都会发生变化,不利于实验数据的收集。”
男的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费博士真是考虑得周全。不过,为什么要通过食物令试验品摄入安眠药呢?为什么不直接注射安眠药?”
费雪回答:“注射安眠药,药效会过于强烈,另一个试验品很快就会送到,我怕实验开始的时候许波无法醒来。而这个实验,必须是在试验品清醒的时候开始进行。别忘了,我们模拟的实验环境是战争时期的紧急危重创伤处理,军人不会在服用安眠药后才受重伤的。”
男的发出附和声,而我则跌入云里雾里。
实验?试验品?清醒状态?战争时期?这说的都是什么呀?怎么越听越恐怖?
不过,我也从他们的对话中,明白了自己的晕倒绝非偶然,一定是那两根香薰蜡烛搞的鬼。随后在病房里喝下的小米粥,也被掺入了安眠药。如果不是因为蟑螂钻入口腔而呕吐,排出了安眠药成分,现在只怕我还依然躺在病床上,成为费雪他们的试验品。
而这时,我听到脚步声,那男人要开门出来了。幸好门是朝外开的,我赶紧躲到门板后。那男人出屋后,径直朝楼梯走去,并没发现身后的我。
虽然我是资深宅男,又刚恢复体力,但从这个男人的背影看,他比我矮一个头,又瘦得跟皮包骨头一般,于是我鼓起勇气,冲到他身后,扬起手肘,重重地击向了他的后脑。
“砰”的一声,他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
大概费雪在屋里听到了走廊上的动静,伸出了半个脑袋朝外探视。当她看到我后,立刻发出一声尖叫。而我听到她的尖叫声后,便转过身朝她走去,然后一拳击在了她的太阳穴上。当她倒在地上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穿了一件白大褂。我记得,只有医生才会穿白大褂,而护士是不会穿白大褂的。
幸好每间屋的隔音效果都不错,即使我击倒两个人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其他屋里还是没人出来查看。我把那男人拖进刚才他俩说话的那间屋,在屋里找到绳索,把他和费雪分别捆绑了起来。
我猜,屋里准备的绳索,应该是这个男人为我准备的——他说过,原本他提议把我捆在病床上的。
男人醒来的时候,我又给了他狠狠一拳,让他继续昏睡过去,还在他嘴里塞了一块破布。而当费雪醒来时,我则恶狠狠地问她:“你究竟想干什么?”
她也发现局势对她不利,只好抬起手臂,朝屋里的一个写字台指去。
我走到写字台边,看到桌面上摆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盒子。盒子里,有个古怪的东西正在缓慢地爬行着。
那是一只蟑螂。
之所以说它古怪,是因为它的上半身和下半身颜色明显不一致。蟑螂的腰间,似乎有一道裂纹,裂纹外还涂抹着一些白色的药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