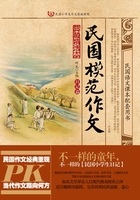入团仪式举行后,一切步入正轨,或者说永远都沿着正轨前行。大概是知道邱昙的时间不多了。一天中午,鲁老打断了读报课,问:“有谁愿意去看她?”很多同学举起了手。我不敢举。柯冉用手撞了我一下,说:“去看看呀,以前你们还是同桌呢。”我摇了摇头,坚决地说:“不想去。”我想起了我的外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凌晨,外公病重。他躺在医院的床上,周围是一片惨白清寒。他的鼻子里插着输氧管,赫哧轻喘,喃喃地说着什么。外婆并没有凑上去听,生活琐屑早已磨掉了她的细腻。她只是低低地絮叨着近日以来连绵的阴雨。我和大人一起站在床边,气氛压抑而沉闷。薄薄的被单里,是外公微躬的脊梁。他的皮肤已然是暗褐松弛。如今想来,一个人一生的尽头竟是这般光景,面容惨白,体态痉挛,四周一片呻吟叹息。即使你最亲近的人在你身边,你依旧孑然孤独。汹涌翻腾在他周遭的是整个巨大的世界,而他蜷缩在岁月的暗角,等待生命最后一次触礁。大约五点钟,父亲牵我出去散心。天色微灰。回去的时候,外公已经走了。窗外的花坛里,大朵大朵的美人蕉开得艳红,像血,炽热的撕裂般的颜色。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真实的死亡。来不及抗拒,来不及自哀,眼睁睁地看着亲人被抽离这个鲜活的人间。这是何等的无力,何等的残忍,这怎能叫人不惊惧,我内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直视这种决绝的惨然。所以,我又强调了一遍:“我不想去。”大家的目光落到了李松身上。他说:“我还要预习下学期的课程,不能去。”气氛一瞬间有些凝重。还是芋头打破了僵局,主动提出想去看看。“反正我也没事。”这是他的解释。最后,我们班几个男生,几个女生怀着一种为我所不知的复杂心情去了。直到下午放学时才回来。“你们去看了邱昙,她在干什么?”我问芋头。他诡谲地笑了笑,低声说:“在打电脑哩,技术高得没话说!我怀疑她有黑客天赋!”“那她说了些什么没?”“她说她想看北京奥运。”听了这话,我震惊了。这是一种面对生命最本真的震动,震动于它的脆弱,又震动于它的伟大。邱昙过早地掀开了生命的底牌,但,即使残酷,她也热爱这生命,即使孤独,她也未曾向生活哭诉。她的一切告诉我,她捍卫一种尊严,她展示一种力量。当天晚上,她就去了。
依稀记得芋头提出举行一个悼念邱昙的班会,可惜人微言轻,响应者寥寥。一套桌椅放在教室的最后面。一段时间里,上面放了一束白花。初夏,阳光下的树木葱翠如初绽。席卷而来的夏日白光里,鸟鸣声忽远忽近,像记忆一样芬芳,像奇异的幻影一样令人心悸。上体育课时,我的脚崴了。宁小宇陪我去看了校医,校医又建议去不远那家大医院看看。挂号,看病,取药。就这样,我们来来回回折腾了一个下午。“谢了。”我对宁小宇说。她摇摇头,回了我一个温暖的笑容。总之,运动鞋是不能穿了。我的左脚换上了凉拖。进教室时,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上了我的脚,平日里死板严苛的物理老师也对我展露出了体谅的笑容。承蒙大家关切的注视,我第一次嫌弃自己的脚趾长得过于平淡,寻思着应该涂上蝴蝶蓝的指甲油,或者像白丽那样戴一个亮闪闪脚链……我看了一眼黑板,这堂课讲惯性定律。讲桌上摆放着斜木和小车。“物体在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后面的章子腾研究着这句话,“这不是说我吗!”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问:“这跟你有什么关系。”章子腾突然变得很深邃,说:“我一直在惯性里生活。
”话音刚落,他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轻笑了一下,补充一句:“算了,说了你也不懂!”也罢也罢,反正我也不想懂。回过头,我看到李松正若有所思地盯着我。我以为这是温暖的关怀,但他紧接着舒了一口气,说道:“我还以为你违反校规校纪出校闲逛了呢。”我头一偏,看到了他桌上的考勤本,忽然有些说不出地生气。“我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我冷冷地说。李松愣了一下,讪讪地回答:“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下午老师要讲新课,你理科本来就不好,缺课的话,很难补起来。”五月十二日。周一。中午英语读报刚结束,我们开始推桌子。我穿着一只维尼熊图案的蓝色拖鞋,坐在凳子上,往前面一挪一挪地,心里一面还寻思着自己的窘样。忽然,我看见有同学指着地面,惊恐万分地叫:“地震了!”一种震感立马从脚心传上来,我感觉到了周遭明显的晃动,抬头看,风扇,电灯都在摇晃。章子腾在动荡里站起来,大声指挥:“冷静!冷静!不要慌乱!”四壁摇撼里,有几个同学跑了出去。我不知道是躲桌下好,还是跑好。见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跑了出去,我也想跑。但是,该死的脚崴了,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我扶着桌子,吃力地站了起来。
正在这时,我感觉手臂被谁搀住了,那人拉着我,一点一点地向门口走。居然是苏明理。楼梯口有老师在紧急地指挥,人流分成几股从不同的通道口向操场涌去。我一面逃命一面感叹:啊!我们学校还真是井然有序呀。自豪之余,脚已经踏上了塑胶场地。震动还在继续,踩在地上像踩着滚烫的鸡蛋黄。一片混乱里,我们还是找到了自己的班级,席地坐下,惊心动魄之外还有些难言的尴尬。“谢谢。”我对苏明理说。她似乎很不习惯这样正式的交流,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过了半天,她像寻找到新大陆一般,兴奋地说:“今天下午的两节英语课不用上了。不亦快哉!”这时,我准确无误地听到了宁小宇愤怒的声音。“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她一下甩开了柯冉的手,“地震一来就一个人跑了,你有没有想过我?”“我们坐的位置距离那么远,我怎么来拉你!”柯冉辩驳道,“再说,当时那么乱,我根本不可能挤得过来。”“算了吧,你太虚伪了。你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我。大难来时各自飞,这算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说了,你简直不可理喻!”他们俩孜孜不倦地争吵着。广播声,哄闹声,呵斥声不绝于耳。人群的间隙,我还看到了李松。生活老师把代为保管的手机分还给了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