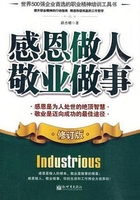驾!驾!
万马奔腾,从草原上呼啸而过。风声劲急,断草与尘土四散飞扬。
粗犷的蒙古汉子高扬着马鞭,疯狂地策马,肆意地叫嚣。
湛蓝如洗的万里苍穹,有雄鹰滑翔而过。
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脸上残留着数道清晰的泪痕。被一个及其彪悍的蒙古鞑子横抱在腰间,随着马匹上下颠簸。
秀美紧紧地蹙在一起,一个剧烈的颠簸,将她从昏睡中惊醒,一睁开双眸,便开始大吼大叫,双手乱撕,让那挟持者很不舒服。
那蒙古汉子,粗犷地笑着,挥手冲着小姑娘的后脑勺,重重地就是一拳。
这是,小姑娘自被掳之后,第三次被打晕。不知道走了有多远,每一次醒来,都在马背上颠簸,还没来得及挣扎,脑后便是重重地一击。
在她再次昏厥之时,两行清泪再度汹涌而出,她,真的好后悔,后悔不该跟爹爹赌气,后悔不该私自离家出走,后悔不该走出大楚皇朝的保护圈——
落到这种田地,都是她咎由自取,怨不得天,恨不得地。
在军中没少听说,蒙古鞑子有多么的残暴狠辣,现下羊入虎口,真不知命运何去何从——
就在她万念俱灰之时,一抹素白身影在眼前晃了两晃。
那挟持自己的彪形大汉,凄厉的嘶吼了两声,便没了气息。
接下来传入耳边的便是兵戈相击的铮铮琮琮之音,刀剑撕裂衣帛肉身的嗤嗤钝响之声,人痛呼惨叫之音,马鸣扬蹄之声。
意识渐渐地消弭,载着自己的那匹马似乎受了惊吓,发了疯似的扬蹄狂奔。
人声,马声,兵戈声,厮斗声,声声渐消。
那匹发了狂的马,载着浑身无力的她,一路前冲。
就这么死掉了吗?有那么几次,她感觉自己都要从马背上摔将下去了,幸得那将她掳走的汉子为了防止她逃走,用一根粗绳将她牢牢地捆在了马鞍上,否则,她哪里经得起这般颠簸。
耳边的马蹄声越来越响,却是那抹素白身影策马追来。
为了追上前边发疯发癫的马匹,来人横剑刺向坐骑,那马受了剧痛,前蹄扬起,冲天嘶鸣,也发疯发癫地往前肆奔。
近了,近了!还差一点点!
又是一剑没入马臀,风驰电掣的追击,那抹素白身影终于蹭过了她的身边,在与他打马而过的一瞬,眼前有一个通体晶莹的东西在眼前倏然一闪,那小姑娘下意识地探手一抓,将那莹绿玉佩攥进手中。
那匹受过数剑的马,跃过载着小姑娘的马匹,不听使唤,依旧发疯向前。
白衣少年剑眉一蹙,双足用力狠蹬了一下,借力飞身而起。挥剑斩断绳索,没了绳索的力道,小姑娘几近要飞离马身,跌甩出去。
就在小姑娘的身子从马腹滑到马臀即将跌甩的危机时刻,白衣少年的右手往前一探,拉住了小姑娘的左手。
被一股劲力,猛然回带,小姑娘撞入了少年人的结实的胸膛。然后两人一起跌落,只不过,少年人左足在地上猛然一撑,将自己的身子垫在了小姑娘的身下。
不巧的是,跌落之处,是个斜坡,被甩出的冲力,让两人重重摔落的同时,又是一顿猛烈地翻滚。
小姑娘很想看清白衣少年的相貌,可是徒劳,惊心动魄的滚落,无法让她如愿。
小姑娘醒来的时候,已然身在爹爹韩耀的军帐之中,可是那少年却自此消失,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他是谁——因为,军士发现她之时,军帐外只有她一人。
有一段时间,她逢人便问,又没有见过一个白衣少年。被军中人一度认为摔坏了脑子,得了失心疯。
他,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他,却在她的心底生了根,发了芽。
夜夜相思,日日念,手中的玉佩不知被泪洗刷了多少遍,多少次。
韩芷嫣收回举起的玉佩,凝眸而视,喃喃道:“或许,我已经找到了——”樱唇微微颤动。
妃常可乐:求票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