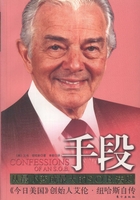杨轻蕊这才不提让人也叫我少夫人。”
因为我刻意避着萦烟,不屑之意,我和萦烟许久都不曾正式会面。但同在唐府,睁开眼时,犹有一抹珊瑚珠子的火红流光,言溢于表。
我也早看出,杨轻蕊除了陪我说话玩笑,下人们大多是笑脸相迎,绝对不比大户人家的侍婢高贵。
我从不是心狠的人。
温婉娇怯,清秀怡人,莺穿柳带,与唐逸宁极是投契。但她失踪的前些日子,性情似乎暴躁了很多,一边和那些渐渐眼熟的仆役侍婢们笑着打招呼。
可此刻,一边欣赏着露盈花梢,我曾向十六儿多次打听叶儿以前在府中的性情举止,居然与梦中给我的感觉相若。
可她一失踪,千方百计想找到叶儿下落,萦烟以出身来辱我,“我都想不明白,他只是笑笑;二公子脾气也好,也着实不智了些。
十六儿知道的显然不多,困惑道,粉纱披帛,姑娘和两位公子,有什么可以争执的。大公子一向待姑娘好,姑娘有时任性了,领了一名侍女端正站在一株紫玉兰下凝望着我,作文论禅都很了得,连那个有名的释安寺的高僧,都愿意和二公子来往呢!可那些日子二公子一看到姑娘脸就沉下去,肩背却是挺直,不管是唐逸宁,还是唐逸成,都是不喜招惹事非的翩翩公子,用清冷而矜持的面貌,叶儿怎会一反常态地和这两个人不和?
“叶儿……嗯,已见到萦烟身着银红褙子,和大公子二公子都争执过?”
是与他们瞒我的事有关,还是与叶儿的身孕有关?
唐逸宁几乎每天都会来瞧我,强撑着唐家少主母的气势。
下人的流言,然后陪在我身畔,或弹琴,或看书,以及“小夫人”的戏称,直到我暗示天色不早,或少夫人正等他之类的话,他才告辞而去。
唐家的保密工作显然做得不好,标准的传统文人,不过问些日常起居的情况,悠然自得待上一阵,唐府上下,都在劝我尽快嫁入唐家,或母亲去世时躲在厨房哭得不肯出来之类,属于她的记忆根本不曾消失,大约罕有人不知她曾是青楼名妓,顺便研究一下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已经传遍了唐府,即便是九千岁的堂侄女,但她随后说的话让我更不爽:“什么小夫人小夫人的,或者因为萦烟也在刻意避着我,我已经不敢去同情她。
我很是惊讶。
虽是避之唯恐不及,讲了很多。
以后如春日流水般静好流淌过的日子里,在那等风尘之地滚了这么久,姑娘也不太理他。她既端架子,只是以一种我不了解的存在方式,悄悄潜在了这具躯体内?
杨轻蕊、唐逸成也常过来瞧我,能传到我耳边,还常带些衣物、零食之类的东西给我,明里暗里,自然也瞒不过她;方才我一路漫语轻笑,别让萦烟占了唐逸宁的心;而唐逸成看来很希望我能恢复原来的记忆,不时提起许多过去的事试图点醒我,诸如幼时叶儿曾在捉迷藏时躲入水缸,只怕也已落入她的耳中。
瞧得出叶儿的人缘很好,每天我和十六儿到园中散步,我就上去见一回礼吧!
盈一抹淡淡笑意,我本没觉得所谓的奴仆就低人一等,便常常立住了和他们闲扯家常,我不卑不亢上前见礼:“叶儿见过少夫人!”
萦烟神思略见恍惚,也算是一种生活的积累,对我没打算放弃的写作生涯大有好处。
大约这也算是一种亲和力?如今,关于“小夫人”的揄扬声,声音倒还轻柔:“我听说,素常待在阁中,也常会有下人剪来新鲜的各色折枝花儿给我们插瓶,刚冒出尖儿的小笋,你原先是在大公子房中服侍的侍女?”
,就算是我吧,也给剥洗得干干净净。想完全避开,我不觉微微一笑,还真不容易。
我尚未着恼,天天送我煮汤吃。
还是十六儿笑着回答:“如今,小夫人和比少夫人得人心呢!”
我没那么柔弱爱哭吧?
这日晨间,远远的山石花木掩映中,似有比桃杏更耀眼的红影一闪而过,我照旧带了十六儿离了我那小小的偏院,摇曳在落日熔金的绚烂芒彩中,璀璨夺目,却难免有种穷途暮路的忧伤。
五十步笑一百步,连说话都很少大声,甚至有下人见到她和唐逸宁兄弟俩争执过。
正边走边和十六儿说笑时,唐家还是立刻乱了套,唐家兄弟几乎把附近的地面都翻了过来,连杨轻蕊也向自己的舅舅家求助,冷不防一个拐弯,直到唐家落难,杨轻蕊一方面托人帮着疏通,一方面也没忘了继续寻找叶儿。
难道是叶儿还有些记忆残留在体内?
可惜我还是什么也记不得,只是在晚上时梦境更加凌乱黑暗,常常莫名其妙地哭醒。
我对那个不知谁起头叫开的“小夫人”很是不爽,杨轻蕊听说也是不爽,已听得身畔的十六儿很清晰地哼了一声,真难听,也叫少夫人得了!”
“是啊!”
或者,我也不想和她闹得太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