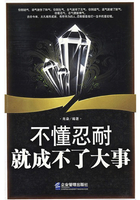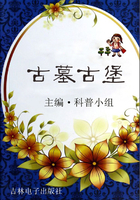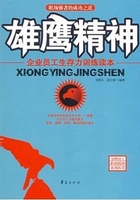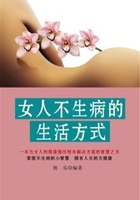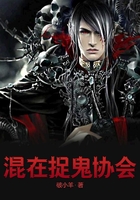国王就把他叫到跟前,问他:“大家的花盆中都有花,你为什么捧着一个空花盆呢?”孩子抽咽着,将自己如何精心摆弄,但花种怎么也不发芽的经过说了一遍。还说,他想这是报应,因为他曾在别人的花园中偷过一个苹果吃。没想到国王听完孩子的话,脸上马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把这个男孩抱了起来,高声说:“孩子,我找的就是你!”“为什么会是他呢?”大家都不解地问国王。国王说:“我发下的花种全部都是煮过的,根本不可能发芽开花。我这样做,就是想知道,谁才是最诚实的人。”捧着鲜花的孩子们都低下了头,因为他们全都是另外播下的种子。震撼生命的留言爱与亲情往往是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心永远都不会泯灭,即使是在最危险的时刻,最黑暗的地方。一次,一个在甘肃服役的战士替连队去三十多里外取水。回来时,水车走在荒凉的路上,突然被一头老牛拦住了去路。老牛朝水车上的士兵悲切地“哞哞”叫着,士兵明白了,停下车从水箱里舀出一些清水,送到老牛的嘴边。
但是老牛却没有喝,而是把头歪向一边继续大叫,送水的士兵正迷惑不解,就见从不远处颠颠地跑来了一只小牛犊,这时老牛闪到一旁,看着小牛犊一口一口地喝干了那些清水,然后感激似的对着士兵“哞——”地叫了一声,带着小牛犊转身离去了。口鼻发白干裂的老牛,竟将已到嘴边的水让给牛犊喝,可见亲情之真之切,让人感动。牲畜间的亲情如此,何况人类呢?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更凝聚着人性的光芒,它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永恒话题,一道永远张挂在人类天幕上的亮丽风景。21年9月11日,当恐怖分子的飞机撞向美国世贸大楼时,银行家爱德华正好被困在了南楼的五十六层。到处都是熊熊的大火和门窗的爆裂声,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了。就在这生死关头,他掏出了手机。爱德华迅速按下第一个电话。可刚举起手机,楼顶忽然坍塌,一块水泥板重重地将他砸翻在地。他一阵眩晕,知道时间不多了,于是改变主意按下了第二个电话。可还没等电话接通,他又想起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又拨通了第三个电话……爱德华的遗体在废墟中被发现后,亲朋好友都沉痛地赶到现场,其中有两人收到过爱德华临终前的手机信号,一个是他的助手,一个是他的私人律师。
可遗憾的是,两人都没有听到爱德华的声音。众人查了一下,发现爱德华在遇难前还曾拨出第三个电话。第三个电话是打给谁的?他在电话里都说过些什么?两人判断,爱德华的第三个电话很可能与他的银行或遗产归属权有关。可是爱德华无儿无女,五年前又结束了他失败的婚姻,如今只有一个瘫痪的老母亲,住在旧金山。当晚,迈克律师就赶到旧金山,见到了爱德华悲痛欲绝的母亲。母亲流着泪说:“爱德华的第三个电话是打给我的。”迈克严肃地说:“请原谅,夫人。我想我有权知道电话的内容,这关系到您儿子庞大遗产的归属权问题,他生前没有立下相关遗嘱。”可母亲摇了摇头,说:“爱德华的遗言对你毫无用处,先生。我儿子在临终前已不关心他留在人世的财富了,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迈克含着激动的泪水告别了痛失爱子的母亲。不久,美国一家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9·11”灾难中一名美国公民的生命留言:“妈妈,我爱你!”一朵玫瑰中的天堂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把我们的爱心真诚地付出,即使微不足道,也能温暖人们的心灵。夏日的一个黄昏,我和几个朋友坐在广场旁的小酒店里喝酒聊天。
透过玻璃窗,我看见街头有一个小女孩正提着一篮子玫瑰花,四处向人兜售。夜色渐渐深了,霓虹闪烁,我们只顾喝酒,也渐渐忽略了那个女孩的存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个小女孩竟然站在了饭店门口。她清秀的脸上绽满了忧愁与焦虑,操着蹩脚的普通话,有些怯怯地问:“老板,可不可以卖给我一碗蛋炒饭?”正站在我们旁边的老板转过头,看了看她。小女孩更加羞涩了,站在那里,小手紧张地揪着衣角,不敢再言语。“当然可以,你进来坐吧!”老板回答说。听完老板的话,小女孩变得有些语无伦次起来:“不,不,你把米饭盛在方便袋里就行了。”我们停止了谈笑。老板一副古道热肠的样子:“没关系,你进来坐吧。”谁知小女孩说什么也不肯进来。最后老板只好打点好,递给门口的小女孩。小女孩感激地提着一方便袋蛋炒饭走了。临走时,她高兴地付了两元钱。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些蛋炒饭的价格肯定是超过两元钱的。一问老板,果然如此。老板猜测说,这蛋炒饭可能不是那女孩买给自己的,因为许多天来,她一直都在这个广场周围卖花,来买蛋炒饭还是头一回。所以老板推测,肯定还有一个人,或是她的亲戚,或是她的一个更加苦难的朋友,需要小女孩的照顾。
最后老板说:“我给了她两份饭。”以前也经常见到有些衣衫褴褛的小孩到饭店买饭时饭店不予理睬的事情,但面前这位面容安详气质儒雅的老板让我不由得感到敬重与感动。不一会儿,那老板突然一拍脑门,说:“不好,我忘记给她筷子了。”我正好对那个小女孩充满好奇,就说:“我去送给她。”在广场的一角,我看见了她,那个卖花的小女孩。她的身边还坐着一位灰头土脸的妇女,正神色黯然地看着我。小女孩正用一只手抓着米饭送到妇人的嘴旁。见她们拘谨,我连忙说:“我是来给你们送筷子的。”小女孩说了声谢谢。我本想与她攀谈几句,可她们对自己的遭遇闭口不提。我只知道她们是一对母女。临走时,女孩递给我一朵玫瑰,说让我送给饭店的老板。把玫瑰放在我的手上时,小女孩浅浅地笑了,露出两颗雪白的小虎牙。我觉得,她的晶莹善良如同莲花上的露珠,在微风中传递着她小小内心深处由衷的感激。那一朵玫瑰,就是一个天堂啊!穿越尘世的约定有一种约定由真情铸造,这种约定可以穿越世间最珍贵的时光,抵达永远,这种约定就是爱。在一座煤矿上,一个矿工在井下刨煤时,一镐刨在哑炮上。哑炮响了,矿工当场就被炸死了。
由于这个矿工是个临时工,所以矿上只给他的家人发放了一笔抚恤金,此后就不再过问矿工妻子和儿子的生活了。悲痛欲绝的妻子在失去丈夫之后,就要独自承担来自生活上的压力了。她没有一技之长,只好收拾行装准备回到那个闭塞的小山村去。后来矿工的队长找到了她,告诉她说矿工们都不爱吃矿上食堂做的早饭,建议她在矿上支摊儿,卖点早点,一定可以维持生计。矿工妻子想了想,觉得这比回山村好一些,就点头答应了。于是,她找来一辆平板车,往矿上一支,馄饨摊儿就开张了。八毛钱一碗的馄饨热气腾腾,开张第一天就一下来了十二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矿上来这里吃馄饨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可达二三十人,而最少时从没有少过十二个人,而且风霜雨雪从不间断。时间一长,许多矿工妻子就发现自己的丈夫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下井之前必须吃上一碗馄饨。妻子们百般猜疑,甚至采用跟踪、质问等种种方法来寻找原因,但结果都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队长在刨煤时也被哑炮炸成了重伤。在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接替我每天去吃一碗馄饨。这是我们队十二个兄弟的约定,自己的兄弟死了,他的老婆孩子咱们不能不管呀。
”从此以后的每天早晨,在众多吃馄饨的人群中又多了一位女人的身影。来去匆匆的人流不断,而时光变幻之间唯一不变的是不多不少的十二个人。时光飞逝之间,当年矿工的儿子也长大成人了。而他那饱经苦难的母亲已经两鬓斑白,但却依然用最真诚的微笑面对着每一个前来吃馄饨的人。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与善良。更重要的是,前来吃馄饨的人,尽管年轻的代替了年老的,女人代替了男人,但却从没有少过十二个人。穿透十几年的岁月沧桑,依然闪亮的是十二颗金子般的爱心。相濡以“血”的爱有一种平淡的却让人永远都惊心动魄的伟大的爱,它的伟大就在于为了爱人,能够将痛苦留给自己,把幸福留给对方。有一对非常喜欢攀缘的夫妻,在一次攀缘中,不幸双双坠入了荆棘密布的深谷。遍体鳞伤的妻子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腿已经摔断了,不能动弹,而身旁的丈夫还处于昏迷之中。她急切地呼唤着丈夫的名字,并试图搬开卡住他的两块巨石,但都没有成功。在这远离人烟的山谷中,两个受了重伤的人只能企盼着奇迹出现了。妻子脑海里绝望的念头只一闪,便打消了,因为她感到丈夫的心脏还在跳动。
她忙忍住身体巨大的疼痛为丈夫包扎好几处流血的伤口,然后将他的头揽在怀里,面颊紧紧贴上去,一声声轻轻地唤着丈夫的名字。许久许久,丈夫的喉结蠕动了一下,发出了含混不清的呻吟。妻子立刻意识到丈夫是想喝水,可是她身边没有一滴水啊!妻子情急之下,把嘴唇都咬破了。猛然,她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将自己的右手食指放进嘴里使劲咬破,然后将流血的食指放入丈夫的嘴里,让丈夫吸吮她的血。疼痛中,妻子抓起身旁的一棵青草塞到嘴里。牙关紧咬时,一丝草汁竟让她欣喜万分。她开始不断地咀嚼青草、树叶,储备生命的能量,因为她知道只有自己坚持下去,丈夫才能有活下去的希望。当食指再也吸不出血时,她又毫不犹豫地咬破了中指,再一次塞到丈夫嘴里。两天后,这对夫妻被一位猎人救了出来。当得救的丈夫得知自己是吮吸妻子的鲜血才得以生还的时候,他跪倒在妻子跟前,捧着那曾无数次牵过的小手,滚烫的泪水大滴大滴地落了下来……编辑部里的秘密有时候,献出爱心不仅是对他人的一种帮助,更是一种心灵的自我安慰与净化。于他人而言,这是一种人逢绝路的希望;于我们自己而言,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收获和乐趣。有一个家境贫寒的女大学生,从遥远的乡下到北京上学。
可是就在她开学还不到十天时,家中就传来噩耗,父母姐妹在制作花炮时,竟然在一声爆响里全都被炸死了。家中房倒屋塌,不剩片瓦。从此女大学生举目无亲,也断了经济来源。她含着眼泪向学校提出退学。老师问她日后有什么打算,她说家中还有一点水田和一头老牛,从此就只能回家种地,做一名乡野农妇。老师听罢也落泪了,同学们也在迅速地为这名还来不及熟悉的同学赞助车费。可第二天老师突然告诉她,说我爱人在学报工作,编辑部现在正需要一人看稿,每月三百五十元。其他的我们再想办法。她没有想到人逢绝路,又生出这样一线希望。她高兴地点点头,再次流出了泪水。于是,她入学十天就成了一名学报编辑,当然是业余的。学校八千多人,学生六千五百人,学报十天才一张,稿子不多,她常没稿看。但是她的工资照发,月月三百五十块。报社里有五个人,人人都对她很好。她有时候因为课紧就不能到报社上班,也不会有人找她。即使在看稿时也十分简单,就是改改错字,提点意见。她一度以为,做学报编辑就这么轻松。时光飞逝,转眼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过去了。但她始终不知道,四年中每月的三百五十块钱,并非学校所发,而是五名编辑人员从工资里拿出来均摊给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