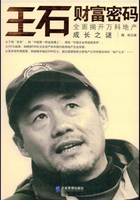堂下的妇人听见惊堂木的声音,浑身颤抖,连手中紧紧抱住的包裹都被这声吓得从怀里掉落下来,由于包裹里的东西太过沉重,又是垂直地掉落在地上,包裹受到冲击,外面一层的麻布散乱开来,将包裹里的东西顿时暴露在公堂之上。
妇人见状,赶紧将身体蹲下,迅速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众人的眼光,将滚落出来的东西缓慢地抱住怀里,塞进包裹里面。
“来啊,将鲁余氏拉开。”
县官见到此景情,包袱中必定有什么可以之物,他的话音刚落,两个衙役扑上前想将鲁余氏拖开,但是她紧紧抱住包裹,眼睛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将身体抱成一团,如果想将她拖开的同时也要将她怀里的东西一起拖开,捕头见此状,上前一步,对着鲁余氏大吼一声,在她害怕分神之时,将她怀中的包裹扯了出来。
包裹里面的银票和白银纷纷从松散包裹里掉落在地上,鲁余氏看着在空中像雪一样的银票,听着白银敲打着地面的声音,两眼充满了眼泪,忍不住用手捂着脸,跪在地上痛哭着,凄凉的哭声让大堂内的人都有所动容,只呆呆看着她哭泣。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不知道她是在哭自己被抓还是哭着死去的丈夫,对她来说,一切都晚了。
“鲁余氏,你包裹里的巨大银两是从那里来的?是不是杀害你丈夫以后,在帐房里面偷取的?从实交代!”
县官又一次敲打惊堂木,眼看天色也不早了,再让她这样哭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很显然这个问话打断了鲁余氏的哭泣,她缓慢地抬起惨白的脸庞,用衣袖擦拭着眼角的泪珠,红红的眼睛看着公案上的县官大人,轻轻抽泣着,点点头又摇摇头然后有点点头。
“你点头又摇头,到底是什么意思?”
鲁余氏看着县官大人,又转过头看着一旁的殷莫霏和无夜,然后一直向着他们不停的磕头,额头上缓慢渗出殷红的血来。
看着她样子,殷莫霏赶紧摆摆手,轻叹道:“其实银两的事情小,我不知道的是,鲁先生视你如珠如宝,为何会了这点银两就要杀死疼爱你的丈夫?”
“老爷,一切都是奴婢的错。”鲁余氏说道这里,眼泪又止不住地再一次流了下来:“老家的母亲身染恶疾,需要银两救治,我与相公商量,能否找老爷先预支工钱回去医治母亲,但是家中来信,说需要大量银两,是相公工钱的好几倍,相公说老爷最近有很多的事要处理,不想在增加你的负担,但是我救母心切,就让他在帐房里拿点银两,以后发了工钱在补回去,但是……”
鲁余氏顿了顿才缓慢地说:“他的脾气,老爷你也是知道的,从来不徇私,坚决不肯从帐房里拿出钱,已和奴婢几天没有说过话了,我想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到厨房里熬了一盅汤送去帐房,当时他的脸色有些好转,看见他喝完汤我就回房了,到了房间才看见桌上有大量的银两,还有一封书信,相公说是老爷已经让自己从帐房里支出银两,当时我才知道相公是如此疼我。然后我就入睡了,蒙蒙胧胧中听见外面说着火,然后就看见相公他……”
她说到这里,再一次痛哭起来。
难怪树叶上写着疑凶,正凶还是另有其人,本已将嫌疑洗脱的君宛灵又一次在没有证据证明下又成为嫌疑犯,殷莫霏暗暗感叹着。
“如果鲁余氏说的是真的,杀害鲁先生的另有其人,也不代表君姑娘没有罪。”
李柔摇晃着纸扇,嘴角处露出笑意,这个案件的凶手不管是谁,只要让这个该死的小贱人成为一辈子的嫌疑犯,关进大牢就好。
“李小姐说的甚是,现在这个案件错综复杂,先要调查鲁余氏所说是否属实才好进行下一步审理,那么下官可以退堂了吧?”县官看着两位贵客的脸色后才做出判断:“将鲁余氏和冰凌押入大牢,明日在审理,退堂!”
在惊堂木的响声中,鲁余氏被两个衙役押入缓慢地离开大堂。
“老爷,我不知道那银两是不是你给我们的,但是我相信我的丈夫,他不会骗我的,他说你答应给我们银两就一定是你答应了,没有想到他却遭此毒手。”鲁余氏临走时候,转过头,一边擦拭着眼角的眼泪,一边用坚定的眼神看着他。
“等等,你说是我答应借给鲁先生的?为什么我毫无印象?”殷莫霏吃惊道。
他并不是在乎这点银两,但是鲁先生与我谈起银两之事为何毫无记忆?殷莫霏看了旁边一脸疑惑的无夜,从这个反映来看,自己确实没有与鲁先生说起这事。
“主人,我记得前几天鲁先生一筹莫展,只有来向你告假会老家的时候却是满带微笑,难道说这件事是真的?”
无夜说的也却有此事,自己与无夜分开的时间并不多,难道真有此时,自己却不记得了?如果是真的,鲁先生的死是因为那件事,但是有是谁在鲁先生死之后补上后背一刀来掩饰?想到这里,殷莫霏的脸上出现了一丝不安。
余光望着身旁的李柔,她真含情脉脉的望着自己,但是眼神之中却深藏着算计,他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或者她知道些什么,顿时殷莫霏开始恐惧眼前的女人,如果她真的知道那件事,那么为什么要借此事来除掉灵儿,也许她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自己多想了。
“老爷,相公留下的书信可以证明奴婢没有说谎。”鲁余氏的喃喃道。
听道此话,县官的手在空中轻轻挥动两下,押解鲁余氏的衙役松开了手。
“你说的书信在什么地方?”
“回大人,在刚才的包裹里。”
捕头赶紧从装满银两的包裹里摸出一封已经揉虐的信件递交给县官,县官将信的内容大致地看了一遍之后,恭敬地递到殷莫霏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