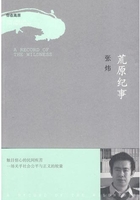马路宽阔但路面凹凸,各种型号的车辆狂奔乱走,司机狂按喇叭,狂踩刹车,一副暴土扬尘无法无天的景象,大约这种中等城市的交警深得老庄“无为而治”的精髓,司机们的信条均是那句民间对联“法外人法无定法”什么的。
有单个或手挽手的南方漂亮女孩在人群中穿行,她们时不时让我眼前一亮。
我在宾馆结账时从服务员那儿得知,汽车站就位于火车站广场。
我没有按照昨晚来宾馆的路原道返回,我选了另一条路,随便走走,也许走着走着就到了,万一到不了,再打听不迟。这种行为有点透着自己是大城市下来的,对中等城市一副“拿下”的自信。
事实也确实如此,我还没怎么走过瘾,就又回到了火车站广场。
路上经过邮局,我给李琴发了张跨世纪的明信片,这是我出门时,她叮嘱我的唯一一件事。
我趴在怀化邮局油漆斑驳的柜台上买明信片。明信片印刷精美,对折的那种,还有特制信封,好几块钱一套。世纪之交,邮政系统无疑又发了一笔。
我记得我给李琴的赠语大约是:祝你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进步!再迈上几个新台阶!我还说了去外地的感觉很好一类的话。
更大的进步——我是暗中鼓励她辞职、出国、嫁老外?
迈上新台阶——我是暗中鼓励她把我迈过去?
我想我有这方面的意思,同时我想她理解的估计是“祝她发财”一类的吧。
数年前,我刚认识李琴的时候,她刚大学毕业,我刚结束了与徐颖的那场艰苦恋爱,当时心中发誓再不能找那路死缠烂打的女孩。
李琴给我的感觉恰恰就不是这路死缠烂打的女孩,她的诸多西化观念与我一拍即合,而且她也称得上漂亮。
当时我跟哥们公布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时,曾经夸口:碰见波伏娃了!
几年之后的今天,我再也不敢这么提了。当然李琴性格敦厚,确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姑娘,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日渐乏味,我想她随时都将对我绝望,但这种想法也已持续了一两年了,李琴似乎停留在“随时绝望”这状态中不动了,我们之间越来越像兄妹,什么“绝望”、“分手”之类戏剧化的东西似乎永远不会在我们之间发生,我不知我们将这样“和平演变”到何时到何种程度?也许还真就白头偕老了?
对此种前景我无能为力。
中央屡次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跟李琴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切都压不倒稳定”。
这说明我们缘分极深?
由它去吧。
火车站广场上排着一溜中巴,揽客的吆喝声及发动机的隆隆声响成一片,我走过去碰到的第一辆中巴就是去凤凰县的,汽车前挡风后的一块纸牌子上写着“怀化——凤凰”,车内已满员,油门轰隆作响,车蠢蠢欲动,车门处一位中年妇女探出半截身子一边用当地普通话冲我大声喊着一边冲我招手。我问她去凤凰多少钱,她说20元,她又指给我看车内唯一的空座——油箱后面的一个小板凳……
我似乎已没什么可犹豫的,我还不至于对名人名胜避之唯恐不及,而且哪个县没几个名人名胜呢?而且我有一哥们去过凤凰,我好歹去看一眼回北京也有的聊……
凤凰县在当代产生了两个文化名人——黄永玉和沈从文。这二位我均不太了解,他们的书我也仅仅是翻过,没读过。
我在凤凰住了近十天,在这个弹丸之地四处乱转,但这二位的故居我就是没撞着,当然我也没有特意去寻找。看来我跟这二位没什么缘分。
在凤凰的最后一天,我本想是不是去沈从文故居看看,因为我听我每天必去的那家饭馆姓王的老板讲,沈从文故居离我住的县招待所也就几百米。但当我收拾好背包,退了房,我还是直奔长途汽车站了。
那天是个阴天,我只想尽快离开凤凰。
关于黄沈这二位文化名人,我想再说两句。我知道沈从文后半生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另外好像出了本书,叫《坛坛罐罐》什么的,他们的具体情况我没研究过,我只是感觉,湘西大山,历来出土匪的凶蛮之乡,现在出了两位这么有“品位”“趣味”的中国文人,是不是挺有意思?
同时由这二位,我也想到了一串中国文人的形象,古代的,当代的,那个趣味啊,味道啊,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啊,花鸟文化妻妾文化古董文化啊,老北京老天津老上海老房子老胡同老照片啊,那叫一个细腻,那叫一个得意,那叫一个小气,那叫一个……无耻!
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就算少年吧,他们(黄沈二位)的经历若加诸于我身上,我可能做得更次,但这不能阻止我说出我的感受。
10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稀里糊涂就上了去凤凰的车,我在此费这么多笔墨就一个目的:我去凤凰绝非奔着沈从文和黄永玉。
我怎么这么麻烦,我这岂不是越描越黑?
我在反文化吗?但其实我只不过是用一种文化来反对另一种文化罢了,否则我就不会这么麻烦这么做作其实就是……这么文化!
我忽然发觉,我这次出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文化气息:世纪之交,孤身远行,不定目的地(以“漫无目的”为目的),逃脱及躲避一切成形的生活和观念,难道这他妈不是一个巨有文化的人的所作所为吗?
一个混混,一个农民,一个工人……
一个官僚,一个职员,一个商人……
一个妇女,一个老人,一个孩子……
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就去苏锡杭了,人家就去新马泰了,人家就待在家里大宴亲朋看电视了,人家就拎着点心水果串门了……
怎么到你这儿就得这么累?
我的这路“文化”,从何而来的呢?
英美垮掉派?日本“斜阳族”?面对恺撒说“别挡了我阳光”的第奥尼索斯?竹林七贤李白柳永?郁达夫鲁迅?禅宗祖师爷慧能?庄子?兰波?达达?《迷墙》?王朔崔健罗大佑?周星驰?侯跃文石富宽?“北京二赵”及天津苏文茂?
不再贫了,或说不再炫耀本人的知识体系了,总之,这些,就算我的“师承”吧!
11
得承认,从怀化去凤凰的路上我心情愉快,我坐的那个位置在油箱之后,虽说油箱上堆满行李,但不挡我视线,我坐的板凳是椅子的高度,我视线开阔,只是抽烟时要找行李的缝隙弹烟灰,这类长途中巴永远都是塞得满满的才肯上路。
这天天气晴朗,汽车在湘西的大山间盘来盘去地穿行,景色称不上心旷神怡却也安静迷离,山间有雾,阳光是那种黄蒙蒙的。
那位卖票的中年妇女始终站在我身旁车门内的脚踏板上,整个行程近三个小时,她就这么一直站了过来,有几次我前面油箱上的行李几乎出溜到我怀里,她总是及时帮我扶正。我对她心生敬意,在后半程我几乎一直在作这样的思想斗争:我是不是跟她换换?
可我始终没动,其实到后来我已坐得腿发麻了,极想站起来伸展伸展,可每次话到嘴边,面对这个脸膛粗旷红润的妇女所显现出的那副神情,我的话又咽了回去,那神情所显现出来的是一副天意本该如此的心安理得,且她毫无疲态,时不时嗓门很大地用方言跟司机热火朝天地聊天,看她开心的那副样子,我的让座别再吓着她,至少她或许会觉着我有毛病?
到了后来,激烈的思想斗争又让我悟出了点道理(找辙?):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不可随意造次,地主和长工是你说换就可随便换的吗?在一定限度内的不平等似乎就是天意,吃肉吃腻了吗?忍着点吧,正如长工渴望荤腥不也一样得忍着,得苦中作乐?直到越过了那个限度,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每个等级的人都受不了了,那就起义吧,造反吧……
我又明白了为什么历次造反运动中的头目、核心都出自“朱门”,这帮家伙是吃饱了撑得难受啊,加之奴隶们实在也是饥寒交迫了,禁不住添油加醋一通煽乎,就“起来”了……
我没有坐得两腿发麻直至疼痛,她也没有站到眼前发黑冒虚汗(我敢肯定让她眼前发黑比让我腰酸腿疼要难),我们就这么待着吧!最后,我几乎是这么倒过来想了:她占据了全车唯一一个可以伸直腰身的位置(脚踏板上因堆有行李只能容一人站立),应可看做她在利用职权搞特殊化呢。
于是我不再想了,再这么下去我真成文化人下乡了。于是我便安心地抽烟,安心地看风景,并且在有限的空间内变换着坐姿,做些有限的舒展,好在已进入凤凰县境内了,忍忍就到了,你高尚也罢,你卑琐也罢,届时在县城汽车站都将随着你身体的直立而烟消云散。
12
我在凤凰绷了三四天,终于还是开始嫖了,其实也谈不上“绷”,主要是我孤身一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不敢贸然行动。
而且湘西出土匪是有名的,有部电视剧叫《乌龙山剿匪记》,还有部书还是电影就叫《湘西剿匪记》吧,说的就是这一片发生的事,我出门前有来过此地的朋友对我说,现在那儿已经没土匪了,要有也是官匪一家那种,公路上设卡子和收费什么的,占山为王劫富济贫那种早就没了。
这我倒是信,但土匪没了,土匪的遗风或许还在?比如民风凶悍什么的。
三四天之后,我的心里渐渐踏实了,除了当地自产的那种震天响的土炮仗每每让走在街上的我心惊肉跳之外,这儿的民风几乎可以称之为“温顺”,是否淳朴,倒是没看出来。
看来当年,这共产党确实有两下子,你不服是不行的,剿匪是彻底剿干净了。
温顺就好办,哪怕是一肚子奸诈的温顺,因为对于如我这般一个准流浪汉的过客来说,“奸诈”可以说毫无用武之地,还没等你把我骗了,我已飘到别处去了,而且关键是我也没什么好骗的,对我犯不着花这等心思,对我这路人,打小最怕的,就是放学路上被蛮不讲理的痞子拦住——“把兜给我翻出来!”——对此我是一点招没有,只能乖乖照办,干吃这个亏。
“骗”,我是不怕的,我只怕暴力,从小到大,唯有暴力可以制服我,制服我们,虽然是口服心不服。
他们用别的招都不灵(他们也够笨的,骗术永远是那么拙劣,从不长进),唯有用暴力这一招,他们还真是“一招鲜吃遍了天”了。当然,有些人已经受到了报应,比如家长、女友、教师……但有些,至今拿他们没办法。
13
无论如何,“嫖”这个行为至今在我心理上仍不是很自然的事。
我想嫖,甚至可以说,我打小就想嫖,大约十年前,我还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以一个妓女的身份写了一篇歌颂娼妓的小说。那时候社会上还没什么鸡呢。
从理论上,我是早就想通了,然而我的行为却严重滞后。
从深圳到北京,朋友们带我出入过不少的歌厅、迪厅、洗浴中心等淫乐场所,我的表现基本上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尴尬”。有时候我甚至想,我他妈干脆做个“老八板儿”得了,那样倒也省心,可立码我又觉得,那样我怎么能甘心?
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心理健康的嫖客呢?而且像我这路人,对自由、浪荡、云游满怀激情,不仅排斥婚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良家妇女的认识一步步加深,“不能碰她们”——这几乎成为我的一个生活准则。难道我不是比那些拖家带口的家伙们更有理由去嫖吗?
为什么我这种人却在这方面有着严重的心理障碍呢?这不是不给哥们活路吗?
不行!我要去天涯,我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将自己投入烟花柳巷,折磨我吧,挑逗我吧,让我的身心彻底跟女人亲昵起来,如歌里所唱的,我“已等待得太久太久”了。
14
我想再次隆重声明,我去凤凰,与沈从文无关,更与黄永玉无关。
我为此值得这么“隆重”吗?搞得像要洗清自己的耻辱一般?
我觉得似乎还是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