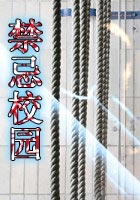那天晚上,我没有回自己的公寓,在妈妈那里住了一夜。我无法一个人面对这些句子,特别是在黑暗里。他还爱我,而且从一开始,就爱的比我想的要多得多。但此时,他却身在天涯,完全不知道我心里的感觉,以为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他为什么要离开我?”我脸蒙在被子里流眼泪,说的语无伦次,“他还爱我,他写信,却不是寄给我的。他可以什么都不要管,告诉他要我,我哪里都不会去,我会永远跟他在一起的。”“他爱的不一样。”妈妈说,然后打趣道,“Les artistes sont les nouveaux aristocrates. 艺术家们是新贵族。总是爱做些拐弯抹角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误会了,如果他不来找我,我也找不到他,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巴拿马,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珀斯…他在环游世界,地球是圆的,他总有一天会到巴黎的。到那个时候,他会看见你比他离开的时候更漂亮,比从前更好更懂事。”“哪一天?”我固执地问,当然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务实的英国人福克花了八十天环游地球,超现实主义者格列佛花了八年,那么林晰--这个表面上现实主义,骨子里无药可救的浪漫主义者需要多长时间?林晰的影展在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开幕。我去了,一个人。所有的照片粗看都是风景照,却都远远的小小的藏着一个朱子悦的影子。La vision d’amour,情人的视角,似乎是个很好的卖点,开幕当天很多人来参观,遗憾地发觉没有摄影师本人出席。现场放着些白色的花篮,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遗作展览。离开那里之后,我独自走在入夜后的街头。一阵风吹起,寒意突如其来,街上的行人都不约而同地扣紧了衣服、加快了脚步。我却在玛比隆地铁站入口处的台阶上突然站定,那个瞬间,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现在,唯一一个指向他行踪的线索也断了。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开始是热的,很快在风里变得冰冷,我手忙脚乱地在包里找纸巾。一个过路人递给我一张印着“Manga Café”标记的纸餐巾,我没有抬头,说了声“谢谢”,擦掉眼泪,走进人流里。哭过之后,我意外地发觉自己仍旧有勇气和力气去做每天要做的那些事情--上课、读书、参加小组学习、做饭吃饭、打扫房间等等,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长大”吧。
而与此同时,我又有了新的麻烦。原以为很好相处的新室友一声不响地把房间转租给了其他人,一直到搬家的当天才通知我:从明天开始你就要和一个男人同住。第二天,男人搬进来了,告诉我他名叫华胜杰,二十一岁,刚刚大学毕业,来法国读建筑的,下飞机的时候身上只有几百块欧元,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手的地区奖学金。我有点惊讶自己竟然能在这种情形下面,心平气和地帮旧室友搬家,友好地说再见。第二天又主动向新室友提出来,星期一早上陪他去银行开户,只因为他几乎听不懂法语,也不认识路。我自嘲地想,自己可能真的是变了。我清楚地记得华胜杰搬进来的那天是十月二十五号,因为,就是在两天之后,一则看似微不足道的新闻报道在法国各地三十多个城镇引发了将近三周的骚乱。十月二十七日晚间,巴黎北郊的克里西苏布瓦市,三个男孩为躲避警察追捕,在一处变电站内触电,其中两个当场死亡,另一个重伤入院。警察在随后召开的媒体发布会上否认曾追捕这三名男孩,声称他们去当地是为了调查一起抢劫未遂案。事后,几百个愤怒的青少年走上街头,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商店,袭击了一所消防站,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随后的一个星期里面,骚乱迅速蔓延到巴黎市郊各处。我住的那个街区也有不少半大孩子效仿那些住在城市北面的先驱们,每天早晨出门都能看到被烧毁的汽车、垃圾桶、被砸得粉碎的公车站和商店橱窗。我并没觉得害怕,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几个礼拜都没洗车,存心弄得又脏又旧的样子,只穿洗退了色的旧运动衫出门。那段时间,妈妈三天两头打电话过来催我搬家。我敷衍着答应了,却一直拖着没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担心那个二十一岁的小华,可能因为他是林晰的校友。他晚上要打工,在市区一间公司做制图,我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在地铁站等他,把他从那里带回家。几天之后,我给他剪了一次头发,虽然剪得很不好,他却不介意,好像还很开心似的。也就是在那一天,我正拿着理发推子研究如何补救他耳朵后面一块剃坏了的地方时,从镜子里瞄到一眼他的表情,方才想到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头了?不管后来如何保持距离,我隐隐担心过的状况还是发生了。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法国各地的骚乱逐渐平息,新闻里终于看不到游行、催泪瓦斯和防暴警察了。而他做好一桌子的菜等我回来,告诉我他喜欢我。于是,我只好搬家了。找到房子之前,我每天早出晚归,尽量减少跟我那个男室友的接触。
有的时候晚上有课,我就背着个行李袋,装了换洗衣服出来,去我妈那里过一夜。那段时间,我隔三差五地出现在图尔农街那间顶层公寓里,有的时候事先没打过招呼就跑去了。妈妈自然是没什么说的,难得的是强恩也表示欢迎,而且看起来也不像是假客气。有几次,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写作业,他看到了,还会热心地跑过来帮我分析一道财务题目,或是侃侃而谈地讲解法国和美国会计准则之间的异同之处。日子久了,我不禁有些内疚,想到自己过去总觉得他太老太俗不够Chic(时髦别致),身上穿的衬衫总好像大了两个码似的,在巴黎和南特待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法语仍旧讲得怪怪的,始终都搞不懂妈妈究竟看中他哪里了?接触得多了,才渐渐地发觉他似乎也是个很不错的人,脾气很好,很有些学识,为人处事也很有风度。
不过,内疚归内疚,我对他还是客气而疏远的。直到有一次,他看到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十八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作业,告诉我他最喜欢的画家是弗朗西斯克·加尔蒂。我惊讶地笑起来,拿给他看我一直当做书签用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的就是加尔蒂的作品《威尼斯大运河》。在让·巴普蒂斯特·柯罗之前,这个威尼斯人就是欧洲大陆上最诚实真挚的记录者了。一天早上去学校上学,停车的时候,遇到我同班的几个人,刚好被他们撞见我大包小包颠沛流离的样子。我自嘲地解释,原来的地方住不下去了,正在找房子。一个男同学瞪大了眼睛,夸张地问我:“你露宿街头了?!”两个女孩子提出来,我可以暂时住在她们那里。我谢了他们,很开心自己竟然变得这么受欢迎了。
转过头来,又觉得自己在小华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实在是太小孩子气了,懂事一点的高中生也不至于这么不上路的。那天晚上,我又跑去他打工的地方找他,拉他去附近的小餐馆说话。看他一副不情不愿不尴不尬的样子,我心里也没底这事情要怎么讲才能既讲得清楚,又不伤面子。从晚上九点到深夜十二点餐馆关门,我第一次把过去八年里发生的事情说出来,讲给另一个人听。我讲得那么平静,没有掉眼泪没有哭,说到特别美好的地方会忍不住露出微笑。他安安静静地听着,跟我一起笑一起难过,时不时地问我:“后来呢?”出了餐馆,我们在深夜冷落的街头走着。小华对我说:“如果他能听到你今天说的这些话,他肯定会回来的。”我在心里回答:问题就是他听不到呀。权且当是种安慰吧,我没有说话,转过脸去对小华笑了笑,开车带他回家。在我找到房子搬家之前,我们又做了几天的室友,后来也一直是朋友,经常一起出去喝酒或是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