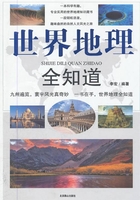抢劫是在这个时候莫名其妙就开始了。
这世上所有的突发事件都是莫名其妙就开始了。
这些劫匪应是十分的年轻,当其中之一踩上柜台监管众人时,他看见这人穿着NIKE的经典款型。
手中拿的枪亦都是AK-47,标准游戏玩家心态,嫌点三八不够气派。
劫匪跑走后几分钟,警察和电视台才赶到。
他受点擦伤,并无大碍,只是晚间做梦,梦见有一天一地NIKE鞋子向他扑过来。
是电话铃声将他吵醒。
听时,是她的声音
——我在新闻上看见你。那样慌乱中,你是如何保持仍然戴住那顶红色圣诞帽子?
呵,到底还是被她看见。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诚心要找一个人,不会找不到。
他就不再回答。但其实,这样的话从她口中说出来,简直要令他感动了呢。
停一停,她又说
——你没事便好了。只是这段时间那么乱,今后出门,至好是戴个电饭煲在头上。
他和她都对住电话笑,仿佛旧时光又回来。
令他错觉或者她亦不是不在爱着他的,或者她对他是有一点真心的。
然而,这个猜测亦不是错了,亦不是荒唐。
只是他永远不会得到确切的答案。
是在当年圣彼得堡最后一场雪浩荡降下时候,他去见她,向她求婚。
见他来,她看上去十分高兴。
说自他走后,再没有人可以坐在灰天空下陪她听伦纳德?科恩,大雪天亦再没有人同她争吃家中最后一个泡面。
他打断她,郑重同她说,他爱她,想要同她结婚。
他几乎可以听到这句话在她心中惊飞群鸟。
但她竟然做得到淡淡然笑一笑。
她同他说
——呵,你多傻。干什么要给我一个教训你的机会?本来你对我没有需索,我对你便谈不上拒绝。其实是,若你同其他男子一样避免同我奢讲感情的事,仅仅肉身相对便是好的,亦不能不算拍手无尘,两厢清白。然而你来同我讲爱,又没有力量令到我着魔一样来爱你。分明你要给我一条因寂寞而结婚的路,呵,它太暧昧太浑浊,你清楚我,我不肯走的。
——如何你便肯爱那个老人?你父亲都应较他年轻。
——我爱他跟我不爱你完全是两件事情。但若你一定要扯到一起来说,我只能告诉你,我的爱太有限了。
——但我这么爱你。
——呵。你看窗外这一场大雪,当它下时,你以为它不会止歇。但雪终于有停的一刻,再强烈的感情都会过去。
他整个肩膀塌下来,十分颓唐,似是天地间再没有值得背负之事。
她安慰他
——难道你还没有发现?对我这样的人,这样的感情方式,还是做朋友来得要长久些。
说这话时,她神色间闪过一丝悲悯,亦不知是对他,抑或是对她自己。
过两日他又去找她,只见门户大开。
内中空荡荡。
呵,戏已散了么?
室内残留几张报纸,长窗风来,吹那报纸扑飞如鸽群。
他退出去再看看房间号码。恍惚间似听见伦纳德?科恩那一把铜器般沙哑声线“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他不能相信她竟然走了。
大厦管理员认得他,来同他说
——那位年迈的先生深切手术失败,死在手术台上,她已不必留在这里。一早决定下来的事,难道她没有告诉你?
他说不出话来。
她永远令他说不出话来。
那管理员犹在滔滔不绝,不知已是第几百遍说这回书,十分流畅
——自我认识她,她便已是他的情人。当日你搬来这里跟她同住,简直令我惊奇,她是一向没有什么好名声的,怎么你却不懂得忌讳?
那一日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动手打人。
而她竟然已经离开他的生命。
这世间情爱稀薄难求,所以爱这回事,不论结局如何,都是一种杀伤。之后,有人逃亡,有人身亡。
有时他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她。
呵,以为。
若是他在黑暗中吸过他午夜的几支烟。
入睡时便会得梦见她。
梦见她蹲在面前,似一只瘦削的大白狗,说自己想在天际线上开一树金合欢花,还说这样就快乐了。
他在揪心疼痛中醒来。
倾尽一生无法将她的幻影赶尽杀绝。
他亦没有办法令自己不去爱她。
即使她杀死他,杀死他的感情,七十个七次。
身未动,心已远
没有理由的她就觉得厌倦。
从前她单单是为着该男子削水果时微微抿紧的嘴唇就爱得扑天扑地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爱的急失,实在只能用诡异来形容。
真的真的不是没有爱过这个人。
她同自己辩驳。但有什么用。连身体里面最坚持的那个自己此刻肯承认的亦无非只是“爱过”。
在熟知了他十三件衬衫同九条裤子的搭配规则,三样领带的结法,七种表达不满的方式之后,她发现自己对他失去了爱人的心情。
裸足
在她十二万分的厌倦中,气温如常跌落至零下。
又到呵气成霜季候。
她裸足穿浅口高跟鞋。鞋面有黯蓝扶桑花。
脚背皮肤冻至青苍苍,街灯下明明白白映出昏黄光泽,如小块绸。
她抱大捧温室百合,白色。
它冰冷地靠近她的怀。她便收拢它在胸口,如抱婴孩。
暮雪是这个时候这个样子开始降下。
她裸足踏雪,急急归。
街角音像店播放老歌,少年时她热爱过。
彼时的她同此刻这一个抱花疾行的女子,截然是两样的。
至少当年的她不穿高跟鞋。
那时候成日只得软塌塌一双短靴,鞋带松松系住,一脚蹬上便可跑走。
想到这里她就笑一笑。
笑时闻见百合香。
陈酿
所以她同她的新邻原先生是如何认识其实根本也不重要。
反正不是这一个,亦会得出现另一个。
当然最好是这一个。
因这一个恰恰是情逢对手的。
那一日是如何。
那一日暮雪,十二万分厌倦中她抱花而归。
电梯内遇着一个男子。
那男子不年轻,领带深酒红,婉转系一个温莎结,呵,老风流。
巧得很他共她都往二十九层。
出电梯,他向左,她向右。
五日后,百合恰恰开到败了。
他许是算准了时辰,抱花瓶中插大捧白色香花来访。
那花瓶冰静剔透,如一口巨大玻璃樽。
上有两点水珠一前一后滑落至她地毯。“噗”。然后又一声“噗”。
她并又注意到,他抱花瓶时候那么用力,像抱着情人。
她就知这男子是可以令她欣悦的,在她认为自己已然是昏聩了的疲惫时分。
他大概是在十五岁就学会了沧桑,所以直到五十岁仍会同少年时一样的男子。
老式做派的情种。
这个时代仅剩的听黑胶唱片用蘸水钢笔的人。
爱情出师无名
自认识原先生她便忐忑不安。
连他送来的白色香花竟亦较其他花束盛放得长久。
莫非他有无边法力连薄情草木亦逃脱不得。
有时,对住仍同她共鸳枕讲亲爱的情人,她幽暗心里有个小小声音
——做些什么,阻止我。我就快要爱上别人了。
但他又听不到她的呼告。且听到了又能如何?
甚至之后发生一件事令她放弃同自己抗争。
那一日,她的情人竟鬼使神差向她说
——你看,没有我你怎么办,谁来安慰你的寂寞?
她觉他荒唐,大力驳他
——一切好处你都占尽,口头的便宜你也要贪,你我都寂寞至此,即便说安慰亦是相互的事,什么叫没有你我怎么办?
他自知失言,到底是有些脸皮的男子,立即噤声。
终于她肯使自己知道,寂寞的人以相互伤害为乐,且对方怀抱再暖再坚实,亦不过同时要她以自身怀抱支付,说到底是一场交换。
而大凡不见得有好理由跟好代价,但只觉必须要去做的,不那么严格来讲,便已经是爱情。
夜来
于是她同原先生在一起了。
但是否可以叫做在一起呢,如果两个人走出电梯仍旧掏出各自家门的钥匙。
然而在一起就是她同他常常将时间消磨在一起。
反正时间怎么样消磨以及同谁消磨都差不了太多。当然。是这一个,那就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