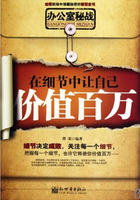他果然深更半夜地把车开了出去,买到了治理外伤的药,给她身上红肿的地方包上,特别是屁股,不仅给她喷上外用的止痛药,还内服了其他止痛药。接着把她抱上床去趴着睡。她这才勉强地睡着了。没有睡着之前,还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感动了:打她,她也认为这正好说明上原爱她,是因为她之前“欺骗”他,他生气了才打她的。
第二天,她的腿还很疼,几次爬起身来,都只能拖着一条腿走路,她只能打电话给学校请假了——这是她一年多来第一次请假。
为了安抚她,或者说表示诚意,同时也是表示她是他的人,他还请来隔壁几家的几个老人为他们做了订婚的事,也许是他给的钱,这几个老人竟然给他们买来了干墨鱼、海藻(分别象征男性生殖器和能生育的女人)、一根长长的亚麻线(表示白头偕老)……这些是日本传统订婚仪式上东西。
离婚协议寄出去之后,她都胆战心惊的。果然,如她的预料,一个月后,她原单位领导就打来电话,查问她为什么要离婚。她说是感情不和,但单位领导不是傻瓜,他们问她已经留学两年了,要离婚为什么不等到回来之后再说,为什么这几个月都耽搁不了?她只能撒谎说,那就等到她回去再说离婚的事。不过,单位要她立即回国。她怎么发誓要回国都不被领导相信了,最后领导说最后一年的留学费用由她垫付,她回国后再进行报销。
她索性以此作为借口,再一次向她的丈夫提出了离婚。那边不同意,她便授权她弟弟向中国当地法院申请离婚了。她丈夫找不到理由,他们也就离了婚。
办完这些事已经又过去了半年,如果她不赶快与上原直行结婚,她毕业后就会被入管局勒令回国了。这下轮到她向他要求结婚了,她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们刚刚吃过饭。上原直行打着饱嗝说道:“我还没有与她离婚呢。不过,你等着,她的病已经很重了,活不了多久了。”
没有与她离婚呢!她却不敢发脾气,而是温柔地给他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让他赶快去办。
他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要让我生气,今后打工的钱也要给我。”
她没有办法,却也答应了,虽然给的也只是一部分。有一次,也许是担心她毕业后就回国,他竟然带她看他在新潟的住宅,那是他买的,现在由他老婆住,他说他今后与她结婚了就住那里。
那是一套大约七十平方米的套间。她见到了他的妻子——一个看上去很可怜的人,也许是因为病重的原因,头发很少,也理得很短,像一个老男人似的。看到上原回来的那一瞬间,他妻子很高兴,但看到他身边的女人,表情也就暗淡下来了。
“我就要死了,我们夫妻一场,你就不能让我快活地死吗?你不仅不来看我,还把这个女人带回来。”
没有想到他说:“你这样活着,还不如早一点儿解脱。”
他妻子立即气得站都站不稳了:“我知道你不提出离婚的原因,我现在要求你离婚,你不要想在我死后,什么都霸占了。”
“什么是你的?都是我挣的钱。”
“我不给你做家里的事,你能挣钱吗?”
上原气得在房子里转,可他不敢打老婆,他是怕老婆经不住打,打死了就麻烦大了。其实,动一个指头都不敢,因为有家庭护士在——这是属于医疗保险的范围。如果不是,他也许是不愿出钱请的。
他老婆转而对她说:“你不要与他结婚,上他的当,这个人又自私、又凶恶,等到你有一天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一样对待你的。”
她听进去了。然而留在日本的想法,似乎比什么都重要。相反,她似乎也与上原一样,希望他老婆早死。
然而半年后,她老婆依然活着。而她领到了毕业证件,签证也已经到期了。她没有回国,黑了下来。
那一段时间,她见人就说,她在日本旅游一个星期就回国了,她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却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过起了担惊受怕的日子。只不过,她与上原住在一起,也就不需要什么担保了,他倒是很用心地给她找到另一家料理店打工。于是,她对上原更是百般顺从了,还给他打洗脸洗脚水。他不高兴的时候,就会打她的耳光,她还自我安慰,比他原来打她时要轻得多了。
上原倒是守承诺,经过他的担保,把她弟弟弄到了日本留学,在广岛读书、打工。
这下他更是趾高气扬了:“我是你们家的恩人,你们姐弟这一辈子都报答不完的。”
稍不顺心,他就打她,不需要什么原因,只不过是担心打重了,她上不了工。他有时候还砸东西,但这个吝啬鬼不砸稍微贵重的东西,砸碗、扔筷,还有撕她的衣服,撕的都是旧衣服。
有一次她弟弟从广岛来看他们,也许是送的礼品少了一些,上原就挑了她一个毛病,当着他的面打她。她弟弟只是不停地推眼镜,仿佛这才看得清楚似的。她弟弟当然也生气,可制止上原动手的姿态都没有做出过,只是一甩手就离开了他们家,她弟弟把这称为忍辱负重——上原不在的时候,她弟弟也会这样说。
“等到老子赚够了钱,会教育这个杂种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上原就要在郑丽弟弟还没有赚够钱的时候,打够她。有一次,他怕打伤她,就用手勒她的脖子,要不是看到她小便失禁已经流了出来,他住了手,那她就可能死了。
她忍耐不下去,也会想到入管局去自首,再回国去,她甚至编造了一大堆能欺骗原单位领导的话,从而能回到原单位上班。可她毕竟下不了决心,因为她弟弟经常劝她。
她偶尔到广岛去看看弟弟,去了也就不想回东京了。
这一次,上原没有事先说什么就赶到了广岛,进了她弟弟租用的房子。她弟弟没在,他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看你在这里做什么的。”
随即他看到了放在桌子上的一大堆相片,是她与家人照的,这其中还有她与她的前夫合的照片。因为她已经学会想念她平庸的丈夫了——-他不仅从不打她,还事事顺着她。
“我知道你厌倦我了,你把我今天弄成这个样子,就要跑回去了。”
他开始用拳、用脚、用桌子狠狠地打她,她知道大势不好,拉开门就向门外跑。然而没有来得及穿鞋,一出门就被楼梯的边角刺了一下,摔倒在地,这下他把她抓住了,把她的头塞进马桶里,开了水,给她灌了几口脏水之后,又把她扳到地板上。
“小弟,快来帮姐姐。”她咳嗽着,在迷糊中喊叫,并重新向门口冲去。
她弟弟这一次的确没有在,到外面打工去了。
他再一次把她抓回来之后,凶狠地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撕下来。“跑吧,跑吧。”他竟然还笑了起来。
这虽然是初冬,却也有零下几度了,他本来是不需要再打她的,寒冷足以让赤裸裸的她冻僵,但他等不及了,挥动着拳脚,直接打在她每一块肉上,一直打到她不能动弹,小便都流了出来,他才住手。
“死了吗?死了才好。”
他看到她真的不动弹了,这下才急了,他不想送她到医院的,但一旦她死了,他知道他就完了。于是,他叫来住宅附近的一家国立医院的急救车……
她哭泣着讲这些事,其间许多次,我们都忍耐不住让她报案,她说:“我没有身份,报案后,警察会把我抓起来送走的。”
“那你决定忍耐下去?”我想说:既然决定忍耐下去,还找我们干什么?
她无力地说:“我要让他与我结婚。”
“你还要与这个恶魔结婚?你让我们来,就是要让我们要挟他,逼迫他与你结婚?”
这时候,她弟弟也进来了。他了解我们的身份后,说:“夫妻吵架打架也是难免的,只要下次不犯同一错误了就行,报案太绝情了。”
我的上帝,人不要自尊,你说什么都是枉然的。我说:“他们是夫妻?上原直行还没有打死人对吧?”我想发火,却发不起来。
“实在不行,我想让他赔偿一笔钱,最少也要三百万,还要继续给弟弟担任保证人。”
我竭力做到平静地说:“你给他讲过你们姐弟俩的打算了吗?”
她弟弟犹豫了一下:“我对他说了。”
“他说什么?”
“一开始,他都同意。可昨天我再提这件事时,他说他为我担保没有收取我的费用,这些就算补贴我姐姐了,他会继续给我担保。我再说他不守信用时,他却说:如果我们再逼迫他,他就自杀。”
年轻记者刚才听不下去,走开了,回来听到她弟弟的话之后,大声说:“且不说他会不会自杀。他这样打你姐姐,你们还害怕他自杀?你们真够善良的。你们都这样,我们还能怎样?”他又走了出去。
她弟弟看了看我,还想说下去,却又不说了。
“有话就讲啊,你们姐弟急死人了。”
“他说中国人除了要钱就不知道什么了,他愿意与我们这种最低级的民族打交道,已经很不错了。他打了我姐,我们要钱又怎么样了?”他弟弟努力用一种理直气壮的口气说。
我能说什么?我不知道应该对谁生气,我甚至可以从她弟弟的眼神里看到这样的内容:上原既然连你也骂了,我们就应该一起对付他,要让他赔钱怎么的。可他付了钱之后,是否就可以继续打人?
年轻记者此时把上原直行叫到了病房,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你必须赔偿郑丽三百万日元,一会儿就去取,否则我们立即报警,并且要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打她,并且答应他们的所有条件。”
上原鞠着躬谢罪,满口答应,写了保证书后,就跑了出去,从他的信用卡上取了三百万日元,送了回来,恭敬地送到了郑丽的手里面。
到了下午,我与记者离开了,他们姐弟俩对我们恋恋不舍的,她弟弟送我们出去时还心事重重的。
我们分手后,记者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猜想:郑丽一旦出院,上原就会要那一笔钱,她也一定会给他。我们其实白来了一趟,既不能报警,也不能登报说什么。”
我与记者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