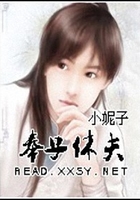接下去几天,二人携手遍访美食,漫游名胜。最值得一提的是顾子瑜心心念念的华山论剑,说起来别提多么豪气干云或侠骨柔情!
按照旅游手册指示,两人先去玉泉院逛一圈。中午12时光景,巧遇一道士正在路边吃午饭,顾子瑜贼溜溜地挪过去瞟了几眼,回来后跟蒋慎言描述了所见“两斤酒、一斤牛肉”的江湖气,大叹老子门人投靠了金庸!再往前走,又见一道士正与游客打乒乓,仙风道骨与凡夫俗子相得益彰、各取其乐,顾子瑜又是感叹奥运助长全民娱乐。蒋慎言大叹绝妙,当然,指的是顾子瑜。
然后,就正式往颇有武侠气的华山进发了。索道竟然在检修,顾子瑜眼见身边一顶顶下山的轿子,偶尔露出的行人脸上尽是疲惫萎靡,顿时生出一种想死的心。她想,若是天赐神力真让她爬上了,估计也得是明日凌晨,然后,要么去舍身崖纵身一跳,只当了结尘缘,要么就拿沉香劈山救母的巨斧一头撞死。因为她很难想象爬上这千层云梯,她的腿还是否健在。
最终,还是在蒋慎言的怂恿兼软磨硬泡下,一脸不情愿的顾子瑜挥舞起了细胳膊细腿。路遇一操粤式普通话的下山游客,颇为好心地提醒他们:山上很冻。当时两人都没有放在心上,后来才体会到不听劝的下场。
华山之险非文字可以言明,顾子瑜偶尔往下望便要吓出一声冷汗,怪石千仞,山体陡峭若直。李白真不该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估摸着他是没爬过华山吧。再望向索道上的闲置的小车厢,似悬在万丈深渊上,全身依靠那细细一条缆绳,仿佛一阵风袭来便可吹落。
坡度随行进渐渐加大,台阶一望无垠,两人的速度也直线下降,当然,一切是为顾子瑜之龟速拖累。尤其行进过程中,她还要时不时回望几眼,看了更加惧于陡峭程度,腿都开始脱力,于是步伐更见沉重与煎熬。
可随即,顾子瑜的小宇宙不知何故蹭地一声就窜了起来。大改之前的蜗牛状态,她雄心勃勃,大吸一口气,憋住,连蹬十几二十级,然后喘口气,待肌肉中的乳酸被循环掉,再狂吸一口气,憋住,狂蹬。如此循环,看得蒋慎言大叹折腾得够呛。
后来再问她,原是被那会儿过路的两位旅人深深刺激到了。“我好歹也是一年轻人,居然被一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赶超,说出去面子往哪儿搁?更过分的是,另外一个超过去的还是残障人士,愣是被人搀着一步步边跳边挪,路过了我。咳,你说说,我能不爆发么?”
蒋慎言恍然大悟。可真的感谢那两位仁兄!否则他俩上山都不晓得是二零一几年了。
到了半山,看着隐在云雾中的夕阳,蒋慎言不无感慨的说道:“若真像金庸先生所言,华山派在此修行,那么御剑飞行,终日欣赏如此大气磅礴美景,该是何等自由快活!”
“诚然,华山派出了个令狐冲,但更多的还是岳不群、林平之之流。我仰慕华山,完全是因为射雕、神雕里东邪西毒南丐北帝中神通的华山论剑!”顾子瑜边忍痛脱去被血泡浸湿的鞋袜,边不屑道。
登龙并无太多困难,身体前倾、手扶锁链、眼看脚下即可,大抵是小宇宙持续升温的缘故,顾子瑜终于回复了“顾大胆”的勇气平均值,七八十度的倾斜完全不放在眼里。而后到了天梯,奇险初露端倪,八九十度道并不长,顾子瑜兴奋地跃跃欲试,手脚并用就爬了上去,一边好奇地往下张望,一边对身后死死拖住她,令她不得不紧靠峭壁的蒋慎言腹诽不已,愤愤难平。
到金锁关,也就意味着离东峰不过一个小时行程。传说把锁系到金锁关,在登顶至山巅时将钥匙扔下万丈悬崖,象征阖家欢乐同心同德再也无法分开。顾子瑜是不太信啦,但还是由着蒋慎言虔诚地脱下手套,将两个金光闪闪的锁挂上并合掌许愿。而她在一旁看着,只是不断感慨,三天内这金锁铁定被撬。
再走,居然没路了,入眼处不过是个平齐山脊。顾子瑜纳闷不已,再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云梯在此!绝对竖直的坡度,几十米的锁链横贯上下,石阶窄到只能容下前脚掌之一部分。紧挨着云梯有个后修的很窄的铁梯子,大约八十度,看着也怪渗人。两人对望一眼,顿生一种视死如归的惨烈。
然后顾子瑜就率先上去了,本已脱力,奈何脚上缺稳固支点,也只好卯足全身劲道孤注双手。不断后仰,看得蒋慎言一颗心悬得老高老高的,看她双脚颤抖,巍巍颠颠,摇摇晃晃地挪步,他觉得这心脏病是铁定落下了。
到了关键的地方,顾子瑜往下一望,正要惊呼,忽然脚下一松差点没坠云,本能地用尽全力吊在锁链上,顿时吓得哇哇大叫:“救命啊!我没劲儿了,我要掉下去了,我要死啦!”
这下蒋慎言确定自己要死于心脏病了。边一个劲稳住自己,边鼓励她一点一点往下蹭,直至她终于不再壁虎挂,慢慢开始挪动手脚,再然后终于过了,他的心才归了位。真是九死一生!
大抵是受了惊吓,接下去的一路上她保持安静,伴着冷月无声。摸黑到了东峰,准备明晨一睹华山日出之壮观。11月份,地面上已初有寒意,更别提到了山顶,简直寒风凛冽。顾子瑜直奔东峰宾馆,居然全满,只余大通铺。十几米长的窝棚,被单下尽是干草,根本是乡下牛棚之华山版。顾子瑜终于彻底死心,同意蒋慎言山顶露营的提议。罢了,当是可怜他背了真么重一帐篷上山的兢兢业业!于是,买了两件超厚的军大衣,顾子瑜无奈地走上了人生的第一次“混账”道路。
未免太早睡觉,顾子瑜又提议赏月。幸而,冷归冷,裹上大衣也不至于冻僵。加上外面亮如白昼,一轮空灵皎洁、飘逸圆满的明月悬于谷间,却又仿似触手可及。顾子瑜低着嗓子唱了一曲《但愿人长久》,蒋慎言眼神灼灼地看着她,如此总算没有辜负这良辰美景。
就这样,两人在西安待了整整一周。电台请的假也到期了,加上顾子瑜的皮肤颇为不适应古城的干燥,肠胃也被面食、杂粮折腾得够呛。于是,一周以后,仍是一个周末,两人飞回了上海。
当时又怎么想得到呢。这竟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共同旅行。回去之后,却是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