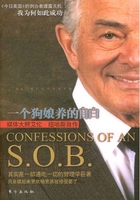“这是为什么啊?”我估计自己就是钻破了脑袋也想不透他这种莫名其妙的责任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傻瓜,王旭这个大傻瓜!
“你觉得他那个家能给他什么呢?”
我沉默着一言不发,那个早就残破不堪的家,如今彻底崩塌的家,唯一剩下的就是这片空荡荡的房子,我们的家在心里都是一团火,是寒冷的冬夜始终点亮的那盏风灯,就算走得再远身上再冷,想起来也能泛起来一点温暖。可是王旭的家,只带给了他孤独的责任感。
“那你让我怎么跟萧阳说啊?”
“你怎么想得就怎么说吧。也许离开王旭对萧阳确实比较好。毕竟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你知道门当户对也是有一定根据的。”
所以过了两天,我就照着李景赫告诉我的跟萧阳说了。
我记着那天天挺凉的,大概不是十月六号就是七号,虽然国家规定十一黄金周应该放七天假,可是全国人民都很明白高三的重要性,这七天到这帮备战高考的学生手上,也就只剩下三四天了。我要见萧阳也只能等到学校放学以后了。谁知道就连放学这件事儿高三的同学们都跟一般人不一样,明明课程表上到四点半就结束了,我却在“嗖嗖”吹拂的小凉风里苦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一边胡撸着身上的鸡皮疙瘩,一边心焦如焚,那种残忍的话让我怎么说出来,他妈的王旭!铁定是为了我这张没把门的嘴。真想能有个人狠狠抽我一顿大嘴巴。
本来我心里就够难受的了,一看见萧阳漂漂亮亮地从学校大门里头走出来,我立马浑身就哆嗦开了,一扭身就想跑。其实当时我要真跑了可能也就没什么事儿了,偏偏就是倒霉催得又遇见李景赫了。原先我就说过这一切就都是活该着,在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儿都是“活该着”这仨字儿组成的。
“你干吗来了。”
“找萧阳有点儿事儿。”
“嗯,她快出来了……程筱,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什么事儿啊。”
我的心就好像被一只大手紧紧攥住了,它一点儿一点儿地使劲,把我那颗本来就不太强壮的心慢慢地挤压成一小团,就等着最后突然爆炸。
“其实我……。”
话刚说了半截,他就被一群人包围了,都是学校篮球队的,不知道这些人是有预谋的还是怎么样,不早不晚就在那一秒钟全体冒出来。那里边有一个跟电影明星那么漂亮的姑娘,一张手就把我的小赫儿抱了个严严实实。我的心“啪”地炸碎了。李景赫我算懂了。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吧,关于你和这个电影明星一样的姑娘。就像千军万马从我的胸口奔腾而过,这一刻我终于明白,我永远地失去了我的小赫儿。
“程筱,我……”
“别说了,我去找萧阳了。以后再说吧。”
我一狠心冲着萧阳走过去了,把李景赫晾在身后瞅也不瞅他一眼,现在我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我还不如留下话跟萧阳说。
可是等真站到萧阳跟前了,我又瞅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藏着掖着的,没什么意思。”
她都这么说了,我也就只好全跟她实话实说了。等我说完了,她平静得像没什么反映,两只眼睛直勾勾瞪着我。可我就觉得更瘆得慌,鸡皮疙瘩比刚才起得还厉害。
“是王旭让你跟我说的吧?”
“不是。主要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我全知道。程筱,要说王旭,我认识他十八年了,他心里头想的什么没有我不知道的,一迈步我就知道他往哪边拐。你回去告诉他,澳大利亚我肯定去。可是去之前干什么这是我的自由,他管不着!”
“萧阳……”这下子谁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你知道王旭他妈是怎么没的吗?他肯定压根没提过。有一年冬天,他妈带他上后海滑冰去,可谁知道那一阵子冬天暖和,冰冻得不瓷实,再加上有人在上头凿窟窿钓鱼,王旭一没注意就掉冰窟窿里头去了,他妈跳下去救他,结果就没上来,听说后来让人捞出来的时候,头发眉毛上都结了冰柱子了。打那以后他就变了,以前他和别的小孩儿一样,能疯闹着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后来他爸非说是他把他妈害死的,天天出去喝酒去,喝醉了就揍他,还老把他扔到屋外边冻着,三九天也就穿一身秋衣秋裤。我妈实在看不过去,就老让我爸偷偷把他接我们家来。那几年他身上老是一块一块的青,可你问他怎么回事他硬是不说,有一回他爸拿个啤酒瓶子{卒瓦}他脑门上,那血哗哗地流,他连眼泪都没掉。实话跟你说吧,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上他的。我想着只要能让他过得高兴,我怎么着都成。我告诉你,只要王旭能觉得高兴,我怎么着都成!”
漂亮的女孩儿冲我转过身来,高高地昂起头,眼睛里放出炽热的光芒就像着了火,。这么坚定地站在一片荒野里,哪怕是突然刮起来龙卷风也吹不动她半分毫。我看着她那双火热的眼睛,突然从后背冒出一股凉气,就像是被谁泼了一瓢凉水,然后一瞬间被冻成大冰柱子,再“咯嘣咯嘣”的一片一片碎成块儿。
她说的那最后几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让人听了打心眼儿里觉得瘆,我这时候才突然发现,说不定这表面上看起来跟一张纸那么薄的姑娘是我们这里面最坚强的姑娘。她真的是个挺坚强的人,骨子里有那么股子不服软的劲头,但现在这种强硬却让我觉得可怜得要命。我就想立马为她上刀山下油锅,煎炒烹炸随她的便,让我想把所有的一切都大包大揽扛在肩上,让我恨不得掏心窝子,把什么都拿出来给她。
可我就是一混蛋,本来挺好的事儿就被我这缺了一个把门儿的破嘴全给毁了。
后来我一直没能见着萧阳,吃饭也就少了,没办法啊,以前她老是给我们送饭,现在连个面都不照了,我没钱的时候也就只能到老阔那儿蹭饭吃,可又不是天天都能蹭得上,晚上再饿也就只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忍耐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特浑,觉得自己这张破嘴,真该找根儿针给严严实实缝上。
有这么一天晚上我睡不着了,冬天差不多就快来了,都说一年有四季,可在北京从来就是过了三伏是三九,昨天还能穿短袖今天就得套棉大衣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披上衣服就出门了。一开门儿就看见院里有个黑影静静地坐着,吓了我一跳,差点以为是哪个不开眼的贼偷,进这家偷东西实在挺亏。走进了才看清楚这是王旭,还光着大膀子呢,真不怕冷。嘴里叼着烟,一点猩红的火光在黑暗中朦胧地闪动。这几天王旭都特沉默,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五十个字。
“你不冷?”
真是冬天快来了,我披着军大衣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小子不定偷摸摸蹲在这多长时间了,也不知觉没觉出冷来。
“还行。”
“王旭,我挺混蛋。”
其实我连个混蛋都不如,就是一惹祸的炮仗捻儿,逮哪儿就在哪儿点一炮,搅得人人都不得安宁。
“哪儿的事儿。”
“我这张嘴真他妈浑!”
“不说出来难道要毁了人家?抽吗?”
他一伸手,递过一包烟,他最爱抽的哈德门。
“抽。还是哈德门?”
“不愿抽给我!”
“孙子才不愿意抽。”
我笑着把那包烟从他手里抢过来,坐在他身边点上一根慢慢抽。
我们俩是挺有名的大烟枪,坐在那一会儿一根烟一会儿一根烟,一包烟挺快就抽完了。谁都清楚抽烟不是什么好习惯,一个大烟鬼会让自己本来完好的肺部变成什么样儿,牙齿和手指头染上什么样洗不掉的颜色,以及最后会怎样悲惨地死去。尽管很清楚地知道这些东西,但当时却认为那一切没什么大不了的,什么样的恐惧都比不上试图用烟草制造快乐的感觉,吸一口那种辛辣,从嘴里走进肺里,让它停留一段时间,最后再慢慢吐出来。这就是我们当时最愿意享受的乐趣,不计后果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