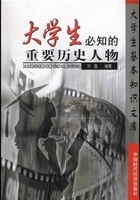不等她往深处去想,雪狼他们就跟了上来。
“把大家就叫出来吧!”
楚漓不给雪狼一丝喘息的机会,直接吩咐道。
雪狼听话的从腰间拿出一只被掏空了的牛角,仰首向天,吹了起来,响声低深暗闷,叫人心慌。
雪狼连续吹了几分钟,脸鳖的通红通红的,花朩蕾本想奚落他两句,但转眼间瞄到的情形,却让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只见那些个帐篷里,急匆匆的挤出了不少人,每个人出来时,手里都拿着一把大刀,行动迅速敏捷,没有一丝凌乱的迹象,不消半刻这些人已又序的跑了过来,脚下小步挪动着,一排一排,顷刻间,整齐在站在了花朩蕾和楚漓面前。
这个队伍让她震惊。
足足上万人的队伍,一刻钟不到,就集合到了这里,还没有一丝慌乱的迹象。
这样的高效率,让花朩蕾对他们的上司,无法不起敬。
再看雪狼时,他的脸上,再也看不了一丝,跟她争吵时的狂妄了,有的只是沉着和凛然,跨马走到她们的右侧,雪狼“唰”的一下,从腰间抽出一把刀,只见队伍里所有的人都看向了他那把高高举起的刀,战士们的眼里,有着与这冰雪格格不入的热忱,有着对不顾一切的向往。
这样的队伍,再一次震撼了花朩蕾,她由衷的替楚邪,感到担忧,这样的队伍,即便没有鹂鹰,只要楚漓想坐上那把交椅,随时都可以。
“蕾蕾,看!这就是我的人马,这就是我楚漓的力量,所以那天的话不是戏言,只要你愿意,我楚漓就算永世不得超生也会挥师南下的。”
耳后,楚漓的话,久久激荡在她心中,是,她曾经问过他,要是她想杀回去灭了大漓,楚漓可愿意?他当时回答她,说:只要蕾蕾愿意,他随时都会陪她杀回去。
曾经她以为那只是一句戏言,不承想,他竟一至记在心中。
楚漓的态度,又一次另她迷惑了。
“好,那我们明天就挥师南下,我要楚邪死,要楚澈生不如死!”花朩蕾说这些话时,没有回首去看楚漓,没有带一丝情绪,只是平述。因为,她打心眼里,对楚漓不信任。
楚漓从她耳后,俯视着她,“只要是蕾蕾的意思,漓一定照办!”他说的铿锵有力,说的字字千金。
“雪狼听命!”
雪狼举刀转身!
“告诉所有的兄弟,做好准备三日内南下,直取大漓首府!”
雪狼被楚漓的命令给吓呆了,可是鹰王的封印未解,“主子,三思!”
楚漓,大喝一声:“传令下去!”
雪狼愤恨的对着花朩蕾道:“妈的,又是这个女人?”
楚漓举刀,架在雪狼的脖子上,狠狠的,一字一字的道:“传令下去。”
雪狼痛恶的看了看楚漓,又看了看花朩蕾,举剑转身。在他转身的瞬间,楚漓在花朩蕾耳后,幽幽的道:“蕾蕾,我说过,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那怕永世不得超生!”
楚漓的话,让花朩蕾觉得,那么悲怆,那么苍凉。
怎么会呢?他不是一直在利用她吗?从转让李记,从给她鹂鹰,从看着她嫁给楚澈,从带她转走漠北,为什么可悲的人不她,而是他呢?
“等等!”在雪狼举刀的刹那,花朩蕾大喊了一声。
雪狼回首,眼眸里闪耀的水光,“丫的,可算做了一件让老子顺心的事!”雪狼重重的将刀插进鞘里,冲着花朩蕾道:“老子今天请你喝酒,喝漠北最好的马奶酒。”
花朩蕾嘲弄的笑了笑,“那酒太骚,还是留着你自己喝吧!”
雪狼笑笑,“奶奶的,不给老子面子!”
花朩蕾收住笑,转头看了看楚漓,“楚邪的命长不了,不急一时,等再拿到鹂鹰时,名正言顺,不费一兵一卒,岂不更好?”
楚漓温暖的笑了笑,接过雪狼手里的刀,高高举起,那种王者风范,显露无疑,“众将士听令!”
下面的士兵,哗啦啦,全部单腿跪了下来。
“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要告诉大家,我,草原漓王,不日就要南下,解救水火中的兄弟、乡亲们了,凭什么咱们要在这荒凉的漠北少吃短喝,皇上却在皇宫里逍遥自在,掠夺我们的粮草,抢走我们的妻女,这公平吗?”
楚漓的话,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最后那句“这公平吗”?问的更是天神共愤。
下面的士兵,哗,的一下,全站了起来,举起手中的矛,大声相应,“不公平!”喊声震天惊地,响彻云霄。
练兵场,那样的阵势,惊的花朩蕾方知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
那个的训练有素的队伍,那些彪悍的草原男儿,哪是她那几个乞儿所能比拟的,一个是皇上,一个是王爷,一个是世子,不管那一个盯上了她,诚心要她的命,她都活不了。这就是封建社会,这就是现实。到现在,她不得不低头了。
练兵场上的回声,在她心里久久激荡。
忘了怎么回的指挥营,忘了怎么回的庄子,只是有一个问号,不停的在花朩蕾脑子里盘旋,为什么楚漓总要对她说永世不得超生?为什么那日他会那么的悲怆?
如果说,楚漓是装出来的,那么雪狼呢?他眸子里的泪假不了。究竟有怎样的事,是她不知道的?直觉告诉她,这事,还是跟鹂鹰有关。鹂鹰!又是鹂鹰!
啪!窗外传来一声什么打碎了的声音,花朩蕾急急的跑了走去,什么人也没有,但窗下,那个装着腊梅的花盆却掉了下来,碎在了地方。
花朩蕾笑笑,敢来偷窥,却不敢让人知道,看来这个庄里开始有人对她好奇了。无所谓,反正她整日闲来无事,出去露脸,没什么大不了。
回屋拿来脖套和手套,披上厚厚的貂皮大衣,花朩蕾走出了,她那间屋子,真奇怪,楚漓在时,屋里总有四五个丫环在忙,怎么他一走,丫环们也就跟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