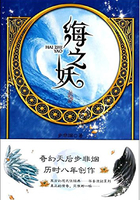“林涵,我们走吧,离开这个晦气的地方。”容峥扯动着红唇说道。
林涵微扯了一下嘴角,对容峥的话不置可否,在她看来,这个地方一点儿也不晦气,反倒有些神圣,她连高声说话都觉得是对医生们,病人们,还有那些漂浮着的看不见的灵魂的不敬。
林涵一手扶着椅子的把手要站起来,程池心里一紧,走了过来扶住了她的手臂,一条胳膊揽住了她的肩膀,林涵抬起眸光对他轻轻一笑。
楚慕楠紧抿着薄唇,摊开手接过容峥手里的手提包,手指相触的瞬间,容峥的身体微微一抖,咬了咬内唇,低垂下眸子转向别处。
楚慕楠心里微鄂,喉间浮动了一下,静默的走了出去,程池揽着林涵慢慢的走出病房,容峥一个人走在最后面。
走出医院,呼吸到迎面而来的带着热气的风,林涵心里百感交集。
她不知道,她未及面世的孩子是不是成为了护士们口耳相传的长廊里幽灵的一员,她只是觉得心很疼很疼,坚硬的像是长了一层厚厚的茧。
城市的夜晚,霓虹一盏一盏的亮了起来,一天又悄无声息的飞逝了——
黑夜浓郁,一件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里,聂雪儿抱着身子靠在墙角,咬着嘴唇脸上丝丝冰冷。
门开了一丝缝隙,一条身影闪了进来,压低了声音叫道:“雪儿,雪儿……”
聂雪儿没有应,连头也没有抬,保持着刚刚的姿势,她心里像被冻僵了,波澜不兴,耷拉的脸皮里,往日里神采照人,光华流转的眼睛,此时没有一抹光彩。
“雪儿,是妈妈害了你,对不起。”聂霜降摸索了半天,总算摸到聂雪儿的身体,她抱住了她,禁不住泪水连连,“雪儿,你身上怎么那么冷?”
聂霜降眸子闪过一丝惊慌,两只手抚上了聂雪儿的脸,努力瞪大了眼睛却怎么也看不到她的表情。
“雪儿,别吓妈妈,你说话啊。”聂霜降的声音里透出了一丝惊惧,手掌摩挲着聂雪儿的脸滑到了她修长冰凉的颈子上,然后又爬上了她的额头,聂霜降心尖微微一跳,叫道:“雪儿,你病了,我去找他,让他给你找个医生。”
聂霜降说着就要站起来。
“妈,不要去找他,不要。”聂雪儿一急,拉住了聂霜降的裤管。
聂霜降蹲了下来,猛地抱住了聂雪儿的头,哽咽着抱紧了她:“雪儿,我苦命的孩子。”
温热的液体滑进了聂雪儿的颈项,黏黏的,酥酥的慢慢滑动。
聂雪儿喉间一紧,一丝苦涩的液体袭了上来,她略略带开聂霜降,睁大了眼睛看着眼前五官模糊难辨的聂霜降,轻声恳请道:“妈妈,我们不要报仇了好么?离开奢铎,回到爸爸身边去好不好?妈妈……我……我爱上晓武了,我不想伤害他。你答应我好不好?我一刻也不想在这儿呆着了。”聂雪儿的眼泪无声无息的掉了下来。
“你……好吧,在欧阳晓武和我之间,你到底还是选择了他是么?”聂霜降声音里透出了些微的哀伤,沉沉的,听得聂雪儿的心一钝一钝的疼。
“妈妈,你怎么这么说呢?你和晓武一个是我最亲的人,一个是我最爱的人,不论你们谁有事,我都不想。我只是觉得,奢铎他……不会帮我们的,妈妈,这么多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么?妈妈,这么些年,你光顾着报仇了,我想问你,你快乐么?”聂雪儿用力抓住了聂霜降的手臂,仿佛就此抓住了一线希望。
聂霜降的脸沉了下来,抿着嘴角僵冷的笑了笑:“雪儿,这些话你早就想说了是不是?”
“不是的。”聂雪儿摇了摇头,有些苦涩的勾起嘴角:“我到最近才明白,我过去错了好多,我说不清楚,只要跟晓武在一起,我心里就很踏实很安稳,很想就那么跟着他一辈子。”
聂雪儿激动的跪了起来,紧紧的握住聂霜降的双手,眼泪漫上了眼眶,“妈,我一想到不能和晓武在一起,我的心就好疼好疼,像要窒息一样。我知道,你恨他,妈妈,你连带着也恨我吧,只要你同意让我和他在一起,我不结婚也行,啊,奢铎不就是怕我结婚么?我不结了,我把我自己撕成两半,成么?一半留给奢铎,他想怎样就怎样,另一半我带走,妈,我的心已经给了晓武了,身体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妈,我想死,死了就能和晓武永远在一起了。”
聂霜降的心疼了起来,已经好多年没有跳的这么剧烈了,她莫名的哭了,无声的,一滴一滴的眼泪从她早已干涩的眼睛里泛了出来,她深吸了口气,借以缓和窒闷的胸腔。
“雪儿,傻孩子,别哭了,妈妈放你走!”聂霜降无声轻叹,把聂雪儿扶了起来。
“妈妈。”聂雪儿的眼里闪过一抹光芒,被聂霜降搀着走到门边,她的心里蓦地犹豫了起来,敛着眉睫心事重重的样子。
聂霜降把手按上了门把,只需轻轻一转,聂雪儿就可以离开这里,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聂雪儿倏地按住了聂霜降的手,眸里蓄着担忧之色,哭得沙哑的嗓音道:“妈妈,我要是走了,奢铎不会放过你的。”
“这个你就不要担心了,去找欧阳晓武,最好带他离开欧阳家。”聂霜降语气淡淡的说道。
“走吧。”聂霜降推着聂雪儿走出门口,一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才走回来。
大厅里的灯倏地都亮了起来,彻夜不眠的保镖们一个个蹦了出来,站在两旁,披着老虎皮的沙发上坐着高大的奢铎,他健壮的长臂揽着一个妩媚妖娆的女人。
奢铎光着膀子,他本就身材魁梧,光着的上身肚皮突出,胸前长了一撮浓密的毛发,碧绿的眼睛一闪一丝寒,看起来虎虎生威,他撇开女人坐直了身子,碧眸越过聂霜降凝望着她后面长而幽深的黑暗道路,低沉的轻叹道:“她走了!”语气似发问又似陈述,透着一丝淡淡的惋惜。